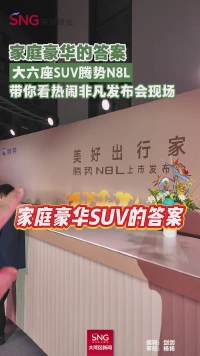人物简介:张博钧,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福田英才”、深圳市后备级人才。2006年4月入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年3月至今,任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多年来,张博钧深耕信息通信行业,见证了行业的诸多变革与发展。2007年,张博钧投身于深圳信通院的筹建工作,随后便一路伴随深圳信通院,与之共同成长并见证了深圳信通院从无到有、逐步壮大的全过程,也见证了深圳从“手机之都”迈向“创新之城”全球信息通信创新高地的重要历程。
口述时间:2025年8月8日
口述地点:深圳信息通信研究院
一、福田上沙工业区建起“世界领先的电波暗室”
2007年7月6日晚,北京的夏夜还带着热气,我刚结束一天的电磁兼容测试工作,手机突然响了。电话那头是领导的声音:“明天一早飞深圳,有个大项目要你盯。”没说具体做什么,也没说要待多久,只说“场地已经选好,得赶紧启动”。
那时我入职刚一年多,每天面对的是做不完的各种各样通信设备的EMC(电磁兼容)测试。挂了电话,我翻出几件换洗衣物塞进背包,心里打鼓,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座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创造经济奇迹、充满活力与机遇的年轻城市,我去了干什么,能不能干好?
第二天,飞机落地深圳,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车穿过热闹的街道,最终停在福田区一片老旧厂房前——上沙工业区,听说这个工业区以前是做纺织的,现在已是废旧厂房。带我来的同事指着工业区12栋的场地,说道:“就这儿,要建咱们的南方手机检测中心实验室,10月11日高交会揭牌,只有3个月时间”。
我当时就懵了,以现有的场地条件看,很难满足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要求,尤其是专业的电磁兼容暗室。这种大型暗室不是普通房间,是测手机电磁辐射的“专业考场”,至少得是9米长、6米宽、6米高的密闭空间,内壁要贴满吸波材料,对地面承重的要求极高。可眼前这厂房,层高不够,地基下面是什么情况也不清楚。

厂房筹建
最后我们选择在两栋厂房之间深挖,在楼房的“夹缝”中建设暗室主体结构。我们24小时连轴转,政府部门也开了好几次协调会,环保、城管、电力的人都到现场,“有问题当场拍板”。
同时,我们也有了个更大胆的设想,暗室地板的吸波材料一般都是手动铺设的,费时费力,我们提议采用自动化的方案,“要建就建全球独一无二的电波暗室”。我们打算建一个5米法的全半电波自动转换暗室,就是说转台可以自动升降、地板可以像抽屉一样自动伸缩,这在当时都没先例可循。可设计图纸改了十几版,施工队都说“做不了”。我带着暗室建设团队和施工方守在工地,一边画草图一边改工艺,凌晨三点还在开沟通会,最后硬是把液压装置加轨道的方案给落地了。
10月11日高交会开幕那天,暗室也正式落成。自动滑动的地板和升降转台,加上世界领先的吸波材料……有国外专家评价,这是见过的全球独一无二的电波暗室。
值得一提的是,脱胎于旧工业区的福田上沙创新科技园也于当年10月高交会期间正式开业,同期获授“深圳市移动终端产业园”,开业初期入驻50家科技企业,超80%为研发型,涵盖手机制造、LED等领域。向通讯科技奋进的时代,在福田启幕。
二、华强北成为“全球智能硬件创新中心”
暗室建起来了,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2007年前后的深圳,手机产业正处在“野蛮生长”的年代。华强北的街巷里,随处可见打包的手机零件,小作坊随便攒一台手机贴个牌就能卖。但这些手机大多没做进网许可,没有通过严格的技术测试,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当时全国手机品牌一半来自深圳,这种现象使得大部分正规厂家都跟着受到了不好的影响。
企业想合规,就得把样机送到北京检测,一来一回要花不少时间,测试不合格还得重新整改调试。有次我去华强北调研,一个老板叹着气说:“我们也想做正规军,可等检测报告出来,市场早被别人抢了。”
这正是我们来深圳的意义!深圳信通院是北京之外首个通信终端产品的国家级检测中心,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手机考场搬到深圳家门口”。
头一个月,来送检的企业挤破了门。当时有个厂家,产品送检后有个技术参数的测试结果一直都不理想,我们主动为他们的技术团队协调了场地和测试设备,使他们的问题得到了快速地解决,事后他们激动地说:“现在在深圳,马上就能改,太值了。”慢慢地,变化看得见。企业手机新品上市周期至少缩短了2至3周,上市成本低了,企业合规检验的积极性就高了,市场活力就更凸显了。

WCDMA射频测试系统
有件事我印象很深。2009年,当时一个大型品牌商送检一款3G手机,测试时发现电磁辐射骚扰值偏高。他们的工程师驻场改了一周,每天和我们的测试员讨论到深夜,最后达标时,整个团队在暗室门口鼓掌。后来这款手机成了爆款——这就是深圳企业的韧性,给个标准,他们就能做到极致。
产业聚集效应也跟着来了。我们入驻上沙创新科技园后,周边陆续搬来十几家手机方案公司、整机厂商。根据园区统计显示,我们来之后,纳税涨了50倍,人才结构也更高端了。
再后来,手机行业“变了天”。技术门槛越来越高,利润越来越薄,不少小厂转型去做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留下的华为、中兴、小米、OPPO、vivo越做越大,成了全球品牌。看着华强北成为了“全球智能硬件创新中心”,我突然明白:我们守的不只是检测关,更是深圳产业升级的“转折点”。
三、从“本土检测”到“全球认证”:跟着产业跑,才能不掉队
随着“深圳手机”产能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产品出海的需求也越发旺盛。但是企业产品要出海,去欧洲要CE认证,去北美要FCC认证,去东南亚也有当地的标准,每次都得找不同的机构,费时费力。当时有个做智能终端的企业老板找到我们:“能不能一站式搞定?我们连认证标准都看不懂。”
于是,我们开始“补链”,引进优质的国际认证合作机构,工程师们也加班加点研究法规、扩充能力,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为企业打造“一站式”检测认证服务的平台。
记得当时有个企业,他们的产品想要进入欧洲市场,我们帮着分析法规要求,研究测试方案,还培训他们的团队看懂欧洲标准。后来他们的产品成功打入欧洲市场,每次提起我们,都说“当年多亏了你们那套‘出海套餐’”。
技术也得跟着迭代。5G时代来了,通信产品的类型也越来越丰富。有次企业送来一款无线光通信设备,我们在测试评估时发现没有针对性解决方案,于是我们和他们的研发团队一起攻关,最后形成的测试评估方案,为制定行业标准提供范本。
随着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快速发展,我们在跨界新赛道上大干快上。2023年,智能网联典型应用系统验证平台正式上线,这是我们在深圳建设的首个面向整车和汽车零部件检测认证的综合性认证检测服务平台。
有一次在实验室遇到一位转行到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老朋友,他们的新车来做测试,看到我们新建的整车测试环境,颇为感慨“没想到你们发展这么快,什么新方向都让你们抓住了,不愧是深圳速度啊!”
这让我想起2007年那个简陋的厂房——从手机到智能网联车,从检测到赋能,我们始终在做一件事:跟着深圳的产业跑,跑快一点,再快一点。
现在我们的业务早就不止于手机了。具身智能、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深圳瞄准的新赛道,都是我们的新战场。
有次参加福田区的座谈会,有人问“你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说:“是知道深圳的企业需要什么——他们往前冲,我们就把‘后防线’筑牢。”
四、从“手机之都”到“创新之城”:深圳的密码,藏在“敢试”里
今年是深圳信通院成立18年,也是我来深圳的第18年。有人问我,深圳从“手机之都”变成“创新之城”,到底靠什么?我想,就藏在那些“敢试”的细节里。
刚建暗室时,福田区政府把协调会开在工地,局长带着工程师蹲在泥地里画图;我们想要扩充检测服务能力,区里马上对接专用场地;企业送检缺钱,区政府就送检测认证扶持政策——这种“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氛围,让创新没有了后顾之忧。

OTA暗室
我记得早在2008年,福田区政府在制定深圳国际创新中心场地建设方案时,就专门征求过我们对场地的建设意见,层高不够,就调整楼层规划;电力不足,就协调电网扩容。有次深夜加班,看到区里的工作人员还在现场盯进度,我说“太辛苦”。他笑着说,“你们科研人员能出成果,我们这点累算啥。”
这种劲儿,深圳人身上都有。我认识的一个检测工程师,从2007年跟着我们干,现在成了5G测试领域的专家,他说“在深圳,只要肯学,就有机会”;有个企业老板转型做智能终端设备,现在产品卖到全球,每次见我都要聊技术创新——这就是深圳的包容,允许试错,更鼓励成长。
现在的深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手机之都”了。站在深圳国际创新中心的办公室里,能看到远处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那里的科研人员正攻关量子科技;楼下的街道上,年轻人拿着智能硬件原型机讨论方案;我们的实验室里,测试员在给低空飞行器做电磁兼容检测……从通信到科创,从跟跑到领跑,这座城市始终在突破边界。
有时我会想起2007年那个闷热的夏夜,接到电话时的忐忑。如果再选一次,我还是会背上背包来深圳,来福田——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说,敢闯敢试,就有未来。
18年了,我从刚入职的年轻人变成了老“信通人”,深圳从“手机之都”变成了“全球创新高地”。我们都在成长,都在见证彼此的奇迹。这大概就是深圳给每个奋斗者的礼物:你把汗水洒在这里,它就会还你一个惊喜。
编辑 白珊珊 审读 秦天 二审 李璐 三审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