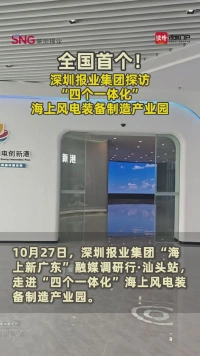正月十五是过年的又一个高潮,也是年的终结日。
正月十五俗称元宵节,当然要吃元宵(汤圆),年前做的汤圆已经吃完,在正月十二或十三重新做些。元宵节中午,还要弄一顿好吃的,有猪肉、鸡等好多荤菜,还包包面,大人也喝酒。
老家流传着“三十的火,十五的灯”习俗。除夕晚上,家家户户特别挑选干燥而耐燃的木柴,在火厢(有地方叫火塘)里烧起来,且通宵不灭。火烧得旺、时间长,预示着家业兴旺,日子红火。此时,全家人围坐在火厢边守岁,一边吃着自制的点心,一边商讨着新年打算,描绘着新一年的美好图景,全家人如何努力实现。正月十五晚上则是点灯,每家在所有房间点上灯,直到深夜,或到第二天早晨。这样做,一是为了给已故的祖先照路,好让他们过完年后回到各自的去处(大年三十早上,子孙们已到祖先坟上接他们回来过年),二是祈望新的一年全家人安康,生命之灯常亮。记得我家曾有一盏马灯,铁制的,有玻璃罩,十五的晚上要点一夜。

那时家乡还有正月十五赶毛狗、嚼虼蚤的习俗。有的是在临晚饭前,有的是在吃早晚饭后,抱一大捆干柴草,来到房屋附近的菜园子里,找一块空地,点燃柴草,火焰熊熊而起,我们小孩便在旁边跳动或跑来跑去,并大声喊叫:“赶毛狗哟!赶毛狗哟!”家里准备的鞭炮,此时也要放完(过了十五,年就算过完了,就不再放鞭炮了)。赶毛狗非常好玩,十分热闹。整个大队,能看见的湾子,烟火和“赶毛狗哟”的喊声此起彼伏,火焰若隐若现。那时我不知道“赶毛狗”是什么意思,后来慢慢知道,它的寓意包括除邪免灾、驱赶有害动物、祈求平安和丰收。赶毛狗对那时的小孩子及年轻人实际有些娱乐的作用。那时的农村娱乐十分有限,有的大队组织演出队,排练《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现代京剧样板戏,也只在春节前几天或年三十到正月十五之间一两天时间,到一些村子演出几场。有的大队放几场电影。有的大队有高跷或秧歌队,但元宵节都到大公社汇报演出了,偶有猜灯谜活动,那也只是街上文化人的娱乐。
所谓“嚼虼蚤”,就是吃点心。晚上,大人将春节期间亲戚拜年提来还没有用完的点心拿些出来,全家人围在一起边喝开水,边吃着点心。平时很少吃到这些东西,觉得十分美味。后来,好吃的东西多了,这些放了一二十天的点心,有些嚼不动,吃的人也少了。渐渐地,走亲戚不再送这些廉价礼物了。虼蚤,是骚扰人畜的寄生虫,将其嚼掉,寓意消灾避害。
老家还有接出嫁的姑娘(女儿)回娘家过元宵节的习俗。或许是大年三十出嫁的姑娘不能回娘家团年(当地习俗),或许正月初二姑爷带着媳妇给丈人和丈母娘拜年,难有女儿与父母亲单独交心谈心的机会,所以,各家各户有把嫁出的姑娘,在元宵节把她们接回来过节气。
爷爷奶奶的姑娘即父亲的姐姐——我喊姑妈。亲姑妈十八岁出嫁那年去世,后来姑爹续娶夫人,认父亲为弟弟。夫妇俩与我父母情投意合,亲如兄弟姐妹,两家相距二十多里,但有好出产,第一时间互送尝鲜,相互扶持、互相帮助。拜年走亲戚送节气,与亲姑妈别无两样。姑妈家五个儿女,与我们兄弟姊妹年龄相仿,互为发小玩伴,经常往来。我在荆门工作时,家中油漆家具都是他们做的。后来我们两家都搬到胡集街上,来往方便且走动更多。至今我与几个表弟、表妹偶有联系,在我的引导与支持下,三表弟余啸俊一直在深圳工作。
有一年,父亲要我带着礼物去接姑妈来家里过元宵节,来回走了一天多。从快市五里牌,到岛口王岗近三十里路,要过好多道山岗和冲洼。特别是到了小河口,翻河堤,找艄公摆渡过河,有时小船到对岸去了,等船回来要个把小时,好在艄公一直在船上,只要有人喊,艄公便摆渡过来,就是一个人,他也会把你载过河。记得过河一次收费一毛钱。姑妈来到家里,与爷爷奶奶、父母亲又是一番亲热,与全家人又是一顿好吃的。那时普遍清苦,来往礼物不多,但父母亲与姑爹姑妈亲如兄弟姊妹走动了一辈子,快活了一辈子,令我印象深刻,成为我们子孙珍惜亲情友情的榜样。
过了元宵节,春节才算结束。进入新一年的平常日子,大人开始忙春耕,小孩则开学。起初小孩子有些不习惯,也不情愿,对春节期间吃好的、穿新的、走亲戚、天天开心的美美日子依依不舍。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学、挣工分和家务活又压上了肩头……
春节已经远去,于是乎,我们小孩子又数着日子,期盼着来年更美好的春节!
编辑 刘兰若 审读 伊诺 二审 刁瑜文 三审 张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