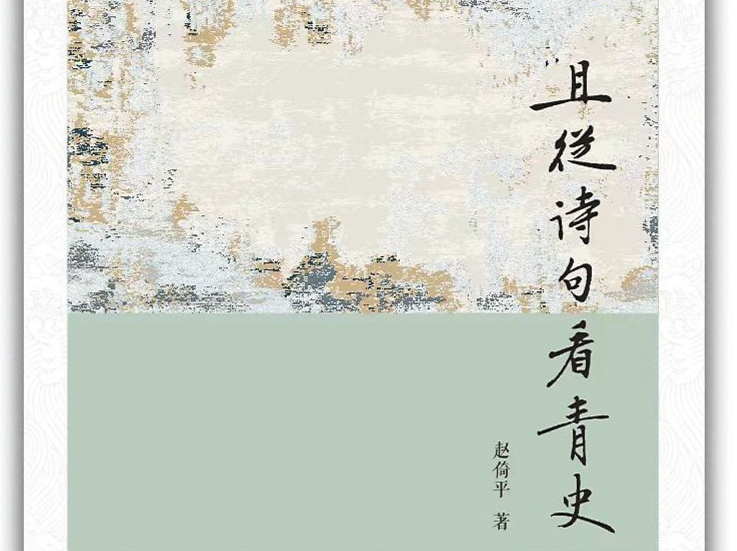■ 后商
大概从2004年归国开始,多多的诗歌就抛弃了抒情的细密,叙事的慷慨,转向以断语、棒喝为主的风格。诗歌从依靠动词运动挪步到依靠名词运动,动作少了,动词少了,但从高处或更高处来的名词却多了。更重要的是,浪漫主义诗歌让步于精神诗歌,感性作为探索的代价被多多放弃了。

无词
说多多拥有一套诗学,一定会遭到他的反对。但多多有着强烈的以诗学入诗——并非以观念入诗——的倾向,基于此,道出多多对于诗歌的想法就十分必要。在写于2017年的诗歌《词内无家》中,诗人在十二个字中写了五个“无”,“无名,无坟,无家/无名歌唱无名”。在极致的重复中,诗人展露了对“无”的信任:原本是形容词的“无”在复沓后变成了名词;原本空洞的“无”在复沓后变成了实在;原本渺小的“无”在复沓后变成了至高者。“无”的来源也很容易领会,“无”既来源于多多在现实中找不到、看不上、念不了的体验,也来源于多多所持有的“诗歌凭‘空’而来”的信条。在此不妨将多多的诗学总结为“无”的诗学,一方面多多并不相信诗学,另一方面多多又高度信赖“无”。
多多自称从策兰出发,两者都触及了哲学与救赎的命题,其实多多所见证的乃是全然不同的策兰,策兰没有如此多的无。多多的无与其说是哲学诗学,不如说是自我写照,自白的无就是有,就是全部有。在多多的诗中,大地赤裸裸地呈现为几股势力,几对关系,万事万物或高或低,读者都能够踏在其上,与诗人一同历险。他想象着自己处在风暴中心,控诉恶人,惩罚罪人,击垮敌人,他几乎是唯一的幸存者,因为他一脚还在废墟之上。
不妨从头说起,诗人对事物、对奥秘的精准言说,激化了对自我的依赖,对生命的依赖;但人的生长宿命并非完全可以把握,对自我和生命的依赖往往伴随着无法挽救的恶果,我们已从创造力神话见识了太多例证,在这些创造力神话中,诗学乃作为献身后的果。时代无所谓成败,诗歌才会有所成;词无所谓丰寡,人才会有所“回神”。但种种壮举之后,是不堪一击讲述的生活,以及无从说起的命运。这大概就是“无”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吧。
像多多这样取向断语、截句、诗学的诗歌在中国几乎成了主流。这股潮流我称之为诗歌的抽象化,它不同于极简主义,也不同于观念主义。它主要根源于中国诗人强力的文化心态。诗歌在中国历来被当作最便宜的、最佳的体裁;同时从1970年代开始借由本土生产的现代主义神话,诗人被鼓励进行独自的自由创造。在新近的二十余年,中国诗歌的抽象化更是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诗歌的抽象化来自于文化对所有人的开放,艺术在各维度的多元化,以及人们感受力的泛化。虽然就艺术而言,艺术越来越“小”,主要局限于当代的艺术体系,但是就审美而言,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只有这样或那样的抽象化,才能兼顾艺术和审美。像多多这样强风格的诗歌实实在在是这股潮流的未来所向。

▲多多:原名栗世征,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表性人物。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后来调到《农民日报》 工作。1972年开始写诗,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曾获北京大学文化节诗歌奖(1986)、首届安高诗歌奖(2000)、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4年度诗人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2010)等。曾旅居英国、荷兰等地。2004 年回国后被聘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2010年被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做驻校诗人。著有诗集《阿姆斯特丹的河流》《行礼:诗38首》《多多诗选》《多多四十年诗选》等。
创造
然而多多的诗歌不止抽象化那么简单,他尝试向世界宣告:诗歌至真至简,诗歌不容置疑。在田野上,在新院中,在命运的必然前,其实什么也不需要说,什么也不必说,因为每一个为之存在的我都领会到了那个奥秘。
《无词词语》如是揭示了多多诗歌的生成。多多从《道德经》的观念出发,过渡到对家以及与家有关的命运的“抛弃”,再过渡到持续地肯定创造,肯定“完成”——实际上在多多的理念中不存在完成。在《无词词语》的后大半,人的形象被替换为诗的形象。多多向我们强调:创造是无,创造是从未适时抵达、降临的奇迹,创造是死亡,正是无、死亡中蕴藏着新的“完成”,新的人。最后,多多展示了一个悖论黑洞,写作是无有相生,诗歌是无有相生,生命是无有相生,然而这再也不是《道德经》那种优游的处世,反而是弥漫着必然与痛苦的绝境。
“字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根基在云里”,多多在《听雨不如观雨》写道。词是家,这是多多屡次写下的证词,也是多多秉持的信条。这个信条与其说来自于哲学、精神,不如说来自于实感,对诗歌的实感。现代主义在达到“高峰”时“跌落”到“灭点”/“寂点”,并非毫无来由。词是空无的,但词又是无限拥有的,这并非悖论,而只在于如何操弄智慧。在多多的想象中,词不再是可被打包的语言,或是存在或不存在的主神,而是无边命运之“无”的“黑洞”。
其实,多多的“主体”也并非实存的人,而是既虚构又内蕴的人。“主体”并不随时间有所改变,他没有语言,没有动作,没有爱之所有,而仅仅拥抱着力量的消逝,某种不可能实现的存在。而词像是“围绕”的、外在的,它们向诗人靠拢。如果说写《手艺》时的多多还小心隐藏这个主体,使其保持和一般性的接近,那么晚期多多则彻底暴露了这个主体,他再也没有任何居心将自己的“做”——在梵语中,艺术即“做”——和手艺人的“做”小心地对应起来。
很多时候,多多无意泄露了他对人与事的普遍的爱。在《那时》中,从诗句中消失的“你”,又在蜜语中重现。在《在几盏灯提供的呼吸里》中,自然化身落叶提供人以工作,以恩赐。在《捧读月光下的战栗》中,“生可以死,死可以生”实实在在祝福着自由而爱的人。
浪漫的多元的时代过去了,扑面而来的是平庸的僵硬的时代。这也意味着那个饱满的,同时又充满决断的文学已成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控诉式的,但又沉默的文学。当然,妄想某种文学与时代存在极大关联是奢侈的。

《拆词》多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10月
孤独
在和现代纠缠的时候,多多也是无力的。偶尔他极失败,他如此痛恨、斥责“还原论”,字里行间还是流露着“还原论”的痕迹。但大多时候,他又将“现代性”扫荡一空,这时候他就像引他成为诗人的波德莱尔一样,超越现代成为古典者。现代或现代性是否为超越性提供空间,答案或许是否。这一点在多多的诗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多多放弃了对现实的超越:诗人在追问词的同时,也放弃了词与此时此地现实的关联,当现实赋予他灵感后就离开了。另一方面,多多起码展演了“对抗”现代性的后果:他部分诗歌呈现了“写作,使亘古可以忍受”的倾向,然而忍受说到底无关现代、无关生活,它只关乎自己。
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孤独的诗人。他已独居太久,也已在自己的腔调与风格中沉醉太久,陈年的桌子上堆积着三年前的颜料,居室内新书没有太多,旧书由于时常翻阅,沾染了无声的“沉默”、无声的思想,整个房间笼罩着药一般的气氛,似乎不曾有人来过,又似乎太多人来过。
理解多多的难度在于,他拒绝传记,拒绝从诗跳入其他体裁,跳入其他现实。见过他的人都知道,多多脾气坏,底气强,立场不容置疑,同时他“空”得仅余一具躯干,内里也没有生活的繁杂。多多晚期的诗主要聚焦于图像反抗磨灭的过程,即多多以诗为自我认同,赋予诗一个家。诗人的图像似乎不是诗歌,而是某种未被写下的诗歌,是常识之外的常识。
到了晚年,他遭遇了孤独,遭遇了沉默,遭遇了匮乏,遭遇了“死亡”,但他以前所未有的心拒绝了它们,并非仅仅因为他未遭遇好时代的好。多多却开始写起了“孤独”——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孤独大抵是属于青年的词。多多像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我们的草皮屋顶绿着/我们孤独,如曾祖栽下的白杨//我们的孤独,由血肉筑成”。以“革命”“后革命”形容这样的孤独太局限,以“一无所有”形容太宣泄铺张,或许多多的孤独在于他如此坚守于他的精神身份,不为世界和生活所动摇。
如果说,朦胧诗仅仅是一个策略,是一次对过去的抒情,它从未真正地创造历史,它将历史矮化成一个同谋者,同时将自己排斥在那个富有责任的历史的对方。那么,多多所希冀的诗歌则是一次对历史的彻底反对,对循环与还原的彻底阻断,对个体、自由、创造的高度张扬,他像使徒一样领受一个无限的未来。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