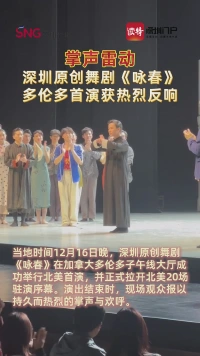编者:深圳诗人阿翔说,他在这座城市呆久了,难免在写作上会有“落根”之感。因此他的写作也构成了“深圳诗歌地理”。实际上,移民与流动,是诗人带有“永恒的乡愁”的意味,带有“在路上”的特征。
阿翔自称是一位“隐秘的诗人”,或“一个充满矛盾的诗人”。但他又被贴上了许多标签,如70后,旅人,自由职业者,啤酒主义者,民刊收藏家,戏剧爱好者,摄影发烧友……只是这些都不足以概括阿翔内心的丰富性。作为诗人,阿翔信奉“写作即消逝”——面对世间的诸多不合理,只能让诗替自己的灵魂说话,在消逝中不断地呈现。

深圳的移民与流动,是诗人“永恒的乡愁”
■阿翔
1
时常坐在地铁中,车窗外的黑暗似乎是感受不到时间,而一过隧道迈入露天,风景在我眼里一闪一闪而过,仿佛是时间的实体,又仿佛不可捉摸的幻象。我究竟想抓住什么?或者还能回顾什么,可能我只会记得一本书的章节、在路边欣赏一朵新开的花、在夜空相见烟花一瞬间的惊艳,却不记得我写过的一首诗,写过就忘了,忘了就忘了吧,我把诗歌交给了时间,而时间永远处于消逝中。更多的是一首诗重叠另一首诗,层层叠叠般地覆盖过去,对我而言,或许遗忘也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让自己处于头脑清空状态,也意味着下一首永远在重新开始。
回到写作上,通过一首诗意识到时间的消逝,也许我该明白,这绝不是仅仅一次性回顾。也就是说,一首诗的完成即成为消逝,谁也挽留不住,即使稍稍停留一下,却已失去了当时写作的冲动、构思、激情,就像一道闪电那样亮过之后迅速消失了。
我不会这么轻佻地感慨:逝者如斯夫……有时候,写作的时间有大部分被我丢弃掉了,也许本该是丢弃掉的。因为诗人不会停留在过去,面对的还是不可知的未来,而未来只要在写作上到来,就成为形而上的消逝。

▲阿翔:生于1970年,安徽当涂人,1986年写作至今。在《大家》《花城》《山花》《十月》《诗刊》《今天》等杂志发表作品,著有《少年诗》《一切流逝完好如初》《一首诗的战栗》等诗集。曾获第六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第二届中国诗剧场贡献奖、“第一朗读者”最佳诗人奖、2014年首届广东省诗歌奖。参与编选《70后诗选编》《中国新诗百年大系·安徽卷》《深圳30年新诗选》等选本。曾参与“瓢虫剧社”戏剧创作和演出。现居深圳。
2
这些年在深圳安静地工作、生活、写作,其状态远比当年“北漂”要好得多。以前“北漂”只为生计奔波,时刻焦虑,写作难免静不下心,显得浮躁。来深圳之后曾有友人对我说:“如果一个诗人不能自食其力,他就丧失了所有的生存背景和写作背景。”这话深得我心,一直牢记。
来深十余年,我不记得写了多少首,只知道在一个城市呆久了,难免在写作上会有“落根”之感。所以我喜欢写上沙村、写白石龙、写洞背村、写莲塘、写龙塘村、写黄麻埔、写黄贝岭、写上岭排……这些构成了我的深圳诗歌地理,如果拔根而起,你会看到血肉至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实际上,移民与流动,是诗人带有“永恒的乡愁”的意味,带有“在路上”的特征,在真正植入深圳地域的同时面对工业文明、都市生活、城乡反差等深入体验,体尝出深圳的味道,表现出我的喜悦、迷惘和痛感。
我还曾应朋友之邀陆续参与、协助编选了云南人民版《深圳30年新诗选》、海天版《面朝大海:2012年深圳诗歌大展》、海天版《深圳文学2013-2014双年选·诗歌卷》等选本。可以说在这么一个“深圳速度”的快节奏城市,总有少数人安静而慢悠悠地写作,这是最悖论的现象;另一方面,外来诗人在深圳的书写,有效地产生化学般的效应、优化和组合,为诗歌的生长与繁衍营造了一个十分难得而又恰切适宜的环境,诗人很容易迅速认同深圳,并且找到合适自己扎根的土壤。

▲阿翔
3
我不喜欢追忆什么,但有必要说一下,在我小的时候,因发高烧而误打链霉素(streptomycin),损害了听觉神经,从而影响了我说话表达的能力。至今我有着两耳不同程度的弱听,戴上助听器也是无济于事,因为我听到的“声音”远远大过了“语音”。所以,我与世界的沟通,只能依靠笔和纸,通过一笔一划,几乎不必思考什么,而能把诗性的东西完整表达出来;但是我一开口说话,往往要费半天劲儿,一边思考一边努力想说清晰点,结果显得结结巴巴、含糊不清,虽然听众们用鼓励的眼光看着我,甚至给予掌声,但我不可避免地涌起一阵挫败感。
唯有沉默给予我内心的强大,给予我慰藉。或者说,不说话,才是一个人的完整。通过写作,诗歌在灵魂的黑暗处发出隐约的光亮,哪怕是一闪而逝,这时候我显得敏锐无比。在时间的消逝中,写作仍然是“日日新”的修远,即使掌握诗艺的秘密,它依然是永恒的秘密。就好像木匠掌握了技艺,但是再好的技艺,如果不是用于自己的创造,它最多按图索骥重复前人的经验。最困难的恰恰就是对经验的超越。这是由内向外的伸展,一个世界的自足性、丰富及不可捉摸的神秘,在我身外却是与我内在相关的。
4
就我自己而言,我被贴上好多的标签:70后,旅人,自由职业者,啤酒主义者,民刊收藏家,戏剧爱好者,摄影发烧友……但我终究是一个隐秘的诗人,或许换个说法,一个充满矛盾的诗人。一方面,在有限的诗歌圈,作为诗人,我这个身份是公开的,可以说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在诗歌圈之外的现实中,我却刻意隐瞒了这个身份,就像灵魂在人群中不轻易外露出来,我把自己视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低调而平稳地生活。这样说并不是强调自我的分裂,而是一种里和外的关系,仿佛与生俱来。
所以在生活上,无论与几个友人喝茶还是在饭局,在别人就诗歌方面夸夸其谈或滔滔不绝的时候,我是不言诗的,即使偶尔涉及诗歌几句也是尬聊。而写诗,那只是在生活之外,在内心隐秘之中。也就是说,读书是占有固定时间,写诗是在意料之外多出来的时间,它可能是白天,也可能是半夜凌晨,仿佛是神不知鬼不觉附上你的身。更多的时候,我是克制着自己写诗的冲动,不去写,也许我需要沉淀,让自己的灵魂再沉淀一点。
我不想再追寻写作的意义,就算我把意义弄明白了又有什么意义。写作即消逝,这本身包括了认识、判断、事后的追忆、色彩、梦、冥想、人与自然、游历、责任、阅读等等。在时间的消逝当中,永恒是不存在的,更多的是谬论、不合情理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得到答案,只能让诗替自己的灵魂说话,在消逝中不断地呈现。换句话,时间上的过去绝不是水流去向的目的,而是处于辗转、衰老的消磨,成为内心缓慢的倾诉,即使倾诉有时是缺陷和不完整的。
5
我不敢说诗为何物,亦不敢说掌握了诗艺的秘密。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自己不断提高一个标准,标准是自我修炼的层次,并达到有效性。这些年,我陆陆续续出版了《少年诗》《一切流逝完好如初》《一首诗的战栗》和《人世很长,人时已远》等诗集,这得益于深圳的吸引力、包容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大的变化就是着迷于诗歌系列写作,从“拟诗记”系列到“剧场”系列,再从“诗”系列到最近的“传奇”和“计划”两个系列,这几个系列意图很明显,就是在写作更新中使我从琐碎化状态脱离出来,也许我会意识到,对于未来的消逝而言,它就是一个漫长而又踏踏实实的写作计划。
我将继续旅程,继续生活。
阿翔作品

《一首诗的战栗》

《一切流逝完好如初》

《人世很长 人时已远》

《少年诗》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