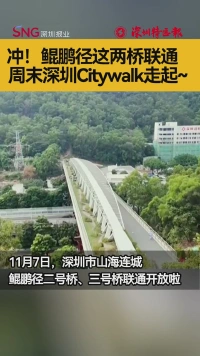经历人间百味,终回四季三餐。《礼记》有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饮食自古以来就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就像淮扬菜,两千多年来在运河边咕嘟着,熬出的不只是鲜香,更蕴含一串串肉食不鄙、口齿留香的千年诗行。
淮安,生来就跟吃有缘。早在距今6000至7000年的青莲岗文化(淮安区境内)时期,出土陶片已出现稻米河鱼的纹饰,有人推断为淮扬菜的源头。春秋时代的吴王夫差挖了邗沟,京杭大运河一贯通,南来北往的船帆成为运河一景,南腔北调的商人挤满了街。千年河下古镇,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两侧酒家林立;河槽盐商的厨房里,大师傅们把寻常鱼虾折腾出花、跃然食案。连《清稗类钞》里记的“满汉全席”,都诞生在南北园林风格兼具的清晏园。
淮扬菜的妙处,全在“讲究”二字。选料用活蹦乱跳的河鲜,刀工要细到能在馄饨(亦称淮饺)上看清书页上的字——就像八字桥震丰园的饺子,皮薄得能透光,用刀背剁出来的肉馅,混着葱姜笋香,汤里是金鱼游水,油里是脆响金黄,难怪人说“过淮不吃淮饺,一趟等于白跑”。火功更讲究,软兜长鱼得用刚出水的黄鳝,大厨“勾火”颠锅,疾秒如风,一气呵成,出锅的美味软嫩得能化在舌尖;文楼蟹黄汤包得趁热咬个小口,吸一口鲜美的汤汁,再就着姜丝慢慢嚼,蟹黄的醇厚在嘴里萦绕,好比诗句里“千斤重的橄榄”,令人“三月不知肉味”。
淮安北部古镇钦工,我曾在那里工作14年。此地藏着会“跳”的美味。传说明清时抗洪,钦差大臣在工地上支起大锅,把猪后腿肉捶得绵密劲道,掺个鸡蛋清,加些绿豆粉,炸成圆子犒劳军民,这便是钦工肉圆的由来。“钦工肉圆撂过墙,拾起还是圆又光,掉在地上跳几跳,吃到嘴里嫩又香。”民谣是这样唱的。这圆子真能跳?一点不夸张,那弹牙的劲儿,确实像把淮河的灵动裹进了肉里。如今镇上的人家,每逢过年、婚寿必上这道菜,一锅清汤煮着,热气腾腾里全是“团团圆圆”的念想。
倘若以为淮扬菜全是荤菜,就大错特错了。淮扬菜素有“一席半斋”之说。西汉淮安籍辞赋大家枚乘在《七发》记载:菜以笋蒲,芍药之酱,秋黄之苏,白露之茹,百种蔬果,园中自植,皆可入席,美不可言。其代表菜品为开阳蒲菜和平桥豆腐。天妃宫的粼粼柔波滋养了肥腴甘甜的蒲草根部,剥至最嫩处,状若碧玉簪。清蒸时,三两虾仁点缀其间,宛如星子落进翡翠盘,一口鲜脆。盐香唤醒豆香,鲜味缠绕古韵,这盅看似朴素的豆腐羹,实则凝聚运河的魂,至今仍在碗里温燠。
一席淮扬菜,鼎鼐四时春。汪曾祺先生谈美食,常说“滋味要正,性情要真”。淮扬菜低调朴实,不事张扬,却把千年的诗、运河的风、家常的暖,炖进一碗一碟中。在深圳的饭馆里遇见淮扬菜,总觉得格外亲切。夹起一根蒲菜,看它在筷子上微微颤动,如见文通的塔影,恍闻运河的桨声,心头会有些许宁静。
我忽然间懂得——所谓美食,不过是把一方水土的记忆,酿成让人魂牵梦绕的味道,无论那记忆是深是浅;所谓乡愁,不过是把漕船晕开的层层涟漪,化为碗底温柔的童话,不论那乡愁是短是长。
编辑 白珊珊 审读 张雪松 二审 王雯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