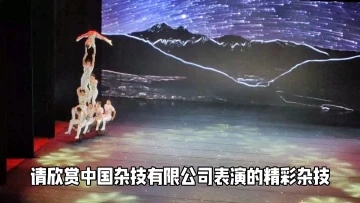■樊林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艺术批评家、策展人

我时常感觉做展览不能一厢情愿,对于板块、场域、作品情境的展开,很值得与大家探讨。我希望把广州三年展的丰富性、可能性放在一个方法论当中,观察四位策展人的工作。
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审美和快感
我到广东美术馆看了两次“广三”的展览,分别是四小时和两小时。观察到尤其在节假日,人们陷入了一种整体性的活动。饮食、文化各方面的消费被标榜为重要的需求,被树立为理想生活的样式。对城市中发生的不同文化事件,具体感受力的显现是复杂而鲜活的,观看广州三年展也就成为一种样式。
当我在西川那件视觉强烈的作品前,希望得到除阅读以外的体会的过程,这时候却两次被一个要照相的女孩拍肩提醒让位。我意识到真正的现实就在理想的对岸,活生生地提示着我。这种陌生感其实是我们过去不太愿意接受的,但是在今天我希望可以讨论,如果日常已经演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制作出一些具有思考、讨论空间的大型展览,意义就是为了指出现实与理想的边界?让现代人在闲暇中找到某种轻松的东西,算不算艺术的其中一个目的?当我们以生产者自居,为艺术生态、创作机制、知识生产不断地绞尽脑汁,这样的观众,尤其是这样的年轻观众,还是给予了我警醒的提示。
我们此刻所面临的是一种后历史语境。某种意义上讲,策展人都是保持着一种学术理想,保持着对文化的思考和批判精神。然而所有艺术史给予我们的、勾勒的展场语境其实基本上已经零散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三年展要包含媒介、艺术、大众、文化、博物馆、全球化、地方性的话,我想我的角度在于,艺术史学者要做的事,是根据艺术在当代的创作实践对艺术和艺术史,尤其是对艺术史提供的话语、框架加以检验。我个人在策展实践中也热衷于此。
当今艺术史其实已成为一面镜子,照见了两种可能的危险,首先是很多时候大型展览有居高临下的空洞设想,尤其在大型城市,因为我们把自己扮演成城市生活文化建设中重要的人,但我坚信广州比其他的某一些大城市实际上更有褶皱,更有历史,更有基础。另一种危险就是日常的书写,尤其是相对年轻的作品可能来自于艺术家对生活特别自我的观察,它们如何被书写为展厅中提出问题的作品。
在这里我借用普桑1638—1640年的作品《随着时光之神的音乐起舞》。画面左边有一个雕像,是古罗马神伊阿奴斯(旧译名为詹努斯),罗马街道、通道和住宅的守护神,可同时看到前面和后面,因此也是始发之神,给一切事业、月份、年头带来好兆头,“一月”就源自詹努斯。因此在所有创造世界的场景当中,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常用他的这一前一后的面孔象征过去和现在。我想三年展就像这种关于时光的预言,共同面对过去与未来,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此刻,把此刻当做终极目标,它才能够留存下来。
当我用这个框架去套四位策展人的作品时,许多问题迎刃而解。比如艺术的独特性,以詹努斯为例,某种意义上它启发我们往回看,我们依然由三年展讨论着艺术的独特性,包括它不说教、要造就一个更高级的善,同时艺术的独特性也在于它的审美、快感。
组织起三年展与历史、现实的对话关系
21世纪早期的展览和讨论,像20世纪早期的展览和讨论一样,可能有一种异质同构19世纪末20世纪初遇世界巨变,艺术状态相应改变。这个时段出现的各种艺术运动,其本身出发点和奋斗目标并非一致,所导致的局面和影响亦然,但在对视觉愉悦方面的强调上都体现出共同的追求,为20世纪人类视觉经历的丰富拉开了帷幕。西方现代艺术起源与后印象派一致,从19世纪80年代前后至20世纪早期,艺术家将自己的思想与快速发展的时代相联系,以期反映与之前的社会生活不同的那些部分。思想、感情或者知觉,都按照艺术家自身的选择和方式得到不同的表达,这样的出发点,决定了现代艺术在不断地拓展内涵的同时扩大了外延。
尤其是战争爆发以及带来的伤害,使得一些艺术家深感于恐惧和痛恨,开始以新的方式表达人类共同的情怀,为争取人权进行新的书写。二战以后,存在主义成为最具影响的哲学,哲学家们希望人们在面对被战火撕裂的欧洲所表现出的荒谬和恐怖时保持正直,强调个体的尊严。存在主义在战后欧洲和美国都形成一种态度,帮助人们认识自己在荒诞世界中的位置。表现主义绘画与其形成的历史环境,是一种“铁与血”的关系。艺术的力量,往往源自这样的关系。
艺术经历了现代、后现代时期,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刻,全球化使得跨国界、跨语际艺术事件时时发生,艺术家之间的沟通明显流畅,各种官方、民营艺术机构致力于构建艺术的、学术的交流平台。多元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交流与影响,使得艺术承载着的人类信仰、创造之重任获得新的理解和阐释。与此同时,新科技拓展了艺术的语言,对过去的艺术传统在观念维度上进行了更新。
回归到作品、现场,我们和观众遭遇“广三”所构建的几重逻辑和问题里,有很多值得琢磨的角度。首先,语境、情境是个最大最重要的问题。在2022年伊始,新一届广州三年展的准备工作,向大家提出了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公共卫生事件席卷全球,影响了二十年来形成的艺术生产机制这样的前提之下,如何再度关注宏观历史问题,深刻地观照现实语境,锤炼出属于第七届广州三年展的具有社会性议题和学术高度的展览方向。
当时我提出,希望以置身于新实验浪潮之中的艺术家、批评家对现实的关联感为前提,将近年来围绕艺术展开的跨学科研究的思想成果与艺术生境相互嵌套,将近现代广东在中国历史、世界版图中的不同角度的重要形象,通过艺术的讲述勾勒出来。从不同的几个方向——诸如海洋文明与社会建设,广东现代化与世界文明的对话,广东人与中国近现代艺术教育,广东艺术家在百年中国历史中的美学贡献等——寻找拓扑点,强调渗透在万事万物中的辩证法,组织起广州三年展与历史、现实的对话关系。新的变化需要大家共同地抱有学术激情,努力地展开深入讨论。实现某种程度上对文化垄断的动摇,扩大和加深广大社会阶层对艺术的兴趣,凸显美术馆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使命和审美取向。所有人都期待新的三年展成为具有新方式新方法的展览,也是一次知识的丰收和一场别致的思维训练。
我们需要花时间谈论,在这个过程中,新科技语言到底能帮助我们什么?所以简单地勾勒从历史到现实的这一场展览的场景,我想提醒各位,尤其是初次到访的观众朋友,这回三年展特别凸显的是美术馆藏品的运用(这也是我的理想之一);艺术史家的进入,书写的意义被提出;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描述”;绘画的本体散发的力量(比如段建宇、钟嘉玲的作品都让我备受鼓舞);展场中的凝聚与消解,普及与深化的矛盾等,都值得我们多加琢磨。
双三年展是城市集体艺术行为
在自然形态之外,人类生活的不断改变往往被纳入合理性之中的进步逻辑。这样的进程中,人的价值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与关系必定密切,每当遭遇社会转型或者急速发展的阶段,这个关系常常被忽略。艺术家用自我的描述重新确认观念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既是使命,也是宿命。城市文化建设的布局中,艺术被放置于上层建筑和审美体验的坐标系里定位。传统与现代,地方与非地方,艺术个性与社会供给,属于矛盾性的变量。社会学框架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更多的希望。将创作始终视为独特的、真正有创造力的劳动,我们就能遇到一些具体的个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坚持着一系列关于人类精神的价值观,关乎真实的生活,不以落后或先进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城市”就是我们的土地,策展人借助“土地”的丰厚资源,勾勒出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行动本身就是博弈。持续多年的数个双三年展,是这个城市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艺术行为。社会议题性作为双三年展的主要思想特征,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当代现实具有的强烈复杂性里,还包含着不确定性和随机现象。策展人与策展人之间,艺术家与策展人之间,观众与作品之间,知识生产与传播之间形成了许多密切的混合。
今天的展厅,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洞穴石壁,相当于巨石阵,描述着最核心、最沉淀的东西。问题始终属于每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愿意留下太多空洞的作品,不希望被以后的人认为我们没有生活,怎么办?在我们无暇沉思的阶段里,借用日常生活来美化日常生活,是不是依然属于艺术的手段?在不断增长的对复杂性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象征城市文化之光的广州三年展,源自构造世界的理智和裹拥世界的感知。其自身的矛盾,在建构一个新时期的文化框架时,导致了许多同时生发的问题和关联。
编辑 陈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