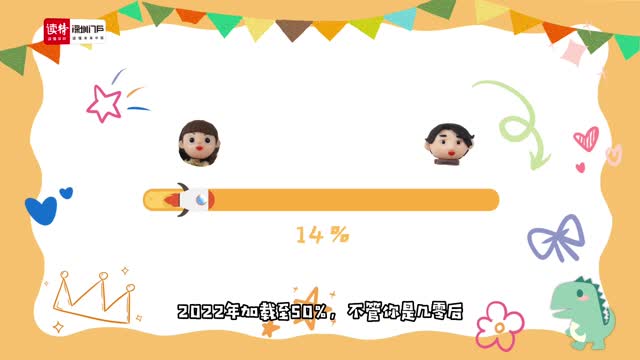“我还年轻,我渴望在路上。”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出版之日就成为轰动世界的传奇经典,其影响力自不必说。鲍勃·迪伦说“它改变了我的生活,就像它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那样。……它像火车一样飞驰而过……你抓住火车,想要上去并随他一起前行,继续这美好的生活”。《纽约时报》认为它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一场颠覆平庸的疏狂漫游,一种永恒炽热的自由声音。《在路上》的故事基于凯鲁亚克和朋友们真实的旅途经历完成,是一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叙述者萨尔·帕拉迪塞是一个对文学、爵士乐、女孩充满兴趣和好奇的年轻作家,他喜欢结交疯狂的对生活充满激情的朋友。通过一个朋友,萨尔结识了生活放浪不羁的迪安·莫里亚蒂。萨尔一直想到西部去,但计划总是一拖再拖,他被迪安自由无拘的生活方式、渴望探索一切的冒险精神和热情所吸引,决定追随迪安“在路上”的脚步,完成西部之旅的梦想,也由此真正开启了通往体验生命以及无限可能的大门。
这部让人热血沸腾的小说被认为是“垮掉一代”的迷惘《圣经》。它关于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将经历的困顿、狂热、孤寂、渴望、恐惧、格格不入、肆无忌惮、动荡不安……每个人的青春里都该有一本凯鲁亚克。
近日,《在路上》首个完整中译本阔别三十年,全新修订,由世纪文景联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加入了详尽注释及作者年谱,以便读者读透作品、作者和时代。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前三个部分讲述萨尔或独自一人或和迪安等几个朋友一起三次搭车或开车穿越美国大陆的旅行;第四部分讲述几人开车去往墨西哥的经历和见闻。他们漫无目的地奔走,在路上体验流浪汉、农民、工人以及其他边缘人群的生活,也沉浸于自然风光的美好,记录下爵士乐时代年轻人眼中的社会风貌。第五部分讲述萨尔从墨西哥回到了纽约,结束了“在路上”的人生阶段,对好友迪安充满怀念。

▲《在路上》(美)杰克・凯鲁亚克 著,陶跃庆何小丽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作者杰克・凯鲁亚克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1922年3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父母为法裔美国人。1939年,他凭借在橄榄球方面的出色表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结识了爱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和尼尔•卡萨迪等亲密伙伴。大学二年级,他放弃学业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当过体育报社记者、商船水手等,还曾进入美国海军服役。凯鲁亚克的创作题材多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1950年,他的第一部小说《乡镇和城市》出版,但并未引起很多人的关注,直到1957年《在路上》出版才使他名声大噪,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跻身二十世纪最有争议的著名作家行列。他还著有《达摩流浪者》《地下人》《孤独天使》等作品。

▲杰克・凯鲁亚克
《在路上》译后记:
陶跃庆/文
五十年代初期的美国,在政治、文化,甚至日常生活领域都笼罩着一种压抑个性的气氛。战后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美国很快进入了大消费社会。与这种安定、富足的日常生活形成对照的是人们精神状态的极度紧张,战争已经结束,但是战争的阴影却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也使得人人自危,对于国家安全的病态担忧夹杂着抽象的道德色彩,不仅毁掉了无数人的一生,也使人无法表达自己对公共生活的看法。人们被迫退回到舒适却单调的日常生活里,成为群体中的一分子,麻木、驯服、没有个性。许多有识之士为此大声疾呼:“当今的时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年代。人们没有勇气,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们把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形象地比喻为“单向度人”(One-Dimension Man)。
到了五十年代后期,“垮掉的一代”率先从实践上冲破了当时的那种麻痹状态,他们是一群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对生活所持的态度,即与社会所公认的一切背道而驰。他们鄙夷那些循规蹈矩以获得社会承认的人,否认传统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追求无拘无束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在路上》集中表达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和态度,因而成为这一潮流的代表作。
作为作家,凯鲁亚克的写作生涯可以追溯到1942年,但直到1950年他才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镇与城》。遗憾的是这部小说没有受到当时批评界的重视。凯鲁亚克几次周游美国,还到过墨西哥。游历生活给他带来无数新鲜的刺激,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951年2月,他仅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在一卷打字纸上完成了《在路上》。1957年,《在路上》正式出版,立即引起震动。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对传统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反叛在战后年轻一代中产生了深刻共鸣。批评界也一改往日的冷漠,称此书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路上》有一种向前直冲的速度感。阅读它就好像是驾驶着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书中那种冲动的活力和狂放的激情不断为你加大阅读的油门,令人欲罢不能。它也展现了一种新的情感和新的生活态度,那就是对现实的背叛以及对实现自我与表达自我的肯定。这些人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投入在路上的生活,以此来表明他们决心逃避或者说退出代表社会的城市,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逃避或者退出看作是对现实社会的绝望或是对未来社会的希望,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社会所不屑一顾的地方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所谓“正常”的生活必须以牺牲个性为代价,政治则仿佛是一场荒诞派戏剧,而那些高雅文化与爵士乐相比简直索然无味。他们向往的是速度,是粗犷的西部,是爵士乐疯狂的节奏,是身与心在迷乱状态下所体验到的激情。指责他们代表了一种颓废的及时行乐是容易的,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充满活力的人生态度。事实上,给他们冠以“颓废”一词是否准确也值得怀疑。首先,在当时那种压抑人性的氛围中,他们的出现本身就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化精神:人们有权在此时此地获得属于自我的个性需求。其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人道主义传统的一次回归。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有这样,人性的潜能才能得到合理的释放。如果我们愿意进一步思考的话,这种行为的背后还包含着一个极为浅显却常常为人所忽略的社会意义:完美的社会正义应当与合理的个人追求相一致。
这部作品对于生活的思考和感受,无疑代表了当时年轻一代共同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我们不妨借用这部作品的名字“在路上”加以概括。“在路上”往往给人一种纵横交错、飘忽不定的感觉,这正是书中所描写的那代人的状态,他们经历了战争与精神上的动乱,抛弃了旧有的社会道德和价值标准,迫切希望用自己的眼光重新认识生活。然而,在菁芜庞杂的社会思潮面前,他们又显得茫然无措。我们将会看到,爵士乐与东方神秘哲学、毒品与存在主义、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与对现代科技成果的崇拜,这些彼此无关甚至矛盾的东西在某些角色身上奇妙地融合。这种思想上的不确定性常常使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出虚幻与骚动不安。然而,“在路上”,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理解,在这无始无终、变幻莫测的漫漫路途上,你永远无法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在他们狂放无羁的举止背后,我们不难体味到一丝悲哀,这是一种人在无法把握社会与自身时所必然产生的悲哀,这种悲哀使书中人物通过性爱、毒品、爵士乐所得到的喜悦中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含义。“在路上”无疑也表现了一种生活的勇气,书中的那些流浪汉们正是在路上建立了温暖的联系,共同逃避城市生活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文明的压力。他们不留恋过去,也不幻想将来,只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从中体会着生活永恒的价值。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成为美国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的先驱。
《在路上》于我而言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1988年4月的一天,当时已经读研二的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翻阅外文书时,偶然发现了On the Road,作为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当然知道这本书的价值和影响,能找到它实在太不容易了,于是赶紧借回宿舍。读了几天之后,就被书里佶屈聱牙的英文吓住了,想着能不能把中文翻译版也借来一起对照着读,结果找来找去,只在《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中发现一些译文片段。忽然之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可以把它给翻译出来呀!
八十年代的大学里,学习气氛非常浓厚,每个人都以发表学术成果为骄傲。当时也有许多年龄较大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就已经颇有成就,我们这些学弟学妹很是羡慕。我有一个同学,王璞,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在入学之前,她就已经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于是我便请教她,是否有出版社可以接受我们来翻译这部书。王璞爽快地答应帮我问问。很快,她便给我回了话,告诉我漓江社的著名编辑沈东子非常喜欢这本书,但要先试译。哈哈!太棒了!试译稿寄出后,焦急地等待了十几天,而后接到了沈东子老师的回信:你们翻译吧!
正好暑假开始了,我与师姐何小丽做了一个分工,她负责第一章,大概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我来翻第二三四五章,基本上是三分之二。我回到洛阳的家中,在炎热的夏天里绞尽脑汁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页一页地翻着。于我当时的英文水平而言,这样的翻译工作并不轻松,但书中那种与我当时年纪正好契合的躁动又强烈的青春激情始终鼓舞着我。那时的我跟凯鲁亚克一样,年轻,充满激情,又体验过抑郁与沉寂,我身上充满了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前几年,有种说法,说我们翻译的是简本或言洁本。要强调的是,我们这个译本当然是全译本!大家或许以为《在路上》这部作品里一定有许多难以翻译的内容,但实际上,当时美国的出版社在出版这部书时,就对书的内容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且对一些可能引起法律问题的描写进行了删改。因此,这部书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些细节。我们翻译的,就是原书全部的内容。何况,以我当时的性格,也根本不会特别去避讳什么。
1988年底,我们将译稿寄到了广西漓江出版社。接下来,写毕业论文、找工作,逐渐成了我研三的核心内容。只是偶尔会写信过去问问情况,回信总说还在编辑中,后来也就渐渐淡忘了。一直到1990年底,我忽然接到了东子老师的信,说书出版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机关工作,赶紧通知了小丽,我俩一起开心了一下,然后也就悄无声息了。因为在机关,你出书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反而会让人觉得你不安心工作。特别是,当我看到书的封面时,吓了一跳。原本是严肃的文学作品,却被加了一个如此香艳媚俗的封面,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本浅薄的通俗文学作品而已。这样封面的作品,如果被我们单位的人知道是我翻译的,肯定也会对我另眼相看。看到封面后不开心的,还有我的师姐何小丽。因为她的名字被印成了“何晓丽”, 至于究竟为何会搞错,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了。好在小丽后来去了美国,在一所大学负责数据库维护,跟文学完全没有了关系,所以也不在乎了。
由于版权的原因,这个译本在印刷了三次之后,就从市场上消失了。当时中国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我们的版权意识也不强,拿到一本书就开始翻译。随着社会的发展,版权渐渐越来越重要,后来出版的几个版本的《在路上》,应该都经过了版权方的确认。不过,我们翻译的这个版本,还是在许多读者心目中有着重要的位置。2018年我去英国旅游,坐车来到了老特拉福德体育场附近一个叫Tabley Superior 的地方。车停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后,我到服务区的杂货店闲逛,远远的,竟然看到了书架上赫然放着一本熟悉的书—《在路上》!三十年前,我翻译完这本书后便远离了文学,三十年后,在旅途中再次与之相遇,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召唤!回到家,我买了一幅美国地图钉在墙上。是的,我要跟着凯鲁亚克一起,再一次横跨美国大陆!我拿出了从前的译稿重新开始校译。
当年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最大的影响,来自于稿费。当时我正准备辞职到南方去,但苦于手头没钱,机关的收入实在太低了,根本无法让我去实现下海的梦想。1991年2月,传达室的同志走进我们办公室,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给你一台彩电!然后朝我扔过来一张纸。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拿起一看,是稿费,竟然有三千六百元!对于当时每月只有一百零四元工资的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笔巨款!我和小丽平分了稿费。然后,我带着一千五百元,辞了职,坐上了南下的飞机。
一直到今天,我都常常会觉得翻译《在路上》仿佛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巧合,因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就如宿命一般,一次次不断在各种道路上奔波。
我与《在路上》的故事,从此又要打开新的一页。
《在路上》书摘:
第一次送别迪安
我们去了纽约。当时的具体情况我已记不清了,好像他约了两个黑人姑娘见面,但一个也没来。他原本和那两个姑娘约好一起去吃晚饭的,然而到那儿却发现她们都没出现。我们就去了他工作的停车场,他在那儿有些活儿要干—他去后面的工棚里换了衣服,又在一面开裂的穿衣镜前整理一番,然后我们就开车离开了。就在这个晚上迪安和卡洛•马克斯会面了。迪安和卡洛•马克斯的相遇是一个伟大的事件。两颗敏感的心一碰撞便立刻互相吸引,两双敏锐的眸子一相遇便立即迸出火花—一个是心胸坦然的神圣骗子迪安,一个是心灵幽暗带着悲观诗人气质的骗子卡洛•马克斯。打那以后我就很少见到迪安了,为此我感到有些伤心。他们精力相当,相比之下我就像是个傻子,跟不上他们的节奏。接着,我周围的一切,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像尘云一样被一个疯狂的漩涡卷起,在美国的夜空盘旋。卡洛给他讲老布尔•李、埃尔默•哈斯尔、简的故事:李在得克萨斯州种大麻;哈斯尔在赖克斯岛 ;简曾经在时代广场徘徊,沉浸在安非他命带来的幻觉当中,怀里还抱着自己的小女儿,最后去了贝尔维 。迪安给卡洛讲西部那些不知名的小人物,比如汤米•斯纳克,一个畸形脚的台球厅狠角色、玩牌好手、同性恋者,还给他讲罗伊•约翰逊、大个子埃德•邓克尔,讲他儿时的伙伴、流浪时的伙伴,还有他遇到的数不清的姑娘,他的性伴侣,色情电影,以及他所崇拜的男英雄、女英雄,他所经历的冒险。他们一起冲上大街去追寻、体验那些有趣的事,不像两人后来的交往那样悲伤、多思、空洞虚无。然后他们就沿街跳舞,就像我喜欢的那类人,我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我一生都喜欢跟在令我感兴趣的人身后,那些有点疯狂的人,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表达,疯狂地渴望被救赎,同时渴望一切,不知疲倦,不落俗套,他们不停地燃烧,燃烧,就像惊人的能连射的黄色烟火筒迸发,如蜘蛛穿过星际,在天空中央你会看见蓝色的中心光点砰地爆裂,所有人都不禁惊呼。歌德时代的德国人怎么称呼这样的年轻人呢?由于渴望向卡洛学习如何写作,迪安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感情攻势,只有骗子能做出来的那样。“好了,卡洛,让我说,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们,而这期间他们的友谊极速加深,没日没夜待在一起聊天。
春天来了,这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们三三两两地组织起来准备出去旅行。我一直忙着写我的小说,在我写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在我和姑妈从南方我的哥哥罗科家回来后,我就准备出发开始我的第一次西部之旅了。
迪安已经走了。卡洛和我去34 街的灰狗巴士站为他送行。车站的楼上有个地方付二十五美分就可以拍些照片。卡洛照相时摘下了眼镜,看上去十分凶恶。迪安拍了张侧面照,显得有些害羞。我拍了一张正面照,看上去像个三十岁左右的意大利人,似乎谁要冒犯了他母亲,他就会将那人杀死。这张照片被卡洛和迪安用剃须刀片整齐地从中间切成两半,一人留了一半在钱包里。迪安穿着一套正宗欧陆风格的西装踏上了重返丹佛的伟大旅程,他在纽约的第一次风流之旅就这样结束了。我说他风流,其实他只是在停车场干活,累得像条狗。他是世界上最棒的停车场员工,他能将汽车以每小时四十英里的速度倒进墙边狭窄的车位,然后越过众多的障碍物,跳进另一辆车,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在拥挤的空间里绕圈,再迅速倒入一个狭小的车位,一个急刹车把车停住,你能看到当他跳出车子的时候那辆车弹了一下。然后他会像田径明星那样迅速跑向开票处,开好票,再向刚驶来的另一辆车跑去。车主才出来半个身子,他就已经钻了进去,门还没关上就启动车子,在一阵咆哮声中将车开向了另一个车位。弯腰进车,启动,刹车,从车里出来,跑步,他就这样马不停蹄地干着,晚上八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夜晚的高峰期,或是剧院散场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穿着一条沾满油污的破裤子,一件磨坏了的皮夹克,一双破烂不堪的鞋子。如今他却在第三大道买了一整套崭新的西装,蓝色带条纹的面料,还包括一件西装背心,一共花了十一块钱。他又买了一块表、一根表带、一台手提打字机,一旦在丹佛找到工作,他就要在他租住的公寓里开始写作了。我们在第七大道的瑞克饭店吃了香肠配豆子作为告别宴。然后迪安搭上一辆去芝加哥的巴士,呼啸着消失在夜幕中。我们的牛仔走了。我对自己许诺等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的时候,我也要沿着和迪安相同的路线到西部去。
我后来的整个旅行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以后发生的一切简直精彩得难以言表。
(晶报供稿)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