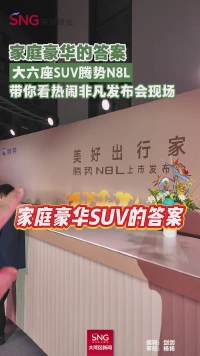先给一个判断——无论从商业选址还是场景打造、IP营销,深圳文和友的第一步都是成功的,在深圳传统商业街区——东门尤其如此。
深圳文和友开业进驻东门两个月,不仅丰盈了东门商圈的商业形态,提升了罗湖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的维度,而且给众多商业综合体提供了自我审视的一面镜子。相信文和友所带来的多种视觉IP冲击给了许多商家诸多启示——原来商业和文化还能如此跨界和互动。
【一】
东门,深圳商业的发源地,中国大陆第一家麦当劳即诞生于此,其商业形态一直是深圳最为丰富的地方,尽管如今停车并不方便,但较早接入的地铁网络使东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人气。
东门短板也是明显的:整个片区商业氛围比较传统,更新进展不快。商业形态虽多,但呈现小散状态,缺乏鲜明主题。自2001年东门进行大规模改造之后,整体变化不大,且商业热度从未越过广深铁路以及和平路以西,乃至于茂业奥特莱斯也是独居一隅,与东门商圈产生了明显隔断。
但深圳文和友的到来,改变了这一格局。
文和友在选址上是独到和老辣的。文和友原来所在的物业正是以零散门面的方式对外招租的,几乎是一处可以被遗忘的商业存在,但这恰是一块相对独立的完整空间——位于广深铁路、布吉河以及解放路所合围的三角区域,河道、桥洞以及铁路上所穿梭的动车和绿皮车,使之具备了动静相宜的各种再造可能。深圳文和友在外形气质上与东门老街实现了呼应,在商业上与对面的茂业奥特莱斯形成了互补,加上地铁老街站所带来的客流便利,深圳文和友具备了地利与人和优势。

深圳文和友以一栋“深圳墟”为载体,以迷幻、科技、复古又富有未来感、强烈色彩为核心的“Y2K”美学为理念,打造了既不同于传统餐饮,又迥异于商业综合体的餐饮主题场景——它几乎以“躺平”的方式解构了此前致力于高大上的综合体模式化通病。加上科幻屏显的演绎与光怪陆离的艺术装置,使之呈现一种类似于《功夫》猪龙城寨的密集虫洞视觉冲击波。用文和友的话就是,通过不同的业态来进行内容活化,满足人们吃饭、拍照、购物、游玩、泡吧甚至看剧等不同需求,从而逗留更长的时间。
在主打餐饮项目上,深圳文和友在本市和本省进行了不少发掘。远在深圳东西部的网红品牌——老地方盐田肠粉、邓家传文糕点和光明乳鸽都被搜罗进来,而此前到处打游击的“小罗臭豆腐”也被固定下来,大大节省了食客们的时间成本。来自长沙、广州、汕头和澳门的美食,则大大延展了吃货们舌尖味蕾的多样性。至于擅长于饥饿营销的茶颜悦色,则是文和友吸引客流、聚集人气的一张底牌,以至于位于华润1234space和茂业奥特莱斯的两家喜茶店的火爆生意都受到了明显冲击。
【二】
即便如此,深圳文和友的Bug又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里缺乏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的深圳关键元素,更缺乏那个年代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内核并非旧式的物件器具、文字招牌在一个仄逼空间的密集堆砌就能呈现的。
依照个人观感,深圳文和友更像是长沙+深圳+香港餐饮文化的一个杂糅。其所展现的深圳,代表性明显不足。这里顶多是文和友团队所想象和演绎的深圳,而非那个年代真实的深圳。即便是创作团队所设想的“深圳墟”形象,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所自带的先锋气质亦相去甚远。

在深圳文和友里,分别设计了“东门肉菜市场”和“东门游戏厅”的场景。事实上,将这些招牌的“东门”换成“长沙”乃至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同样成立。有心人甚至考证出里面的公交站牌是北京的拷贝,而非当年深圳的样式。这一细节败笔无疑令人尴尬,亦非关键所在。其最大的问题是,深圳文和友的场景固然炫目,但所有呈现并没有体现出那个年代深圳的独特性,尤其是时代性。因此,整体场面固然喧嚣,但很难让人走心和共情。
当年,二线关、流水线、安置区和收容站都是深圳人最为深刻的印记。而在招手即停的中巴上“有落”和“猫低”则是上班族最先学会的口语白话。这些带有深圳特征的连接点和关键词在此都难寻踪迹,使得深圳文和友更像是一个充斥着消费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道具影视基地。
一个最为突出的例证是,“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出现在了深圳文和友一处昏暗的地下空间里。当你看到这句口号时,与它在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和广东改革开放40年展览馆里所呈现的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后两者所带有的振聋发聩以及只争朝夕的时代感、紧迫感是前者所没有的。或许因为时间以及功力问题,文和友创作团队没有能get到深圳之根和深圳之魂。就像那张“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的照片里,当年的主人公衣着可能会变旧,但他们脸上所闪耀的自信光芒和时代梦想永远不会褪色。这正是深圳文和友有所缺憾的主要体现。
更重要的是,当年轻的90后、00后在此打卡持续传播之时,将使更多的年轻人误以为,这就是当年的深圳以及深圳内核。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现象值得深圳本地文创工作者反思:因为我们没有拿出更好的产品,最后只得由来自长沙的文和友“定义”和“书写”了当年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深圳。这与主打怀旧风的北京“和平菓局”、上海“1192弄”以及武汉“知音号”的模式还有本质区别,毕竟深圳的历史太短了——这是市场给我们的深刻教育。因此,深圳文和友有着极大改善和完善的空间。
【三】
与开业之初动辄数万人排号入场相比,眼下的深圳文和友正在回归常态。
当初为了客流有序进入,有关方面为文和友在布吉河边设置了一条长长的回形入场通道。这在客流高峰期当然是必要的,但在平峰期,依然让顾客绕场一周就实无必要。即便是网红打卡地,也要为顾客着想——在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永远成立。

从更长的时间来看,深圳文和友最终成功与否,还要回归于商业本身——即能否迈过消费者复购这一关。长沙文和友植根于厚重的小吃文化以及休闲文化土壤之上,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此方面,深圳尚需市场沉淀和持续探索。从“时空剥落”艺术装置在内外空间的展现以及沉浸式戏剧《绮梦》的排演来看,在商业模式之外,深圳文和友显然有着更大的文化追求和抱负。于此,都需要时间来验证。
(原标题《“文理财经”第③期|场景逆袭,深圳文和友的Bug在哪里?》)
编辑 陈晓玲 刘彦 审读 吴剑林 审核 李林夕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