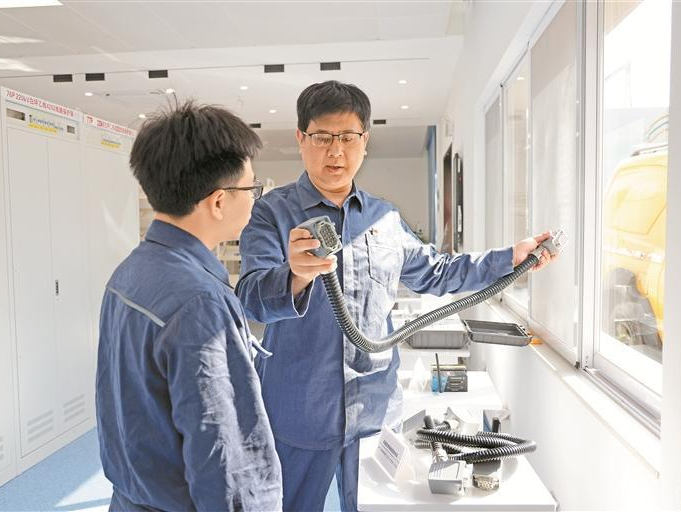逄维维/文
23岁那年夏天,我攥着毕业证站在罗湖火车站。出站口的人潮像刚开闸的洪水,全是年轻蓬勃的面孔,个个手提肩扛,形色匆匆里透着股意气风发。那时的我,就像迎接我的风,浑身热气腾腾的。白裙子被汗水洇出圈圈湿痕,心里的热情却像刚煮开的水,咕嘟咕嘟直往外冒——满脑子都是“闯深圳”的念头,我一头扎进了找工作的人流里。
第一份工作在南山的工厂当质检员,天天跟海飞丝瓶子打交道。夜班的流水线被灯光照得发白,我负责抽查从传送带上送过来的堆成山的瓶子。看瓶身有没有气泡、划痕、毛刺、变形或者色差,就像玩“找茬”游戏似的,连瓶身LOGO印得清不清、色彩是否均匀、边缘会不会模糊都得仔细看。还要检查瓶盖能不能拧紧,会不会漏液,不合格的就挑出来扔进废料筐。这活儿没什么技术难度,就靠眼尖、手稳、有耐心,还有股子对“合格”的较真劲儿。
最难熬的是凌晨两三点,车间里只有机器嗡嗡的响声,困得眼皮直打架。带我的大姐把风扇开到最大档,说:“熬不住就喝点浓茶。”可我实在受不了这昼夜颠倒的日子,更怕家里人问起我的工作,总觉得拿着父母从庄稼地里刨出来的辛苦钱换来的毕业证,干这活有些亏得慌。才干了一周,工钱都没要,我就跑了。
后来进了家香港老板开的公司。面试时他说会送我去学报关,考报关员证,听得我眼睛发亮,觉得总算能学个真本事。结果呢?天天不是填各种表格做准备工作,就是往蛇口代理报关行送资料。要么排队,要么帮老板订票、接送人、办执照年检。有次暴雨天冲进办公室,看见穿裹臀裙的同事正端着咖啡优雅地从我面前走过,她们指甲上的蔻丹红得像樱桃,而我头发上还滴着雨水。我每天都是灰头土脸、汗流浃背地跑来跑去,很少能像她们那样,穿制服、蹬高跟鞋,优雅地走在地毯上。
半个月过去,一个月过去,老板再没提过送我去学习的事。那天我忍不住问:“啥时候送我去学习啊?我到底算啥岗位?”老板笑着说:“你就是文员,不过是‘跑腿文员’。”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么个岗位,一头雾水的我,躲在楼梯间偷偷抹眼泪,心里直嘀咕:这活儿要什么学历啊,我这大学不是白念了嘛!越想越憋屈,干了一个月,拎起包又走了。
父亲总嘱咐我:“不管干啥工作,都得学真本事。”后来我进了家日企,招聘启事上面写着“不看学历,不看专业,只要人品过关,愿意从头教”。面试我的是财务经理阿平,第二天就喊我来上班。他从阿拉伯数字怎么写进账本格子教起,讲借贷方怎么分,讲每个会计科目怎么用,从票证整理到做账逻辑,一步一步带着我。最让我过意不去的是,白天工作很忙,他多半是下班后,骑半个多小时自行车到我住处来上课。
有次刮台风,雨点子砸在窗玻璃上噼啪响。他推门进来时浑身湿透,怀里却紧紧揣着用塑料袋包好的会计书。我心疼得直劝:“平哥,太麻烦你了,这么大的风就别来了。”他擦着眼镜笑:“不麻烦,学会计就得下笨功夫。”
学了大半年,正准备考会计证,领导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说:“你看阿平这人多好啊,还单着呢,你还考虑啥?公司给有家的员工解决住房,这政策错过可就没机会了,你俩……说吧,回家领证得多长时间,我给你批假。”
有次我算错了账急得掉眼泪,他突然翻出结婚证晃在我眼前:“你看,我们结婚了,得分享夫妻共同财产,那眼泪是不是也得分我一半?”他接着说:“我早把你记作‘长期应付款’了,得用一辈子还。”后来我才发现,他教我时总藏着小秘密。“借和贷永不分离。我想做你一辈子的借方,你就是我的贷方,我给一分真心,你就多一分惦记。”他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把我从‘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最浪漫的事,就是和我一起折旧,慢慢变老。你是我长期的股权投资,我是你的实收资本,我会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咱俩这账啊,得算一辈子。”
谁能想到呢?那年夏天罗湖站出口的风,工厂夜班的风、台风天的风、写字楼里穿梭的风,都把“有借必有贷”吹成了“有你必有我”的“爱情合并报表”。厨房里,阿平系着围裙喊我吃饭,抽油烟机的嗡嗡声里,还能听见他哼着当年教我的会计秘诀,早就成为通往柴米油盐的爱情专属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