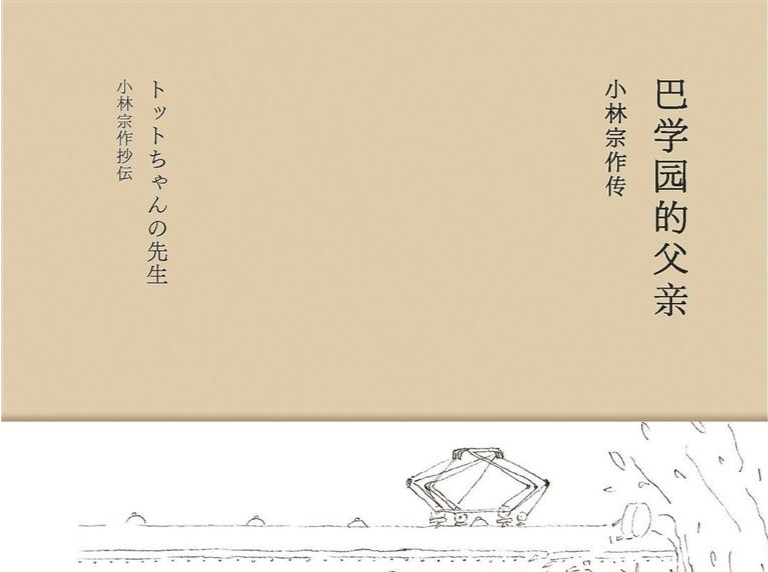《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 董铁柱 著 中华书局 2024年4月版
《谎:<吴越春秋>里的忠与谋》是一本讨论说谎的书,更是一本讨论《吴越春秋》的书。从头到尾,我们的目光都聚集在一个词——“说谎”,与一本书——《吴越春秋》之上。我们说的“说谎”并非世俗意义下的说谎,而是一种叙述方式,即凭借故事叙事所具有的内在意义、张力和跨越逻辑陈述直达思想主旨的叙述方式,我们希望以此为解读古代典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直以来,大众多认为《吴越春秋》的主旨在于讲述吴越争霸中的起起伏伏,其中尤以伍子胥的复仇与越王勾践的称霸为最。不过,一位汉代的儒者讲述几百年前的“故事”,真的只是为了让读者了解那一段历史吗?他究竟有没有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与哲学思想的反思,而希望通过“故事”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呢?
相信在看似纷杂的叙述中有一条主线,是相信先秦以来的思想家们在讲故事的时候都不只是为了讲故事,他们讲故事都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赵晔当然也不例外。不同的无非是在孟子、庄子、韩非子的眼里,故事更多地处于配角的地位,他们在讲述思想的过程中夹杂故事,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在赵晔的笔下,故事本身已经成为了主角,或者可以概括成一个观点——“故事即思想”。在没有用其他笔墨明确阐述思想的情况下,故事本身就是思想的载体,而思想则是贯穿整个故事细节的主线。故事——也就是“虚构性历史叙述”就这样与思想合二为一。
从广义来说,“故事即思想”这一命题试图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新的思路。根据葛兆光所说,中国古代思想家讨论的焦点主要有五个:第一是有关世界的观念,第二是有关政治的观念,第三是有关人尤其是人性的观念,第四是有关生命的观念,第五是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框架的观物方式。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界定与中国哲学的内涵并无二致。因此,在这里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基本是一对可以互换的概念。我们一方面说“故事即思想”,而不是“故事即哲学”;另一方面又强调“故事即思想”,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来说可能是一条新路径。这也是为了强调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的互通性。
“故事即思想”的观点事实上古已有之,明末清初的著名才子金圣叹就认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充满了“神理”,把它视为一部“格物”之书。金圣叹明确指出,圣人用六经传道,而庄周、屈原、司马迁和杜甫等人虽然不及圣人,但具有各自之才,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传道。他们充满了文学性的文字——无论是寓言、史传还是诗歌都蕴藏着道理。这些道理实则源自六经,只不过六经出自圣人之手,而后世之人则根据自己之“才”而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表述方式。在他看来,《水浒传》也正是这样的“文章”,并赞叹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金圣叹的论断看起来非常奇特。在通常的观点看来,施耐庵是一位小说家。在现代学科的分野下,几乎没有人把他视为哲学家或是思想家。与此同时,庄子是哲学家,司马迁是史家,而屈原和杜甫是诗人。他们这几位的身份是如此得不同,似乎怎么也无法被归为同一类,尤其是屈原和杜甫,很难想象他们被贴上思想家的标签。金圣叹把施耐庵和他们四位列在一起自有他的原因,觉得他们都继承了《论语》的叙述手法。可以说,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解读与定性中就蕴含了“故事即思想”的观点。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将《吴越春秋》中的故事视为赵晔思想的载体是对金圣叹的一种模仿。这样的模仿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掘吴越争霸背后所隐藏的赵晔的思想,更是为了希望复兴“故事即思想”的观念,从而真正地从中国文化的特性出发思考中国哲学。劳思光在其《新编中国哲学史》序言中说:“哲学史的主要任务原在于展示已往的哲学思想”,那么哪些才属于中国“已往的哲学思想”,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探讨的问题。“故事即思想”,意味着文学和哲学之间没有界限,合二为一;意味着哲学可以通过迂回委婉的方式表达,而不一定要采取直接论证的方式。或者说,迂回表达和直接论证都可以合理地阐述哲学思想,两者并没有必然的高下之分。哲学家会根据自己的才性和喜好选择一种表述方式。
不少外国汉学家也将传统意义上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视为哲学家,并将他们的作品视为哲学文献。例如罗秉恕(Robert Ashmore)将陶渊明的诗作视为对《论语》的注释,把陶渊明视为一位魏晋之际的儒家思想家;而胡明晓(Michael Hunter)则认为《诗经》是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对先秦以降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深远影响。在胡明晓看来,奠定中国人世界观的是《诗经》而不是诸子,因而他指出从文学作品才能发现中国哲学的传统。
因此,当我们说《吴越春秋》是两汉到魏晋之际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赵晔是东汉不可忽略的哲学家时,并不只是想为《吴越春秋》和赵晔正名,更是希望包括“虚构性历史叙述”在内的众多“文学性”文献能够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史料。正如胡明晓所言:“把诸子视为早期中国思想的主角是晚近历史发展的结果。”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为了找到能与西方哲学相抗衡的“中国哲学”,将注重直接论证的诸子学视为早期中国哲学的核心,并按照这个标准选择了两汉以降的中国哲学家。从《吴越春秋》出发重新主张“故事即思想”,重新找回中国哲学的特质,唤起中国哲学的自我认同,可以更为合理地梳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这并不是想要否定诸子以及其他现已公认的古代哲学家们的价值,而是为了肯定更多尚未得到重视的古代哲学家们的价值。
赵晔在讲述吴越争霸之时,讲的正是他的哲学思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样的思想表达方式视为一种“说谎”行为。这是一种不具有“欺骗性”的“说谎”,就好像古公与太伯父子之间的“谎言”一样。这种“说谎”就是为了等待能够“知”的人来领会。在金圣叹看来,施耐庵用的也是这种“说谎”方式,他用讲述梁山“好汉”的故事来阐明忠恕之道理。不“知”施耐庵用心的读者“犹如常儿之泛览者”,会误以为他在宣扬“杀人夺货之行”;正如有的读者会以为赵晔在赞扬伍子胥的复仇或是勾践的称霸一样。我们将“说谎”视为《吴越春秋》的主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赵晔的哲学思想,就是想表明这种解读是可能的,不过,这种可能也不是唯一的可能。一种委婉的叙述注定有多种的解读方式,这正是作者与读者、言者与听者之间博弈的魅力所在。
编辑 秦天 审读 匡彧 二审 王雯 三审 上官文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