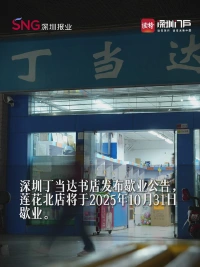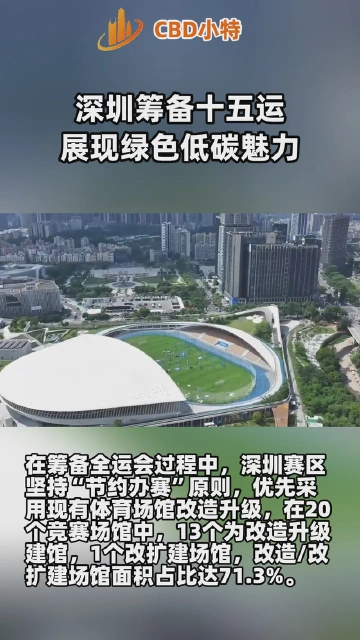□ 包胤彤
【摘要】本文以叶姆斯列夫的语言符号模型为基础,探讨在索绪尔能指-所指二元模型下,如何解释表情符号的意义生成方式。研究发现,对能指形态的拓展定义,可以解释非语音符号标记的文字意义生产过程。表情符号作为字词的替代,其功能依旧没有脱离能指-所指的框架,只是为这一意义产生形式带来新的表现方式;同时,表情符号特有的不确定性,成为其文本应用的局限。
【关键词】网络语言 表情符号 符号学 索绪尔理论
网络语言是语言形式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从简单的缩写、谐音,到“火星文”、数字文、表情符号、表情动画等,互联网沟通语境成为新语言符号的试验场。
本文的理论线索以索绪尔为起点,介绍了叶姆斯列夫对索绪尔理论的拓展,以及符号学家达内西对表情符号的符号学讨论。表情符号在何种条件下符合索绪尔系统下对语言能指的理解,是问题的关键。
一、表情符号给文字加上表情修饰,以视觉联系字词传达意义
表情符号首先是作为一种书写符号存在的,因此讨论表情符号无疑要涉及语言学上的根本性问题:口头文本(oral text)和书面文本(written text)的关系。西方哲学史上倾向于认为口头表达是更加切近真实语言的文本状态,而文本不过是对口头语音信息的记录。这种观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确立为主流的语言观;而欧洲语言由古典希腊语到中世纪学术界通用的拉丁语,直至近现代各国的民族语言无一不是表音文字,即文字书写字音。因此索绪尔等现代符号学先驱以语音而非文字符号作为研究切入点,是顺理成章的。符号学的发展又必然要克服这种语音至上主义:表情符号这一非语音符号列入研究客体,也是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充分拓展了符号的定义之后。
表情符号在英文中称为emoji,源于日语词“絵文字”。它兴起于1990年代后期的日本,界面设计师栗田穰崇被认为是开发出当下意义表情符号之第一人。[1]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早期,网络聊天催生了快速打字法,以及省略语和表情用语。在视频传播尚不方便的年代,互联网用户钟情于能使对话变得生动活泼的简易情绪符号。在文字中穿插一些这类符号,结果是让文字超越字面本身表意的符号功用,而达到类似真实的面对面聊天效果。表情符号通常由人面部的不同表情图像构成,阅读起来如看见说话人的面容变化。另外表情符号可以根据日常生活的事物绘制,比如太阳、花朵等等。用绘图表示本应由文字词语表述的概念,使得穿插表情符号的句子在表意上呈现出不同形态,进而跳出了“字符-字音-概念”这一传统序列。社会调查显示表情符号由它的发源地日本,迅速蔓延至整个互联网世界,并在2010年前后成为全世界网民普遍接受的表达工具。[2]
表情符号在互联网这一最活跃的信息平台上的广泛使用,被符号学家认为代表文字发展的革命。麦克卢汉把人类文明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由象形文字向表音文字的转化,理解为认知模式上的范式转移:基于字母的表音文字允许人们把文字广泛运用在各种生活场合,成为商业生活和城市化进程的催化剂。从某种程度上说,从象形文字到表音文字的转变,标志着人类生活模式由部落制到文明国家的转变。[3]表情符号是基于符号形象的指示表达,在形式上模仿图像,并不带有语音含义。表情符号在文字中的应用打破了文字符号在文本中的垄断地位,使文本变成文字符号与图像符号的混合体。可以说表情符号是给文字加上表情修饰,它们的意思不是通过语音再现,而是通过视觉联系话语字词实现意义传达。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提出“显说性功能”(phatic function)是人类语言的底层功能之一,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克布森进一步把显说性功能理解为与表达性沟通并列的一种语言形式,或者说是一种“后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当一个人尝试吸引对话伙伴的注意力,或者表示自己在听对方说话,此时的语言就具有显说性。[4]加拿大符号学家达内西(Marcel Danesi)认为表情符号在文字中的作用,首先在于构建类似显说性语境的“细微语境”(small talk),通过拉近与谈话对象的距离而使沟通过程更愉悦。其次,表情符号的表达方式是“动情式”(emotive)的——借用这一雅克布森的术语,达内西认为图像形态的符号,能增进使用者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能力。
二、网络表情符号颠覆索绪尔理论中能指-所指演绎关系
表情符号对索绪尔体系的冲击,在于其颠覆了整体语言中能指-所指的演绎关系。文本语言的意义依赖于符号与意义之间的稳定联系,而这种联系在加入表情符号后有可能出现实质的改变。在完全由表情符号构成的交流中,符号本身仅仅起到形象化的暗示作用,而并非被诠释为词语所代表的固定词义。表情符号的排列顺序构成了由形象化符号表示的意义流,意义的排列方式以情节(episode)的方式出现,即表情符号暗示出动作的先后次序。在以下图例中,对话人甲意图逗引对话人乙抢劫银行:[5](图1)

图1 “兄弟,咱们抢银行吧”
对话人乙首先回复“枪”“钱袋”“车”三个符号,表示与“抢银行”这个动作有关的三个事物,并回复笑脸,表示此时的心情。随后对话人乙打出四个警车的符号,表示警察出动,附带的表情为吃惊。之后对话人乙回复四个“枪”符号,一个囚车符号和一个救护车符号,表示警方的武力强大,并逮捕劫匪,或出现劫匪伤亡;最后给出的两个表情为震惊。乙的表情符号形成三个叙事序列:1)劫匪持枪抢劫,2)警方出动,3)警方动用武力制服劫匪,后果是被捕(警车)或受伤(急救车)。这一叙事并非表明说话人态度,而是指示出行为发生的顺序过程。甲并未理解乙的态度,才会用文字向乙确认。对话人乙全程使用表情符号,并且没有表达任何态度,因此在这一例子中,表情符号只传达特定语境下的动作情节序列以及说话人情绪。
表情符号的引入与文本的“去文字化”同步。带有表情符号的文本在表意上,倾向于回到前字母文字的象形化、拟物化特点。[6] 索绪尔在《教程》中探讨的符号基于文字表达,很难用于分析带有表情符号这种非文字符号的文本。相关的所指-能指内涵需要重新审视,而叶姆斯列夫把符号系统限定在特定语言环境的假设,无疑有利于在索绪尔传统下找到表情符号的符号系统含义。
三、不存在纯粹的、完全独立于情境的符号
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被认为是欧陆符号学鼻祖。索绪尔提出的诸多范畴——比如能指-所知(signifiant-signifié)模型,语言系统,符号能指的随意性,整体语言-群体语言(langue-langage)的区别等等——一直是法国、东欧等地符号学家思考的基石。路易·叶姆斯列夫(Louis Trolle Hjelmslev, 1899-1965)是丹麦语言学家,哥本哈根学派创始人。叶氏以索绪尔的继承人身份自居,并且进一步把索绪尔理论的贡献归纳为对语言进行“结构化”思考:用象棋做比喻,假如说索绪尔之前的语言学只是研究象棋的历史,棋子和棋盘的材质工艺,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则是棋位、棋局。叶姆斯列夫把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改称为“内容”(content)和“表达”(expression),并提出了“语符学”(glossematics)概念,把研究对象拓展到经典的语音和语言替代品——文字文本以外。
Glossa一词最早为希腊语,表示“舌头”,进而引申为“人声”“语言”。拉丁语作家往往用glossa一词指代词汇,尤其是艰难的、待解释的词汇。叶姆斯列夫在索绪尔符号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本身可被分解(decompose)并且符号具有复合特征这样的假设。[7]在代表作《语言理论序言》(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里,他提出要把语言学研究从一种辅助性的地位,提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语言学必须成为一个自洽的总体,它需要有一个自源性(sui generis)结构,而不依赖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8] 索绪尔强调的是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总体(relata),这是语言学的本质研究对象;在这一层次以下是语音学和语义学,它们同样通过研究符号能指与意义的关系,在次层面支撑“语言”(langue)这一庞大的表达系统。叶姆斯列夫同时指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可以拓展成一种超越个体语言系统的普遍意义符号学说,即符号学(semiology)。
叶姆斯列夫继承了索绪尔符号学的基本前提,比如说符号系统通过能指表达意义,以及内容与表达之间具体的指涉关系这一学说。语言与符号系统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关系:一方面,语言符号——包括语言、文字和其他丰富的语言表达形式——具有场景性,这表现为任何符号都需要具体场景作为诠释依据。叶姆斯列夫认为不存在纯粹的、完全独立于情境的符号。对一个丰富的符号系统做诠释,即人们生活在这个系统中,能通过符号“意会”到符号背后的意义,就需要符号与内容之间有某种稳定的联系,叶姆斯列夫称之为“恒常性”(constancy)。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符号系统,这表现在语言中用作能指的符号本身也可以是复合的符号结构。每一个语言符号单独来看,都是由更小的元素组成的,这些元素的结构对这一语言符号有诠释意义。这些语言符号内部的元素,被抽象地称为“形貌”(拉丁语figura,复数figurae)。语言的内部结构正是由这样的形式通过一定序列构建的。[8]
以此为基础,叶姆斯列夫拓展了索绪尔的符号诠释模型。他接受了索绪尔模型的基本假设,即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其中包含所指和能指,并具有系统自洽性;所指和能指各自处在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中。在叶氏模式中,“表达”和“内容”两个范畴又与另外两个范畴相联系,即“实质”(substance)和“形式”(form)。这样总共有四个概念范畴:表达的实质,表达的形式;内容的实质,内容的形式。叶氏称这个体系为“符号学系统的层级化”(la stratification du système sémiotique)。[9] 实质-形式的对立是为了回应索绪尔《教程》中对符号任意性的假说。不同的语言中,词语概念对应的实质不一样,这表现为对应词的形式差别。
举例来说,对于“树”这个概念,丹麦语用træ,skov,德语用Baum, Holz, Wald,法语用arbre, bois, forêt,这里每一个词所对应的内容实质都是独一的,无法与其他语言中的某个概念完全等同。[8] 但是“实质”在这些例子中又不能被直接体会感知,而是需要借助“形式”的躯壳才能体现。“实质”是语言交流的意义(purport)指向,它自己确实是一种无形的连续体。语言符号在沟通中通过整体语言(即索绪尔说的langue)的结构,进而表达出深层的意义。
在网络语言里,新符号的使用无疑是叶姆斯列夫理论的一个绝佳例子,并且牵涉到叶氏理论的两个看似矛盾但实质统一的关键点:1)符号系统本身作为整体语言(langue)的组成部分,本身需要恒常性,否则无法实现沟通;2)符号系统内容与表达之间的联系是随意的,并且内容与表达自身是两个独立系统。表面上看,表情符号不是一种随意的符号,因为它们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图形本身展示的表情意义,比如各种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等。然而这种看似唯名论式的符号,可以通过与文本的表达串联,转化为文本符号。叶姆斯列夫举例认为,英语词“in-activate-s”包含了不止一个符号元素,而前缀“in-”,词尾“-s” 虽然不是独立的词语,但是构成符号意义的组成部分。语音与意义之间的联系需要经过诠释,而语音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意义。[8] 表情符号串联在文句中,实际的作用相当于特定的词语或短句,也就是参与其他词语或句子构成复杂符号。或者用叶氏的术语来看,表情符号本身无法形成准确的文句,而是通过给文字文本赋予形貌(figura),进而参与表达内容。
四、叶姆斯列夫为表情符号的符号学意义奠定基础
索绪尔-叶姆斯列夫二元符号学分析模型,始终把内容放在所指-能指的二元框架中看待,这是该模型有别于其他分析框架,比如说皮尔士的三元分析模型的特点。然而这一模型的提出者索绪尔把能指的范围局限在语言上,并且尤其强调字词作为能指的作用。如达内西指出那样,索绪尔并非没有注意到非字词的能指,比如说索氏提到了拟声词的能指作用,并暗示作为能指的元素并非一定是字词的语音,在他的符号理论里始终把这种情况视为例外。而表情符号是由图像所组成的,本身不具备发音和音素这些能产生声学印象的元素,不在《教程》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叶姆斯列夫对索绪尔符号模型的拓展,为讨论表情符号的符号学意义奠定了基础。达内西认为符号可以包含从语音、文字、文本到图画、小说、数学公式等等。有的符号内含大量的子元素,被称为“大符号”,比如一本小说、一个等式等等。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文本”(text),是因为它包含可被诠释的内部元素;文本所对应的所指,被称为“消息”(message)。[1]
在表情符号只是作为辅助文字工具的前提下,索绪尔-叶姆斯列夫的符号理论,可以涵盖作为能指的表情符号。达内西对表情符号的所指研究,离不开叶姆斯列夫的表达-内容框架,而这个框架根源上是索绪尔式的。比如达内西指出,不能单独讨论某一个表情符号背后代表的意义,因为这个符号的意义与其说是它本身的构造决定,不如说它是根源于一个特定的沟通语言,传递这一语言系统下的某句话或者某个表情。正因为如此,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使用者之间产生有差异的理解。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表情符号的使用有规范化的趋势,在海外已经有不少线上的表情符号字典或索引,供人们破解不明白的符号代表的意思,比如emojipedia.com等网站。[10]但是这种规范化趋势注定是缓慢的:由于语言习惯在互联网文化前已经形成,网络符号注定会受到使用者所在地文化的影响。在实际使用中,表情符号的意义取决于表情本身以及它在用户头脑中约定俗成的情绪含义;它不是单向地存在于某个权威的字典或规范中,而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沟通场景下,存在于对话双方对特定符号意义的一致性理解和想象上。这种一致性直接关乎表情符号的使用是否达到它预期的沟通效果,即给交谈加入生动的情绪符号。尽管如此,表情符号规则在实际使用中仍非常容易出现诠释障碍:不同文化背景的使用者对同一表情符号的涵义,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解读。比如常见的“亮甲”和“点赞”表情符号,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解读会完全不同。“亮甲”展示的表情符号在某些用户眼中带有性爱暗示;而在中东、西非、俄罗斯、南美等地,拇指点赞的符号有强烈冒犯的含义。[11]
作为一种网络现象,符号学的意义在表情符号中表现得比传统文字更加突出。由于表情符号不具有语音涵义,它们可以直接与所指构成联系关系而不需要被还原成语言。这一特点是表情符号诞生以来获得广泛青睐的原因。同时借助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体系思路,任何单个的表情符号具有的意思,需要在整体的符号系统中得到确定:用户经常在一个符号列表中选出自己想要的表情,而列表中给出的脸谱和图案,涵盖了各种场合下人们的微观情绪语言。对符号的选用以及接受者对符号的解读,都遵循索绪尔-叶姆斯列夫框架里的符号信息传递规则。达内西在讨论表情符号的词义学(semantics)时,强调了表情符号和图像符号之间的区别,即前者只是用于补充文字文本的意思,因此具有附加性(adjunctive)。一段包含表情符号的文本,不会因为非文字的加入而改变其所指-能指结构。表情符号诞生多年以来,尽管造型更加精美生动,覆盖的内容更广,但作为文本附加用具的属性并未发生显著改变。
但是,如果表情符号本身在作为交流符号的情况下,符号与意义的关系将出现实质性变化。表情符号对意义的指示功能依然存在,也可以出现类似索绪尔讨论的对应指代关系。然而表情符号由于通过符号本身的象征形态来指示意义,在纯粹使用表情符号的沟通过程中,连续符号构成的符号群指代的意义,与文字表达有类别的不同。由纯粹的表情符号构成的文本,可能无法对应文字文本的语义,而只表达物像、动作、情感和动作序列等信息。纯粹表情符号文本比文字文本更加依赖沟通的语境,并且在信息传达不畅的时候不得不借助文字沟通。
五、结语
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经叶姆斯列夫等学者的拓展和延伸,涵盖了由传统文字文本到图像文本的表意系统。在索绪尔传统中,结构系统的意义存在于每一个符号,即单个符号的意义通过它在这个系统中独特的、排他性的作用而被决定。索绪尔强调单个符号意义的随意性,目的是把符号的涵义绑定在系统内部的关系结构里,而非单个符号的意义传统和集合中。在结构主义下,字典索引式的符号-意义对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符号的个体涵义只能跟随整体结构的关系和动态变化。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任何对表情符号做字典化规范的努力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表情符号因而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文字符号,它可以与表音文字共存,在不改变文本意义生产结构的前提下,使文本涵义更加丰富。作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表情与所指或内容的确定联系:只有假设表情符号代表的表情和其他细微的深层情绪属于符号的所指,才能通过文字和表情符号的书写系统表达出使用者的意思。然而由于表情符号通过符号自身形态的象征指代意义,它作为能指与文字作为能指有显著区别。纯粹的表情符号无法完成文字意义的表述,除非被给予非常明确的语境限制。语境限制越少的情况下,表情符号表达模糊的特点越明显。
参考文献
[1]Danesi,M.(2007).The Quest for Meaning: A Guide to Semiotic Theory and Practice [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Azuma,J.& Ebner,M.(2008).A Stylistic Analysis of Graphic Emoticons: Can they be Candidates for a Universal Visual Language of the Future? [C].In J.Luca & E.Weippl (Eds.),Proceedings of ED-MEDIA 2008--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Multimedia, Hypermedia & Telecommunications (pp. 972-979).Vienna, Austria: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in Education(AACE).Retrieved October 19, 2022 from https://www.learntechlib.org/primary/p/28510/.
[3]MacLuhan,M.(1962).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 [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4]Jakobson,R.(1960).linguistics and poetics.https://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j4rqf0rLrzAhUE_rsIHXyWCjQQFnoECCQQAQ&url=https%3A%2F%2Fpure.mpg.de%2Frest%2Fitems%2Fitem_2350615_3%2Fcomponent%2Ffile_2350614%2Fcontent&usg=AOvVaw20-LT9ObbQEBibsPS-NcvM. Retrieved November 3,2022.
[5]Danesi,M.(2019).Emoji:Langue or Parole?[J]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15(2):243-58.
[6]Alshenqeeti,H.(2016).Are Emojis Creating a New or Old Visual Language for New Generations? A Social-semiotic Study [J]. Advanc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udies,vol.7,No.6, December 2016,56-69.
[7]Hjelmslev,L.T.(1947).Structural Analysis of Language[J].Studia Linguistica,vol.1(1-3),69-78.
[8]Hjelmslev,L.T.(1969).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M],trans.Francis J.Whitfiel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9]Hjelmslev,L.T.(1954).La stratification du langage[J].Word,vol.10 (2-3):163-88.
[10]Seargeant,P.(2019).The Emoji Revolution: How Technology is Shaping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Danesi,M.(2017).The Semiotics of Emoji:The Rise of Visual Language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M]. London: Bloomsbury.
注释
1.叶姆斯列夫原著用丹麦语写成,本文一律引用通行的英语译本中采用的译词。
2.本文参照屠友祥对索绪尔关键术语的法汉翻译。langage:群体语言,langue:整体语言,parole:个体语言。
作者包胤彤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深圳报业集团在站博士后
见习编辑 刘兰若 审读 李诚 审核 刁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