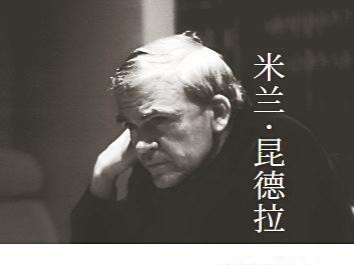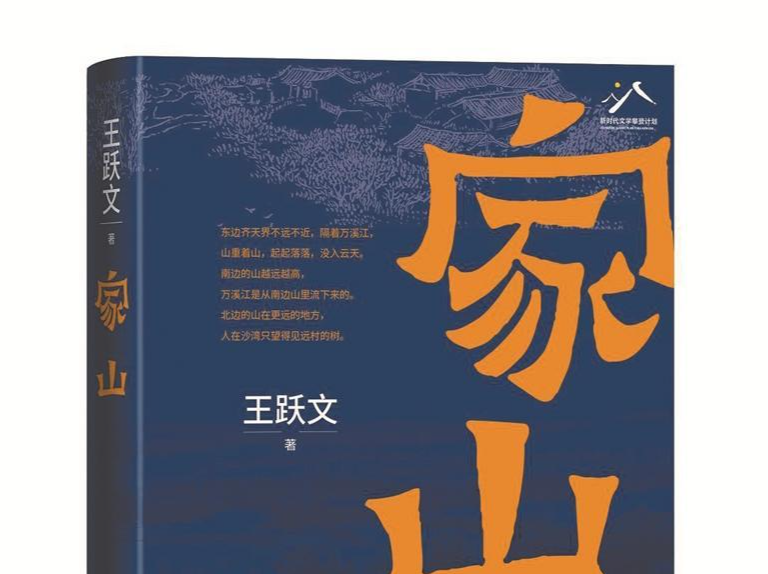不久前,韩东的新书《狼踪》《幽暗》同时面世,两部小说集采纳相似的封面底色,均使用了著名画家毛焰摄影作品并由后者题名,由此可见两本书在内容上某种互文互见的关系。这两本兄弟之书出版于诗集《悲伤或永生》(2022年)之后,体现出韩东某种以现场写作记录时间碎片的写作观,也体现出韩东一手写诗、一手写小说的创作姿态。

《狼踪》 韩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版
诗里有小说,小说中亦有诗,韩东四十多年的写作中,故事其实永远不曾缺席。他在早年诗作《我们的朋友》中,曾以特有的敏感与忧伤写到朋友的相聚场面:“我的好妻子/我们的朋友都会回来/朋友们还会带来更多没见过面的朋友/我们的小屋连坐都坐不下”,经历过岁月磨洗,他将诗意更加完整具象地呈现为故事,流逝在时光中的友情、爱情与事件纷至沓来。《幽暗》集中的《我们见过面吗?》再现了世纪初民间文坛景象,但不是简单的缅怀或纪念——在群英星散、故人远去的今日,作家将故事聚焦于一次貌似混淆的回忆,他写的是此刻与昔日的博弈,写的是人心的叵测与猜疑,也写到记忆之崖突然出现的断层。当时代的浪潮退去,一些学术化记录与历史化书写沾染上层层涂抹的“崇高”,但韩东清醒地写出:“世界就在我们的面前,伸手可及”,伸手可及却未必是“真实”,作家对记忆断层的刻写因此就有了几分自嘲性反思的意味。
收于同一本集子的《兔死狐悲》更像篇回忆录,主角张殿曾沉浮于岁月浪潮,现在奄奄于病榻,他经历了民刊的兴盛时代,并因此与名为皮坚的叙述者“我”结缘为友。小说的标题已暗示出,张殿的故事固然勾连起情节的点滴,其重点却在皮坚的回忆。张殿去世后的仪式上,“我”再次遇到了昔日女性朋友袁娜,后者递手帕的情节与韩东另一首诗的句子恰成辉映:“她递过一块手帕——这太过分了!/那里的手帕也不是手帕/只是事实的一片灰烬。”这灰烬成为对老友的薄奠,亦是以文字完成的时光纪念。韩东没有止步于忧伤,像鲁迅写《范爱农》一样,他小说中的“我”恪守本分,他记录,他回忆,但绝不妄度分别的日子里老友的经历与情思。时间在这里何尝不是也被刻镂出斑驳的断层,那断层里有我们无法窥破的秘密。
对于时间的秘密,最感兴趣的是小说家的注视与思绪,它试图用目光照亮并洞悉生命历史中被断续的部分,又往往归于失败。《狼踪》集中《对门的夫妻》一篇,几乎可以作为《狼踪》《幽暗》两部书的序言。所谓对门夫妻,相互的位置在几十年里不断被新人替换,不变的是“我”,一个单身的邻居。他因此成了观察者和记录者,邻居夫妻的秘密对“我”一次次敞开又一次次关闭,以至于“我”的记忆再次发生混淆。人如草木枯荣,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更生湮灭,小说结尾的诗中说:“唯余无名老楼,摇摇不堕/如大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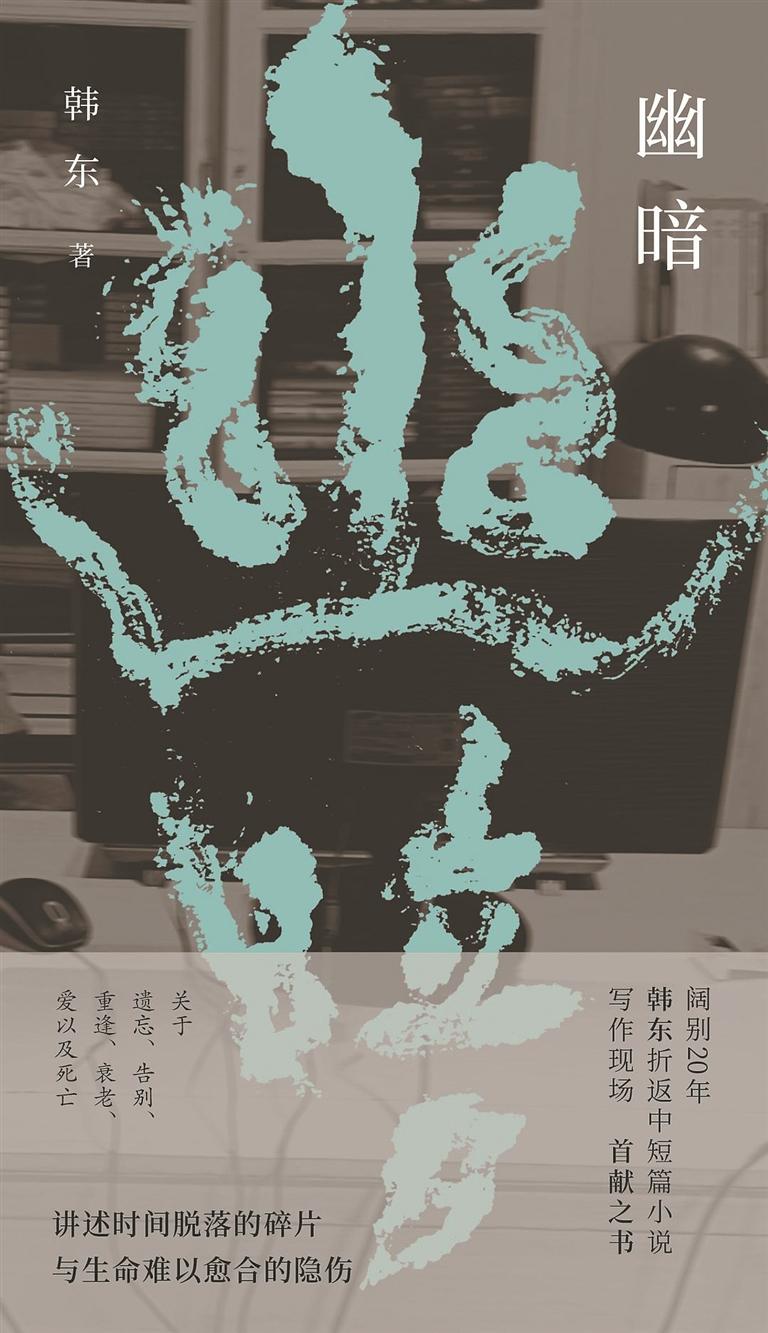
《幽暗》 韩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5月版
除了《老师和学生》外,两本集子几乎每篇都与回忆有关,梦一样的回忆,清晰又虚幻,人的奋斗、妄想、追逐与欢愉都在时间里成为尘滓浮沫,如《幽暗》集中《峥嵘岁月》里马东的起高楼、宴宾客与楼塌人去;或如收于同书的《动物》《幽暗》两篇中的魔幻情节。《动物》写置身异国的教授,一个人生“圆满”的中年男人,在陪伴年轻妻子游览异国时夜遇昔日爱人,后者已化身为鬣狗。面对教授的自得,鬣狗情人“再一次翘起了嘴角,就像要收集更多月光一样”,她告诉他:“这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且“我比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动物》是一则溽热里降临的冰凉寓言,提示着生命除了拼命向上外也许还有别的幽径可供探索。
韩东善写动物,他的名作《花花传奇》写的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猫,写人对动物的爱与无法沟通。收于《狼踪》集的《女儿可乐》则讲述了小狗可乐的一生,这篇小说无疑是对诗作《它是一条无人理睬的狗》的扩写。花花和可乐都被宠爱又保持了自由,如韩东所言:“它是我的狗,我可不是它的人哪!”也许,人与动物的关系就应该是好奇的对视陪伴与直到永远的“隔膜的游戏”。而这种隔膜岂止存在于人与动物之间?《狼踪》一篇中的心理反转,二十年的闺蜜关系中,曾小帆强悍专注,韩梦多愁善感,后者临到末了才显示了自己的世事洞明,她们的友谊原来如此表面缠绵实则脆弱。
《狼踪》《幽暗》两本书的可读性,表现在作者对人性的深刻观察,与对当下嚣攘生活的反省领悟。韩东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要虚度,我们的追求都太过实在。虚度和专注都是我喜爱的,并不矛盾。”也许生命本该是一种欢乐的旅行,毋惜物质上转瞬即逝的拥有,让我们展卷深思,伴随着作家“梦中的影子捡拾土地的余温”吧。
(原标题《诗里有小说 小说中亦有诗》)
编辑 黄力雯 审读 吴剑林 二审 张克 三审 周斐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