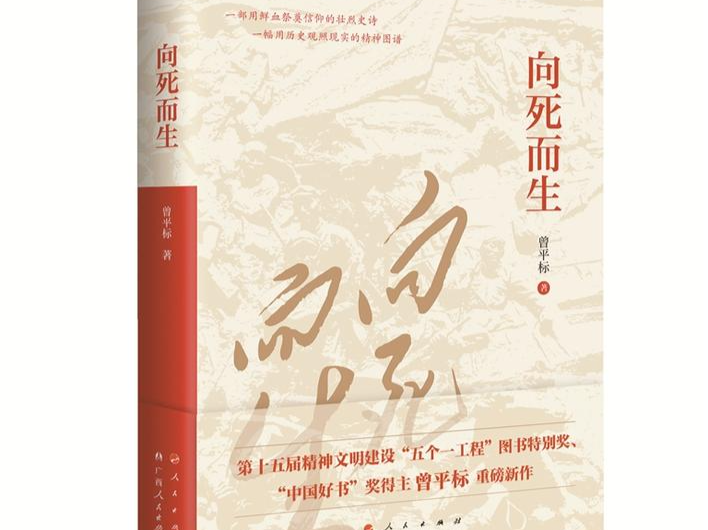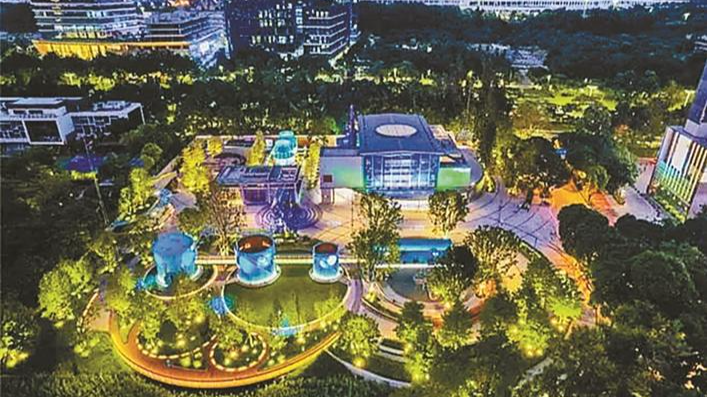“闹城”即山西太原。做面食、挖菜窖、看露天电影、去集体大澡堂洗澡,那是北方人记忆深处的场景;八级工匠、崩爆米花的人、采购员、民兵,那是往昔岁月里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一座大型重工业社区,被安放于古老的太原城中,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熟人社会,一座座功能各异的厂房成了孩子们的后花园,而苏丹是那群最能折腾的顽童中的一个。把记忆写下来,既需要作家之笔,也需要史家之笔,还需要艺术家之笔、思想家之笔、科学家之笔。《闹城》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苏丹教授撰写的回忆录式长篇叙事散文集,苏丹是艺术家,又是评论家,他的文笔有多重属性,也有多重意义。
苏丹以重工业城市太原为背景,记录了其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生活经历,将个人成长、家庭发展与社会变迁融为一炉,具有深刻的文学性和重要的历史档案价值。苏丹带领我们用艺术家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的青春,看到真实背后的荒诞、残酷背后的温情。书中艺术作品的选择和对记忆的艺术化处理,都让人着迷。作者在重现青葱岁月的同时,还以艺术家的专业视角回望过去,重新思考空间、城市等问题,加深读者对艺术与设计的理解;把时间融入空间,有一种时空对应的怀旧美感。书中配有多位知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与文字参差对照,颇令人玩味。

《闹城》 苏丹 著
新经典·琥珀工作室
花城出版社 2020年6月
工业时代与书写记忆
文/孙腾
1
不久之前,一部名叫《后浪》的宣传片火遍全网,有人赞扬、有人痛斥、有人不屑,但难以否认的是,曾经是中流砥柱的60后、70后、80后,已经统统成了被拍在沙滩上的“前浪”。然而正是这些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代的亲历者们,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一个高度集中化的旧世界逐步瓦解,以及一个全球化新世界的诞生。
如果说新世界的标志是电脑、智能手机、无人机,是无所不能的信息化;那么旧世界的标志就是工厂、高炉、烟囱、集体大院,是大干快上、计划生产的工业化。“一五”计划以来,众多城市开始了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北方地区。人们认为,这些城市将作为生产力的象征,与落后的农村社会对立,成为伟大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然而吊诡的是,这些围绕着几座甚至是仅仅一座工厂或矿山建立起来的城市,比起21世纪的城市,其实更像是前现代的村庄。城市的空气并未使人自由。人们居住在单位的员工宿舍之中,在单位的厂房里从事日复一日、绝少变化的劳动,在单位的食堂吃饭,在单位的澡堂洗澡,在单位的礼堂看文艺汇演,在单位的医院看病,在单位的供销社买东西。他们的子女在单位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接受教育,最后进入同样的单位接班。从生到死,从工作到生活,单位便是个体生命的一切。厂里的同事取代了传统村庄中的亲族,化为工业时代的新型大家庭(extended family)。
一个个基于厂房的熟人社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无所不能的厂领导、牛气十足的卡车司机、态度傲慢的供销社售货员、进城偷偷贩卖农产品的村民……这些刻板印象一般的人物出现在几乎所有人的记忆之中。同样遍及全国的还有苏式的红砖板房,绿漆白粉的公共室内空间,木头和玻璃打造的商店展示柜,软塑料封皮的笔记本。当然,还有无数冠以“解放”“人民”“新华”“胜利”之名的公园、街道。同一座城市中的不同“单位”,甚至不同的城市之间,无论空间、话语、形象都几无二致。重工业粗粝坚硬的面相背后,个体共享相似的生活、工作与娱乐,而他们也被要求像机器零件一般,或者说像“一颗螺丝钉”一般,为这个单位以及更伟大的目标添砖加瓦。
尽管无数个体本能地挣扎着,以种种微小的反抗试图获得个性,试图重新以脱离主流的话语定义自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工业化单位成功地消解了个体,在将个体化为计划数据之下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将个体贬低为宏大叙事背后的失语者。而要对抗这种失语所带来的历史空白,就必须搜集足够多的高品质的私人记忆,这种记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
而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伴随着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而来的,是这些工业化单位的瓦解。资源枯竭的矿山、破败凋敝的厂房成了很多城市的常见景观,与之相伴的是停薪留职、破产、下岗、人口外流、老龄化等新名词。这不仅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是从自成一体的经济单元向全球化开放市场的变革,是机械化大生产的工业时代向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的变革,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单位”文化向去中心化、去集体化的变革。在短短十几年里,一种看似牢不可破的制度以肉眼可见的惊人速度崩坏,而其中的个体,则以不同的方式裂解。从前在社会上最吃香的工人阶级老大哥徘徊在失业边缘,“共和国的长子”成了难以振兴的“锈带”。而过去隐于幕后的权力差序,借助市场经济迅速货币化,造就了一个个带有原罪的新时代商业巨子。众多重工业城市从诞生之初便通过经济剪刀差,以农村的牺牲为代价成长起来,而现在,轮到它们自身成为新时代的代价。新兴的沿海商业城市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机会,吸引着人们前去闯荡,与他们共同离开的,还有资本、技术。除了因工业和矿业生产而遭受严重环境破坏的土地,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在加速逃离,这种恶性循环造就了一个个衰退之城。与此同时,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也开始崩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心理上的休克,在无力离开衰退之城的人群之中,茫然无措成为最普遍的状态。在城市化激烈的进程中,无论原生的农业村庄还是次生的工业单位,都丧失了主体性和话语权,化为隐没于高速经济增长之下的黯淡注解。正如清华教授苏丹在《闹城》中描述的:“我看到每一个个体沉醉在这种集体的荣耀里,因感受到温暖而无比幸福。空间消失之后,这种精神状态成了孤魂野鬼,若隐若现地浮现在那些工业革命的遗老遗少的脸上。”
3
今天,在21世纪20年代的门槛上,已经远去的那段时光又意味着什么呢? 脚下的这个时代属于“后浪”们,他们生于繁荣,长于繁荣,成于繁荣。他们的故事阳光、朝气,正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于他们而言,以“单位”为代表的过去更像是一段带有怀旧风的浪漫往事。废弃的工厂变成时尚弄潮儿扎堆的艺术空间;蒸汽火车头被整饰一新,变成达人必去的网红打卡景点;不再冒出烟雾的凉水塔和烟囱仍点缀在一些城市的天际线上,变成能勾起朋友圈中无数赛博朋克式想象的标志;空旷的厂房中巨大而不明用途的机器慢慢锈蚀,变成冷硬酷炫的废土风微电影取景地。这种娱乐化解构,并不是因为年轻人固有的乐观或没心没肺,而是整个现时代试图对旧岁月下的定义,或者说,是幸存者的定义。在这个“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的时代,向前看、向未来看,似乎不仅仅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历史不符合潮流、回忆不符合潮流、反思不符合潮流,这些东西似乎更应该被一股脑塞进旧皮箱,扔到床底下看不见的地方与灰尘做伴,或是泡在福尔马林里,作为表现“古怪落后”的标本,供猎奇者把玩,为新时代贡献最后的经济价值,直至土崩瓦解。
非常遗憾的是,几十年前那个曾经给我们留下许多快乐记忆的工厂乐园早已荡然无存。两天之间,我反复乘车路过那个片区,却根本看不到一点历史的踪迹。它已经全部被拆掉了,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区。这让我在情感上很难接受,工业文明的价值居然就这样让今天的都市发展感到累赘,恨不得从根本上予以铲除。
——苏丹《闹城》
而对于那些成长在工业化单位,为了追求个人价值而离开的个体,或者说是那些“前浪”们,记忆的价值可能更加不同。随着他们逐渐进入中年,除了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妥协,以及对未来的某种似有若无的期许之外,另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便是自我的根基。作为中国人,这种根基可能就是故乡、故土,它们深深地雕刻在我们的文化模因之中,不断地以“思念”之名搅乱我们的心绪。然而,故乡,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存在,更是定格在回忆中的一段时间,以及漂浮在时间中的人与事、色彩与声音、气味和触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中的那片土地已经在不断的变化中丧失了它的“故乡性”,慢慢变成模糊朦胧的符号,和乡音一样悄悄退化。任何曾经在外多年又重回故土的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作为对“魂归何处”这个问题的解答,它们已经不再成立。那些跨越了两个时代、两个世界的人们,早已无处可归,定义他们根源的,只有记忆:无法切割、不可剥夺、难于复刻。
在网络中书写期间,我不断回到那个“现场”寻找残存的信息。有一次,三楼的一个窗口探出半个身子来,那张脸冷冷地向下瞥了我一眼,然后收回目光骄傲地望向远处。我认出了他是我小时候的一个玩伴,一个从未离开此处的原住民,紧接着又一张麻木的脸出现了,蜡像一般的面孔依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色泽,但最坚硬耐久的牙已经掉光了。隔着很远我就可以从这些遗世独立的活体身上嗅到陈腐的气息。
——苏丹《闹城》
4
试图从宏大叙事中唤醒记忆、寻找真相,往往是既疲惫又徒劳的。对于一个集体而言,历史如同一块橡皮泥,不断被塑形,以此来解释现存之物的合理性;而当现存之物断裂、破碎时,过往的定义便成为尴尬的存在:在宏大叙事之中,作为社会主义梦想标志的重工业单位被斥为畸形的计划经济产物,在主流话语中曾充满了光荣与骄傲的职工们也变成了懒散低效的代名词。当立场逆转、颠覆之时,矛盾的评价自然会接踵而至。工业单位在过去得到了多少不恰当的夸赞,现在就得到了多少不恰当的贬低。这种反差,以及相伴而来的混乱和冲突,提供了将历史彻底固化的理由。于是,历史变成了档案中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和决议,它们不仅试图告诉亲历者和非亲历者们过去应该“发生了什么”,还试图指出该如何做出评价,不是教育,而是教谕。通过制造历史或是抹除历史,我们制造沉默,制造正确;通过集体遗忘,让个体完成面向未来的自我改造。讽刺的是,工业时代的基本精神仍然健在,我们仍在生产思想的工业零件:千篇一律、光亮冰冷、毫无瑕疵。群体越回忆,个体越失忆。
摆脱群体性失忆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对个体记忆的书写。无论是谁,占据了多么强劲的话语权,都无权也没办法垄断历史。而每一个在历史中沉浮的个体,却可以在自我的小世界中垄断自己的经历。在语言、身份甚至相貌、性别都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更改的时代,这种个体对自身经历的垄断,或者说记忆,成为了自我的唯一界限。对个体记忆的书写并不仅是简单地记录个体存在的依据以备好事者考证,更不是为了满足猎奇者的窥淫癖。书写记忆的过程,不是一台电脑将存储的信息简单打印出来,而是对世界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再组织,是寻找并重新定义自身存在的“极据”(ultimate datum)的过程。对于个人而言,记忆也会不断被当下的立场所扭曲:适时地遗忘、适时地改变,以便我们能够心无愧疚、理直气壮地活下去。工业单位,在某些亲历者眼里,是其乐融融的平等主义大家庭,而在另一些亲历者眼里,则充满了困乏、压抑,以及种种人性黑暗面的集中爆发。这种撕裂可能会让寻求正确性的人无所适从,然而正确性从来不是历史的全部,判断正确的标准既来自书写者,也来自阅读者。书写者以自身的经历关照时间,以主观的感受解读时间,从而摆脱了作为工业化螺丝钉的沉默者身份,实现了对整齐划一的宏大叙事的叛逆。与此同时,当个人生活与巨大宏观力量相撞并破碎的时候,对记忆的书写又实现了个体与历史甚至现实的和解。不过,不是所有的亲历者都能成为书写者。书写需要能力,需要脱离外界强加给我们的失忆,唤醒沉睡于生活中的真实与虚幻。书写需要勇气,需要敢于面对自我与时代的种种不堪,甚至是与自己奉为圭臬并赖以生存的原则切割,在为幸存者代言的同时,也为沉默的逝者发声。一个时代能够拥有多少书写者、能够接受多少书写者,恰恰印证了这个时代的良心。应该向所有记忆的书写者致敬,无论其结果是粗粝的表达,还是精美的艺术,也无论在其中有多少的文过饰非、有多少的自我催眠,它们都是存在的证据。
苏丹的私人记忆,以家庭树、邻里和校园为轴心,借助有序的时空罗织丰富的细节,细腻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北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在一个公共叙事被任意删除和涂改的语境中,这种高品质的私人记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只要这种文本足够多,就能填补“宏大叙事”所带来的历史空白。
——朱大可
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注定成为阅读者。这并不意味着阅读者只能被动地接受。通过阅读,我们得以窥见时间的一鳞半爪,并通过与书写者的认同或分歧判断何谓真实,何谓虚伪。即便是不曾有过相同经历的阅读者,也可以从中获取最为一般的基于人性的微光,在面对未来时不至于重蹈覆辙,亦不至于浑浑噩噩。所以,也要向阅读者致敬,通过不断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身处的时代或许终将摆脱群体性失忆的状态,清醒地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然而我们不断地写,是因为我们写不完全那伤痕;我们不断地追忆,是因为我们再也忘不掉,却又记不起那过去。”
读特特约作者 :孙腾
参考文献: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米塞斯:《人的行为》
杨晓明等:《中国单位制度》
吴海琳:《中国组织认同的单位制传统与当代变迁》
(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