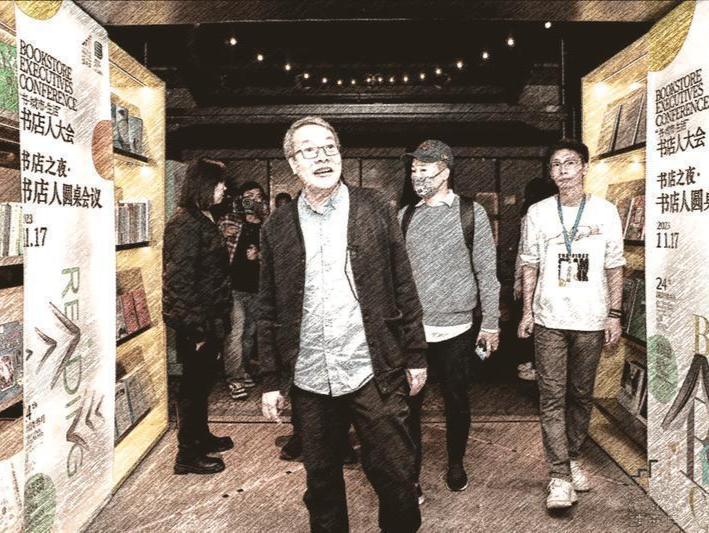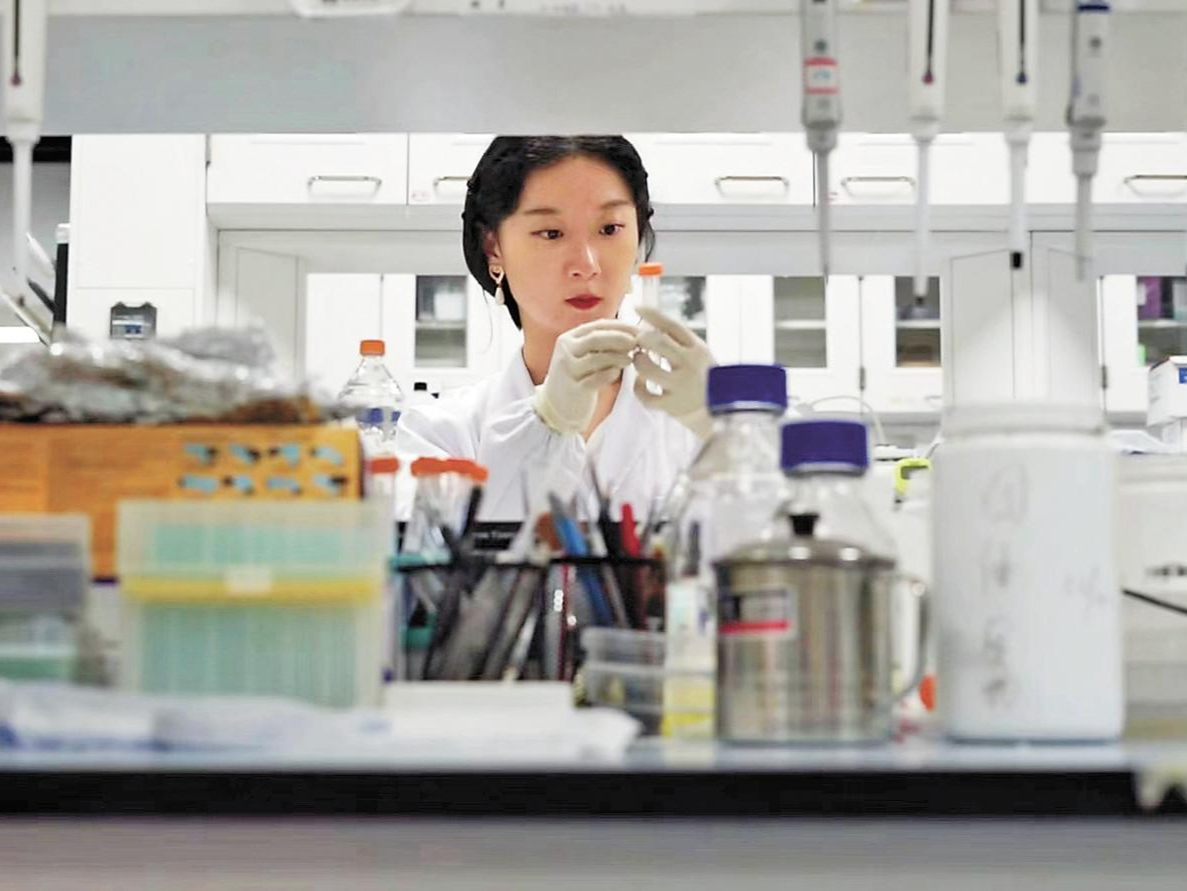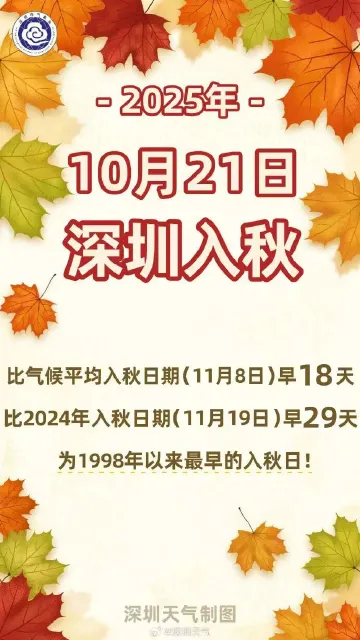10月20日下午,一个由山西省委宣传部主办、香港商报承办的“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山西行”活动的记者采访团,出现在了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的晋国博物馆前。作为其中一员,脚下的土地、眼前的建筑,对我这个来自千里之外的深圳人来说都是陌生而新奇的。
跟随着博物馆讲解员的引导一路前行,仿佛穿越时空,走进晋国六百年的历史画卷之中。直到玻璃展柜中一件熟悉的青铜器复制品把我拉回了现实:它整体为回首站立的凤鸟造型,鸟尾却又是一头鼻子内卷的大象,通体布满了云纹、雷纹、羽片纹、立羽纹、羽翎纹,繁而不乱,华美无比。它就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院徽也是以它为原型设计。今年4月至7月,深圳南山博物馆举办的“晋国六百年——山西文物精华展”中,深圳人也曾一睹它的风采。
原来,晋侯鸟尊的出生地就在此处。
而接连刷新我认知的,还有令人震撼的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一段夯土隔梁将约200平方米的整坑分为马坑和车坑两部分。马坑殉葬马匹至少有105匹,车坑里整齐摆放了6排车辆,阵势壮观。
我一边感叹这是什么宝藏博物馆,一边猜测这考古挖掘的背后肯定有不少精彩故事,这时,晋国博物馆的馆长董朝晖向我推荐了一位老朋友吉琨璋。在我离开山西不久后,吉琨璋被授予了晋国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荣誉。

内卷?外卷?
吉琨璋今年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退休了,可他仍然很忙。我在山西采访期间,一直未能约上他,直到我回了深圳,几次在微信里沟通,才约在10月的最后一天,趁他休息的时间进行一次线上采访。
采访的前一天,我特意去看了吉琨璋参加过的一期《中国考古大会》,主题是“探秘晋侯墓地——寻找西周时期晋侯世家”。在节目中,吉琨璋掀开晋侯鸟尊复制品的盖儿,向观众展示盖上的铭文“晋侯作向大室宝尊彝”:“侯是晋国的爵称,晋国的国君都称为晋侯,山西简称晋,这个‘晋’就是从这儿开始有的,这是我们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早出土的金文‘晋’字。”这就是鸟尊之所以能成为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很关键的一点。

▲晋国博物馆鸟尊复制品
20世纪70年代,为了寻找晋国的踪迹,北京大学教授邹衡依据史书典籍,带领考古队在山西省晋南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对临汾曲村-天马遗址开始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兴起一股盗墓之风,曲村-天马遗址也受到波及。随着墓地被盗,1992年,征得国家文物局同意后,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曲村考古队负责展开抢救性发掘。在这里,他们发现了9组19座晋国早期的晋侯和夫人墓葬。
2000年,考古队在发掘被盗墓贼用炸药爆破的114号第一代晋侯燮父墓时,发现了被炸成碎片的鸟尊。“正因为碎了所以幸存下来。”吉琨璋说,当时的鸟尊碎片和其他青铜器碎片混在一起,区分还是可以的,但再拼接起来就不容易了。于是,鸟尊碎片就被“套箱”,即连同墓土整体从墓室里切割下来,打包运回了北大的考古实验室。经过了近两年的拼合、除锈、复原,鸟尊才得以重见天日。
但那时的鸟尊也是不完整的,它的尾部象鼻有一节缺失了,在2002年上海博物馆首次展出时,文物修复人员给它安上了一个临时的“尾巴”,做出了象鼻向内卷的修复判断,为了不误导观众,上面没有仿制任何纹饰。而这也一度引发了象鼻应该向外卷,还是向内卷的学术争论。
在第二天的采访通话中,我迫不及待地问起了鸟尊。当年鸟尊展出结束后,就回到了出生地。当时,刚刚从一场大病中痊愈的吉琨璋受命负责在曲村-天马遗址的合作工作,经常对鸟尊进行研究。几年后鸟尊借展山西博物院,就此留在了那里。
同时,吉琨璋也在组织技术人员继续对晋侯墓发掘的文物进行修复。有一天,一位到北大去的师傅告诉吉琨璋:“找到鸟尊的尾巴了!”吉琨璋很激动,“当时总有人提出象鼻朝里是不对的,包括我也觉得有问题,没出现过鸟尾巴朝里这种情况呀。”这下,大家期待的答案终于要揭晓了!
事实证明,这是一只“内卷”的鸟尊。2018年我去山西博物院参观时,看到的还是不完整的鸟尊,如今在南山博物馆和晋国博物馆里看到的鸟尊复制品,尾巴上的纹饰流畅精美,气势更胜从前。
冷门?热门?
鸟尊出土地曲村-天马遗址,是晋国西周时期都城所在地,也是今天晋国博物馆所在地。这是中国第一座晋文化专题博物馆,于2014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在博物馆的发掘史展厅,展示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三代考古人历尽艰辛、寻觅求证的经过和考古发掘工作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学生生产实习主要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山西的曲沃曲村,一个是山东的长岛。吉琨璋与曲村的缘分就是从1984年实习开始的。
在吉琨璋回顾自己考古经历的一篇文章中开头是这么写的:“人的一生充满选择,有的选择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选择目的性很强,有的则是盲目的,很多选择都充满着偶然,而偶然的背后可能都有必然,无论哪种选择的结果,对人生轨迹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吉琨璋是在懵懂中走上考古这条路的。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正是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时刻,吉琨璋还记得当时大家最热衷报考的专业是法律、经济,因此高考结束的他也跟风报考了北大的法律系和经济系,没想到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却是历史系考古专业。考古是什么?具体是干什么?吉琨璋和身边的人都是茫然的。热血澎湃的少年就感觉这冷门的专业像一盆冷水浇在了心上。
因此,入学后吉琨璋不免带了些抵触情绪,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居然没有及格。虽然后来他奋发学习,把专业成绩提了上去,但“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没少去法律、经济系旁听,还偷偷啃了康德、黑格尔的古典哲学,热衷于参加各种非本专业的讲座。
大三第一学期,吉琨璋所在班级被安排去曲村生产实习。他们带着铺盖被褥,三三两两借住在当地老乡家中。白天,在骄阳下,他们从布方开始,挖土、用手铲刮平面、辨识土质土色、划地层、判断每一个现象、清理遗迹、绘图、填写标签等;晚上,伴着青灯,他们聚在一起听老师讲课,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吉琨璋慢慢了解考古是怎么一回事,并从中发现了专业的意义。
但他还是不甘心扎根在这冷门的专业里,快毕业时,吉琨璋选择报考了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但没成功,毕业后,他被分配回到了家乡山西,成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那一刻,吉琨璋觉得也许这条路就是命运的选择,但仍然不是他心中所想。

▲1984年,吉琨璋(第三排左三)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82级师生摄于曲沃曲村。

▲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82级曲村实习20年纪念,吉琨璋(前排左四)和同学重回曲村。
“这么多年没有人和我这么聊过。”电话那头,回想起当初误打误撞入行时的挣扎和迷茫,吉琨璋似乎有些感慨,写下那篇文章,本打算是给学考古专业的后辈们一些经验分享,却也忍不住袒露了曾经的自己,在当初老师一遍遍强调要稳固专业思想的情况下,吉琨璋的这些想法和举动其实是既无助又叛逆的。
那吉琨璋后来从事考古,就是赶鸭子上架不得不继续干的吗?当然不是。“我那篇文章原来的题目叫《考古的温度》。”吉琨璋说,曲村对于他们这些考古系学生来说,是精神的家园,对于他来说更是彻底点燃考古热情的地方。
辛苦?快乐?
在回到曲村之前,吉琨璋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
他到现在还对第一天到侯马的场景印象深刻:10月底深秋的一个清晨,他和一位同事坐了一夜的火车硬座来到工作站前,却看到工作站就在一堆刚拆的废墟边上,被一层浓厚的白霜笼罩着,一片肃杀。当下,吉琨璋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凉透了。
不过,吉琨璋还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工作乐趣:发掘、读书、写作、做卡片。以前没有电脑的时代,考古人员就是靠做卡片,将搜寻到、阅读后的资料进行分类记录管理,方便后期研究需要时调用。从晋南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到山西商代考古材料、山西及周边的周代晋系统的墓葬材料,卡片的厚度在增加,吉琨璋的考古热情也在慢慢升温。
也许,这经历过的挫折、磨练出的坚毅、积累下的才识,都是为了更好地相遇。2002年,吉琨璋在曲村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
2004年,吉琨璋负责发掘山西运城市绛县横水倗伯夫人墓葬,发现了一个不见史料的古倗国,还花了7个月时间尽可能保存下来墓中的荒帷(当时的棺罩)。因此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文物局颁布的考古田野一等奖,要知道自从第一届一等奖颁给了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其后十多年一直空缺。

▲吉琨璋在工作中。
2005年,吉琨璋一边组织修复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的青铜器,一边率队开始发掘曲沃羊舌晋侯墓地,2006年春节过后不久,他又组织发掘曲村-天马遗址晋侯墓地的1号车马坑。那时,在这三个工作地点都能看到吉琨璋的床和灶。
吉琨璋跟我说起这些发掘经历时,温度似乎都是打开记忆的钥匙。
比如在发掘横水倗伯夫人墓葬时,已经是4月,天气很热,但是当吉琨璋和同事下到17米深的墓里时,却阴冷潮湿。因为墓太深,需要使用硬梯子和软梯子,下去一趟很不容易,所以他们每天都是穿着棉服,上班下墓,到了下班时间才上来。大家在清理棺内玉器时,都是跪在垫子上猫着腰往下工作,只感觉寒气一阵一阵往身上钻。下了班,他们常常得在吃饭时喝点酒祛祛寒气。
又比如在羊舌晋侯墓地发掘的那年冬天,雪特别大。吉琨璋和同事们在墓上搭的塑料棚子都被雪压垮了,每天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扫雪。夜里,他们住在临时搭建的屋子里冷得只能和衣而眠。
那是吉琨璋工作最忙碌、也是最有收获感和成就感的几年,更让他从此坚定了把考古作为终身事业来做的决心和信心。
我忍不住感叹,“考古真的太苦。”
可吉琨璋却说,“大家可能一直都觉得考古很苦,但是我和我接触到的做考古的同志,都没有听到谁叫苦。”
我突然悟了,“这是不是跟‘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一样,有一种苦,叫作外行人觉得你苦?”
吉琨璋十分赞同我的比喻,“人一辈子总得做点事业。你要是抱着这么一种想法去做,你不会觉得苦,所以我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苦的概念。我自己而言挺快乐的。”
主动?被动?
在晋国博物馆里,最让人难忘的莫过于1号车马坑。它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21米,南北宽14米至15米,是中国所发现西周时期最大的车马坑,比秦始皇兵马俑还要早606年。马坑中的马匹无序叠压,呈现出挣扎状,甚至马身上还有箭镞的痕迹。而车坑的48辆车中包含了礼仪车、战车、辎重车以及生活用车,基本囊括了西周时期的全套车制,我还隐约看到了一辆车上暗红的装饰。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发掘现场。
吉琨璋惋惜当时没在现场,不然就能带着我边看边讲述他们发掘车坑的过程。对他来说,1号车马坑是有特殊意义的,相比从前被动地配合城市建设进行的考古活动和对被盗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是他作为领队首次主动选择的申报项目,显然让他更饱含激情。
“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已经把马坑挖出来了,但是车坑却像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一直没挖到车的位置。”吉琨璋说,发掘车马坑是考古田野发掘中难度最大的,因为先秦的车主体是木制的,当作为随葬品被埋藏在泥土中,经年累月,木材会逐渐朽烂,萎缩成灰,原来的实体变为空腔,淤土又渐渐填实,形成“土车”,所以也被称为“土中找土的工作”。
因为以往也出现过发掘车马坑把车轮削掉的情况,他们必须制定严格的发掘方案。于是,在那个闷热的夏天里,吉琨璋就跟队员光着膀子、穿着短裤,一人一个马扎、一碗水,看着车坑讨论该怎么挖。
假如土下全是车辆,通常车朽烂后中间部位可能会塌下去,而边角位置会高一点。所以他们选择从东北角开始挖,“哇!老天,太幸运了!”电话那头吉琨璋的声调明显都高了起来。后来证明东北角的车位置正是车坑最高的,他们一挖下去就看到了车衡的銮铃,顺着车衡就找到了车轮、车厢的位置,发现车辆是东西向摆放,车轴顶着车坑的北壁。他们果断决定破坏车坑的北壁,向外延伸一米挖到坑底,找到坑底后再往前推进,这时他们惊奇地发现居然有一排10辆车的车轴。
当第一排车辆都露出来后,考古队就这么从上到下与横着往前结合,用了两年时间一步步把48辆车都剥离出来一半车身,一辆都没有挖坏。
后来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先生来看车马坑,对吉琨璋说了一句“你真敢干”。他现在想来,当年的自己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但他当时就没想过怕,“我看过一句话,说是年轻时不怕,老了不悔,人这一辈子就没有遗憾了。我想想还真是这样子,如果那时思前想后不去干,就不会有现在的车马坑了。”
虽然当初是被动选择,但吉琨璋至今无悔成为考古人。也许对有的人来说,考古就像核弹爆发,迅速升温直至无极,但慢热如吉琨璋,最终也会沸腾。
版权声明:
本专栏刊载的所有内容,版权或许可使用权均属晶报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复制或改动,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如需转载或使用,请联系晶报官方微信公号(jingbaosz)获得授权。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