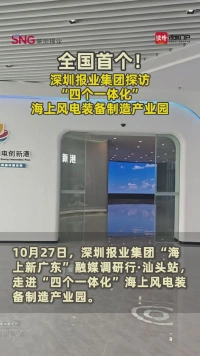冬日早晨,阳光懒洋洋地洒在人们肩头,梅林一处偏安一隅的小区热闹起来。临街的老商铺“刷刷”拉起卷轴门;上学、上班的人群脚步匆匆;受困于狭窄过道的汽车一点一点向外蠕动,间或响起短促的喇叭声;载满包裹的快递小哥陆续出发,如一群灵巧的鱼儿,在几个丝滑的转弯后游进车流……
像无数个平凡普通的日子一样,在这些热闹背后,无人留意的街角,一家裁缝店静静地掀开了门帘。店主兼唯一的员工曾阿姨在缝纫机前坐下,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

曾阿姨正在店门口的缝纫机前忙碌。
不起眼的裁缝店开了近10年
阿姨是四川人,今年56岁,开店做裁缝已有18年了。目前经营的这家裁缝店已经开了近10年。
曾阿姨的小店很不起眼,窄窄的,旧旧的,统共不足十平方米。主要的业务就两项:做针线活儿和衣物干洗。
店面虽小,但五脏俱全。里外各置了一张工作台,靠墙打了两排置物架,屋顶搭了横杆,挂着一排衣物。店里共配置了3台缝纫的机器,一筐五彩斑斓的线卷格外惹人注意,熨斗、剪刀、卷尺、画粉、针盒等工具也都配齐了,摆在方便拿取的地方。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间,曾阿姨能完成周围居民所需要的大部分缝纫工序。


曾阿姨的裁缝店。
曾阿姨每天的生活很简单。剪裁、缝补。来店里改衣服的人比较多,且大多是熟人,裤腿衣袖改多长,腰身放多宽,哪里需要加拉链……交代一声即可。一有人拎着袋子过来,她就从缝纫机前起身,顺手拿起一块画粉,顾客比划哪个部分需要修改,就在那里做个记号。有特殊需求就会商议一个办法比给顾客看。谈妥后,报出价格,并约定好取衣服的时间。顾客一般也不多言,说给多少就掏出手机扫码支付。也有要求取货时才付钱的,曾阿姨也爽快应下。
一天里的大部分时候,曾阿姨会在门口的缝纫机前忙碌。工作时,缝纫机的“哒哒”声陪伴着她,偶尔那台放置在机器上的红色收音机也会打开,咿咿呀呀地响上半天。在这种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曾阿姨和她的小店已经度过了近10年的时光。

曾阿姨在她的店门口忙碌。
10分钟内改完一对裤脚
如果说工厂批量生产的服装是冰冷的工业化的产品,那么,经裁缝店改装后的服装则被赋予了手工的温度。在曾阿姨的眼中,量体裁衣是做衣服的基础。“工厂出来的大货只是一个标准码,对很多人而言并不合身,所以好多人找我就是为了把衣服改到合身。”
曾阿姨接得最多的活儿就是改裤脚或衣袖,每项收费在10块钱左右。这个工序对曾阿姨来说熟得仿佛有了肌肉记忆。
先把衣服平整地铺在案几上,再抽出一把长尺量好尺寸,顺便抓过画粉做个标记。接着用长针挑开缝好的裤脚线,线头冒出一截后,以两指捻起,使劲一扯,整段线就摧枯拉朽地散开了。再上剪刀,沿着标记点,“咔嚓”一声裁剪完成。



曾阿姨正在缝边。
后半部分就剩下重新缝边的工作。曾阿姨拿手一比,就折出了新的缝边位置,压到缝纫机的针头下,脚下微动,手指由上往下快速平移衣物,在若隐若现的“哒哒”声中,走出一排整齐细密的针脚,眼看着针脚已经无路可走了,这时,曾阿姨突然一个反向平移,机器自动剪线,针头抬起,缝边完成。注重细节的曾阿姨,还会掏出小剪刀减去多余线头,这才宣布大功告成。

曾阿姨用小剪刀修剪线头。
像这样一整套工序,曾阿姨平均每天要做30多次。若接的量太大,就需要晚上继续干。在屋内灯光下,没人打扰,她能在10分钟内改完一对裤脚。
高效的工作也体现在耗材上。硬币大小的画粉,一盒有20块,她每年要消耗3盒。黑白色的线用起来最多,她平均2到3个月就会用完一卷。

硬币大小的画粉,曾阿姨每年要消耗3盒。
日复一日的工作在曾阿姨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手指,尤其是食指已经盖上了一层厚茧,指甲缝里也总是沾上画粉。她的视力也在劳作中受损,光线一差,就得戴上老花镜工作。

曾阿姨戴上老花镜查看衣物。
一针一线串联起无数温暖的情感
久居高楼大厦里,被快节奏的生活裹挟向前,对于很多人而言,衣服旧了、坏了、不合身,丢了再买就是了,缝缝补补修修改改实为一桩费时费力的买卖。况且,在繁华都市寻觅一个手艺好收费也合适的“宝藏”裁缝店真的太难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人在频繁光顾曾阿姨的裁缝店呢?“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曾阿姨思索了一下道。

年前,有一位老人拿着一件破旧的毛呢大衣来修补,曾阿姨如实告知“工程量较大,费用也较高,够买一件新的了”,但老人坚持要修补,“花多少钱无所谓,只要弄好了就行。”
不光是眷念旧物的老年人,追逐潮流的年轻人也爱光顾曾阿姨的店。几年前流行“露腰装”的时候,一些稚气未脱的学生便拿着校服请曾阿姨帮忙改短。在和校方商议后,曾阿姨后来拒绝了学生的请求,没想到反而在学校“打响了广告”,很多老师找上门来请她改衣服。
在改衣服的过程中,曾阿姨也有一些奇妙的际遇。比如,她曾遇到两位顾客,他们的裤长分别是110厘米和119厘米,巧合的是,这个裤长数据和他们的职业刚好对上了——这二人分别是警察和消防员。
若要选出这些经历中最难忘的,那帮别人改婚纱礼服一定排得上名次。曾阿姨记得,那是一件腰身不太合适的白色婚纱,由新郎匆匆送来,经曾阿姨的巧手改造后,新娘顺利穿上了既美丽又合身的婚纱,完成了一生一次的盛大仪式。
“这对夫妻,如今孩子已有半人高了,他们还会常常来光顾。”
曾阿姨手里的活儿不停息,神色温柔,语气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经历的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故事。街巷里有孩子跑来跑去,凉风吹过,树影摇晃,这方小小的空间岿然不动,安静沉稳,带着一股无声的力量。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总是很容易让人们忽略街巷的烟火气,忽略不起眼的东西,也忽略人与人的情感链接,犯下下意识用金钱这样单一的价值来衡量事件的错误。某种意义上来说,在钢铁森林般的都市里,每一个裁缝都是帮助都市人重返生活的锚点。他们一直安静地守在那,用针线缝合眷念,以剪刀裁掉冗余和不适,再持一把滚烫的熨斗将平凡生活的褶皱一一抚平。


扎进平凡生活里
曾阿姨的生活和缝纫密不可分,在她眼里,“针头线脑”这个词代表的就是她生活本来的样子。“都是细小、普通而琐碎的事物,不必深究它的意义,一头扎进去,好好吃饭好好做事就好。”
曾阿姨与缝纫结缘,要追溯到小时候。从小体弱多病的她,在十几岁时生了一场大病,无法继续上学。于是,便央求母亲送自己去学了缝纫。“那时用的是手动的缝纫机,脚下踩动踏板,机器才会转起来,还会发出很大的响声。”曾阿姨已记不清初学时被针尖扎过多少次手指了,好在功夫没白费,在日复一日的苦练中,她的技艺逐渐成熟。
1996年,已经生下儿子的曾阿姨在亲戚的鼓舞下,坐了40多个小时的火车,毅然南下来到深圳打拼。“听说这里工资高,很好找工作,便来了。”抱着这种朴素的想法,曾阿姨辗转在龙岗多个服装厂打工,也在工作中学会了使用各类电子缝纫机器,技艺不断精进。

在工作稳定后,曾阿姨和丈夫都搬来了福田梅林片区居住,并于2004年生下女儿。因为要带孩子,曾阿姨辞掉了工作。又因为想补贴家用,她开始在家接一点针线活儿来做。丰富的工作经历,加上细致贴心的服务,让曾阿姨的缝纫手艺在周围一带传开了,很多人慕名前来,甚至有人搬家到龙岗后,依然乘车过来,把一包衣服交给她来改。

曾阿姨在与顾客沟通。
在缝缝补补中,时间的针脚也不断向前。如今,曾阿姨的孩子都长大成人;她做了2次大的手术,所幸均无大碍;她的裁缝铺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那原本肌理粗糙的平凡生活,在曾阿姨用一针一线构筑起的温馨日常里,被反复摩挲,逐渐变得柔软,正绽放出丝绸般温润的光泽。

曾阿姨将需求便签缝在顾客的袋子上。
聊天的间隙,一束阳光打在布料抖落的微尘上,光的形状也被定格在那。曾阿姨轻点一下缝纫机踏板,在“哒哒”的声响中,继续拉着家常。
“我们一家终于攒了钱在成都买了房子啦!”
“儿子几年前结婚了,生了个可爱的孙子咧。”
“女儿在医院实习,最近遇到了烦心事,发来微信诉苦,晚上要给打电话宽慰宽慰她。”
……
日子就这样静静流淌着。
(原标题《深圳Living | 街角小裁缝:在针头线脑里触摸生活的肌理》)
编辑 李斌 审读 刘春生 二审 王雯 三审 刘一平
 读特热榜
读特热榜
 IN视频
IN视频
 鹏友圈
鹏友圈

11月9日,我们将迎来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十五运”)。赛事临近,无论你是投身运动热潮、感受竞技魅力,还是想为拼搏健儿传递心意,都不妨来鹏友圈,留下对“十五运”的专属祝福!带上话题#我为十五运加油#,一同为运动健儿呐喊助威,为“十五运”热烈喝彩! 【本期话题】#我为十五运加油# 【活动礼品】读特积分、优质动态随机掉落深圳盒子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1月22日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已进入冲刺倒计时,想解锁超省心的观赛方式?赶紧打开“十五运全景魔方”(https://huodong.dutenews.com/H5/nationalGame/pc),一键解锁观赛全攻略!无论是赛事速递、赛程全览,还是购票指南、规则科普,都能在这里轻松找到!快到鹏友圈带话题晒出你的使用截图,和鹏友们分享专属观赛攻略吧! 【本期话题】#十五运观赛神器# 【活动礼品】读特积分、优质动态随机掉落深圳盒子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1月22日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将于2025年11月9日举办。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十五运会”)会徽以“繁荣、包容”为立意,撷取礼花绽放瞬间,由三朵花瓣交叠旋转形成图案,通过提取花朵外形和色彩,环绕花心螺旋围合一体,形成同心礼花,寓意粤港澳大湾区交融互通、活力无限,背靠祖国、绽放世界。 十五运会会徽图案由代表粤港澳三地的花瓣交叠旋转而成。
 00:07
00:07山东省烟台市开发区黄金河鱼群风景
- 友情链接: 深圳新闻网
- 粤ICP备10228864号
- 粤公网安备 44030402000917号
- Copyright @1997-2023 深圳特区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