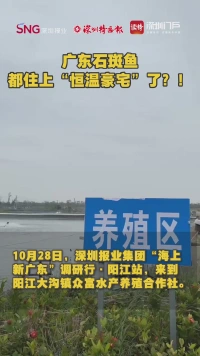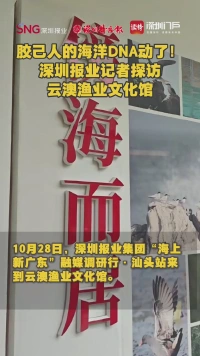近日,南通市一位15岁少年因制止校园欺凌,而被14岁的同学伙同19岁“社会大哥”殴打致死的新闻,再次刺痛人们神经。
本月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白皮书对近五年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进行梳理,发现尽管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总体趋势明显下降,但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奸犯罪人数近年来逐年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容忽视。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普及,未成年人心智“早熟”已经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开始出现规模化、预谋化、低龄化的倾向。近年来,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犯罪者熟练使用“低龄”当挡箭牌,甚至出现了未成年人“帮派”等类黑社会组织,这些事实挑战了公正的底线。南通的这起案件中,我们也嗅到了组织化犯罪的味道。因此,有舆论开始担忧,对此案未成年嫌疑人的处罚会不会太轻,以至无法彰显正义。
未成年人尚未定型,一时走了歪路,社会、家庭、学校也有一定责任。因此,不该单纯用惩罚成年人的手段惩罚他们。如何宽严相济地惩罚未成年人犯罪,既让他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又能够矫正其行为,使他们能在若干年后重返社会,是激愤之后应当好好反思的社会问题。
作为特殊教育的组成部分,工读学校兼具惩戒和教育功能,能够体现宽严相济的惩罚精神,是很多国家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犯罪的有力机构。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态势,说明普通教育和家庭教育,对于一些“问题少年”已经收效甚微。把一部分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送到工读学校就读,使其接受强制性纪律的约束和管理,能阻断其团伙串联犯罪的可能,培养他们对法律和纪律的尊重,以达到教育矫正的目的。
但在我国的实践中,工读学校运行效能并未被完全释放。据媒体报道,因为工读学校招生需要家长、学生、学校三方同意,不再具备强制力,不少工读学校多年没有生源;工读学校被污名化,工读学生融入社会后仍遭歧视,影响了工读改造积极性;工读学校工作压力大,专职师资面临缺口,办学水平良莠不齐,也可能造成“问题少年”扎堆的新问题。
工读学校的运转,需要得到社会有效监督,也需要更多专业力量的全面支撑,政府很难“包打天下”。破解实践中的难题,还需借助社会共建共治之力。
在录取方面,在现行法律规定下,司法和社区应当通力合作,对相关家庭尽到劝说之责,争取家长和学生对工读学校的认可,在家长未尽监护权等一些特殊情况下,应当代行或寻找称职的少儿福利机构代行监护职责,将有工读必要和需要的未成年人尽早转入工读学校。社区也应配合工读学校,加强对工读生的了解和关怀,为他们提供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等岗位,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回报社会,提高社会对于工读生的整体评价,扭转“工读生=少管犯”的错误认知。
在学校运行方面,在坚持公立为主的原则下,适当引入社会资本和力量参与办学,更好解决师资问题;与企业深度合作,强化产学结合,给工读生重返社会提供帮助和辅导;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办学,对工读学校办学进行监督规范,对未成年人心理问题进行及时干预,防止管教过度伤害未成年人权益。
法律上的惩罚不是作为复仇的工具,而是作为纠正罪犯过错的工具——纠正比复仇要艰巨,但并不能因其难而选择绕路。从另一个角度看,未成年犯罪者的人生,同样也是一场悲剧。“仁爱只有当其生长于正义岩石的缝隙中,才能开花。”让他们得到公正的惩罚,帮助他们走上人生正途,才能彰显出文明社会的光辉力量。
编辑 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