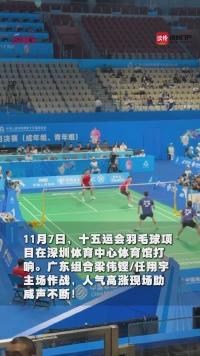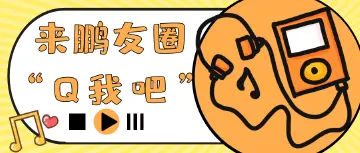“你去哪里?”
一名戴着口罩的保安员从黑色的岗亭里探出半截身子,朝着汽车驾驶座的方向喊去。大约两秒钟后,保安员握着一个体温计走出岗亭。车上的乘客不约而同地挽起袖子,把手臂伸出车窗,给保安员测量体温。尔后,闸门缓缓升起,重启引擎的汽车缓缓驶入停车场,随即远离了视线。
“这是我每天发呆的景色。”站在酒店房间里望向窗外的王宇逐渐习惯了这样陌生的画面。
一周前,这个19岁男孩像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踏上回国的路。他从英国巴斯出发,辗转伦敦、苏黎世、香港、上海,经过96个小时曲折回到深圳,并开始了为期14天的酒店隔离生活。
与王宇同住一层楼的,还有一个叫王杰的19岁男孩——王宇的双胞胎弟弟,前不久也加入留学生回国队伍。如今兄弟俩相距几步路,但因为隔离期,“到现在都还没见上一面”。

英国时间3月20日的伦敦城市机场。
回,还是不回?19岁生日时面临的“选择题”
从3月24日入住酒店计算起,王宇的隔离生活已经过去了一半。“大部分还是在倒时差。因为这边一天要测量两次体温,所以现在时差差不多倒过来了。”3月27日,王宇通过视频通话接受了晶报记者的采访。
王宇居住的是一家经济型酒店,坐落在南山区东滨路上。酒店方圆一公里内有3家大型购物商场,娱乐设施、各式餐厅数不胜数。但对于王宇来说,这里的繁华闹市与自己无多大关系——在酒店隔离的14天里,王宇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面积20平米左右的酒店房间。“除了不能点外卖之外,其他都很好。”王宇笑笑说。
同样的回答,也出现在3月28日的一次视频采访里。这天,和王宇一样想念外卖的是他的双胞胎弟弟王杰——3月24日凌晨,王杰紧随哥哥的脚步从英国回到深圳,并入住同一家酒店开始了为期14天的隔离生活。
难以想象的是,这两个在电脑屏幕里谈笑风生的19岁男孩,才在一星期前经历过一场险象环生的曲折回国路。
把时间拨回到英国时间3月12日,这一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英国进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延缓”阶段,将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应对新冠疫情。“那一天开始,我认识的大部分留学生都开始有些慌张。”王宇说。
英国时间3月12日也是双胞胎兄弟的生日,但他们把几乎全部心思都聚焦在了“是否回国”这道选择题上。
弟弟王杰是最早提出回国计划的人。相较于身处英国小城巴斯的哥哥,在伦敦就读大学的王杰更早发现了疫情的严峻。“伦敦在3月初就已经有确诊病例了。到3月12日就发现整个英国的确诊病例每天都增加得很快。”王杰说,当时身边有很多同学都已决定要回国,或者有一些已经在回国的路上。
王杰向爸妈和哥哥提出了回国的打算。但由于学校方面还没有发布取消课程和考试的通知,课业压力较大的哥哥不敢轻举妄动,爸妈暂且只能先远程帮忙留意机票。
“因为很多航班临时取消,为了确保孩子能回国,家长和孩子们建群研究各种攻略。”妈妈还记得,当时从香港飞往国内城市的机票也很紧俏,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海口和厦门。
据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统计,从当地时间3月13日早9点到14日早9点,英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2人,累计确诊病例1140人。其中包括一名来自王杰就读的伦敦大学学生。当天开始,包括伦敦大学在内的多所英国高校相继宣布停课并取消所有考试安排。这让兄弟俩的回国计划终于没有了后顾之忧。

双胞胎弟弟在飞机上的防护。英国机场登机口几乎“白色”一片。
“15号(英国时间)准备买机票的时候就发现,基本上直飞内地的机票都没有了。”王杰说,爸爸最初的建议是飞香港或广州这两个距离深圳较近的城市,由于飞往广州的机票已经抢不到,只好定下3月21日(英国时间)飞往香港的机票。
原本以为,一切都妥当了。“老公开始用手机跟儿子讨论飞机上的防护措施,教他们防护三个‘输入口’。”面对这场如冒险一般的回国计划,孩子的爸妈总会忍不住提心吊胆。他们在微信群里再三提醒孩子,一路上注意防护,遵守当地防控规定。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一定会回家的,别担心,不然我们俩压力会更大。”兄弟俩在微信群里告诉爸妈,同学们成立了很多个互助微信群,先走的会告诉后面出发的同学,怎么走才会顺利。况且,他们早已准备好了口罩、护目镜、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
弟弟王杰在伦敦大学就读医学相关专业,疫情爆发初期曾翻看过不少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文献,专业上的认知减少了他对病毒传染的担忧。王杰准备了一个密封袋,把几个一次性医用头套、一次性塑胶手套、N95口罩、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酒精棉片、消毒液、洗手液等都装进袋里,作为路途中备用。同时,他把防护服、护目镜和一个N95口罩另外装好,等出发时换上。
王杰说,那段时间英国的防疫物资都卖得很贵,1月底买了100多个口罩寄回国内,当时只需大约6英镑。之后再购买的一批50个医用外科口罩,就已经涨到了40英镑。“跟他们买一般不缺货,但都要半个月左右才能送过来,所以要提前备好。”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3月17日,香港特区政府宣布,为防止新冠病毒从海外输入,从19日零时起,实施入境人士强制检疫措施,入境人士须接受14天的强制居家隔离。而王杰持有的护照签证无法在香港逗留至14天,他不得不考虑其他返深路线。
王杰原本打算从香港转飞海口再折返深圳,但海口也发布了针对入境人士集中隔离的措施。最后,王杰不得不选择距离深圳更远的上海作为内地的中转城市。
英国时间3月21日上午11点,距离飞机起飞还有6个多小时,王杰已从学校宿舍出发,坐上一辆Uber网约车前往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路上,王杰全程戴着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即便是在确诊病例每日剧增的伦敦,这样的打扮依然不多见。“大部分英国人或者说外国人都不怎么采取防护措施,包括我坐的Uber的司机也没有戴口罩。英国的民众对疫情还是不太重视。”王杰记得,初次与司机见面时,司机热情地向他打了声招呼,在得知自己回中国的行程后,司机还对中国疫情防控向好的变化发出了一句感叹。
抵达机场后,王杰在洗手间穿好防护服和护目镜,把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换成N95口罩。“一到登机口就看到几乎全是白色——大家都穿了防护服或者雨衣。”王杰说,候机的大部分都是中国留学生或者海外华裔,大家的防护措施都做得很严密。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201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教育部2019年公布的出国留学数据显示,2018年出国留学人数在上年基础上再增5.37万人,增长8.83%。另据央视新闻3月25日报道,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已有22万,其中14岁以下的小留学生就达到了1.5万人。
疫情当前,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回国成为大部分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的第一选择。

哥哥(右)和同学在前往伦敦城市机场的路上。
11个小时不上厕所,两天用完3瓶洗手液
不同于弟弟直飞中国,王宇却选择了一条更加曲折的回国路线。
王宇计划从巴斯前往伦敦,并在伦敦城市机场搭乘飞往瑞士苏黎世的航班,之后再辗转香港、上海,最后抵达深圳。这是他在查看多个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的行程轨迹后,做下的决定。
“我选了一个稍微冷门一点的线路,从瑞士转机,没有去迪拜或者直飞,因为这样的安全性可能稍微高一点。”王宇说,伦敦城市机场是个小型机场,对比希思罗国际机场的庞大客流量,病毒传染的几率似乎会更小一些。
路线规划好的当晚,王宇立即花费一万多元买下了往返的机票。第二天早上,王宇的同学决定一起回国时,却发现用同样的价钱却只能买到单程票,“在他买完那张票之后,整趟班机就没有再多的票可以买了”。
“大部分直飞的经济舱的价格都已经上到了两三万元,而且也是一票难求。”王宇回忆说,那段时间许多留学生都在刷票,有的同学就只能抢到4月初或者3月底的航班,价格也比较贵。
英国时间3月20日上午,王宇顺利搭乘飞往瑞士苏黎世的航班。由于航班晚点,到达苏黎世的时候仅剩下一个多小时的转机时间。担心错过航班的王宇一路小跑,登上飞机的一瞬间,心中悬起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哥哥在瑞士苏黎世机场转机时候看到通知,机场休息室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都已关闭。
在王宇搭乘的回国航班上,有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士,中国留学生基本都被安排坐在同一个片区。王宇发现,大部分人都佩戴了口罩、手套和护目镜或者是眼镜,有少部分甚至是穿上了防护服,甚至还有一些人选择全程不吃不喝。
“我没有穿防护服,但是护目镜、口罩、眼镜和手套基本上都是全程佩戴。”王宇说,一路上不管走到哪里都先用酒精棉片或酒精消毒液先擦拭。摘下口罩或者摘下手套之前也要先洗手消毒,摘下手套后每隔一两分钟再洗一次手,差不多两天时间就用完了三瓶洗手液。
不同于哥哥的航班,王杰搭乘的航班坐着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海外华裔。在飞行期间,王杰吃了两顿饭。第一顿是在刚上飞机没多久,空姐就给乘客发放了餐食。“我看旁边的人都没有要准备吃饭或者摘掉口罩,我就打算先吃。”王杰火速扒了几口饭,然后赶紧把口罩戴上。直到下飞机前的三、四个小时,王杰又趁着身边乘客睡觉的时候,抓住时机再吃了一些零食垫垫肚子。在这11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王杰忍着没去上一回厕所。
原本10多个小时就能到家的路程,哥哥王宇却用了4天96个小时,从巴斯辗转伦敦、苏黎世、香港、上海曲折回到深圳;而弟弟王杰也经历了52个小时的漫漫长路。兄弟俩每抵达一个地方,就给远在家乡的爸妈发去一条信息,让爸妈放心。
随着3月23日飞机在深圳先后落地,这对双胞胎兄弟从英国的“艰难撤离”终于结束。

弟弟在上海虹桥机场转机等候区拍摄的画面。
落地,8小时重重检验,滴水不漏
“其实到了上海入境的那一刻,心里就已经放松下来了。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回来了。不管出现任何事,我们都回到家了。”在采访中,王宇、王杰不约而同地感慨道。
对于许多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而言,安全感的回归是从见到“全副武装”的中国人在飞机外驻守等候的那一刻开始的。
王宇还记得,飞机在深圳降落一两个小时后开始陆续放客。包括王宇在内的几名从境外返深的留学生被安排坐在飞机的最后三排,等其他乘客全部离开之后,他们再下飞机搭乘专门安排的摆渡车,前往停机坪上的一个指定地点。大约半小时后,他们根据工作人员登记的情况和指引,继续前往机场大巴的分流区,几小时之后再陆续搭乘大巴前往深圳湾。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隔离酒店办理入住。
从飞机落地到抵达酒店,这群留学生历经长达8个多小时的重重检验,包括测量体温、核酸检测、健康申报等等。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等待上,但王宇发现,现场没有留学生露出反感情绪,“大家都能理解而且遵守、配合,没有人表现出不耐烦或者为难工作人员。”
趁着兄弟俩相继在隔离酒店办理手续的空挡,孩子的爸妈两次跑到隔离酒店,远远地见了一面日思夜想的儿子们。“看到实实在在的他们站在不远处,我的心终于彻底踏实了。”妈妈感慨道。
兄弟俩入住酒店的第二天清早,工作人员便传来消息,“前一晚入住酒店的所有人员的核酸检测结果都呈阴性,但出于安全考虑需要隔离14天。”
此时,兄弟俩都彻底松了一口气。

兄弟俩抵达深圳后入住酒店隔离。
在酒店,倒时差、上网课、写论文、微信聊天成为兄弟俩的隔离生活日常。“前段时间家里的猫咪产下了5只小猫,我们还商量给它们分别起什么名字好。”王杰笑笑说,住进酒店快一星期了,也没法跟哥哥王宇见上面,平时只能通过微信聊天,关心一下对方的身体检查情况。
隔离期间,一日三餐都由工作人员派发到每个房间门口的板凳上。隔离人员开门取餐,吃完后再把餐盒放回门口的板凳上,由工作人员陆续收走。王杰习惯了在房门把手上挂一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每次听到门铃响时,他都不会忘记先戴上口罩再打开房门。
▲在酒店隔离期间,一日三餐都由工作人员派发至房间门口的板凳上,再通知隔离人员开门领取。
“吃的都挺好,而且每天都送来水果。因为实在吃不完,现在都堆起来了。”王宇说,街道办还组织了关爱留学生的活动,给隔离在酒店的留学生送去了牛奶、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虽然不能点外卖但还是得好好配合隔离。”同样收到礼品的王杰拍了张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写下了一句感慨。

在酒店隔离期间,爸妈给哥哥送来了“娱乐设施”。
“第一次在机场过夜。”
“第一次辗转了这么多个城市才回到家。”
“第一次在路上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第一次……”是王宇、王杰频繁提起的字眼。对于这对双胞胎兄弟而言,由这场疫情所引发的长达近百小时的回国经历,将像烙印一般被深深印刻在他们的成长轨迹里。
“在抖音上也看到过许多留学生回国的视频。”王杰说,他看到有历经20多个小时回国的,也有历经40多个小时回国的,“每次‘刷’到这样的视频都会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在这场疫情面前,除了王宇、王杰,还有更多的海外留学生选择了“回国”这个答案。
因为不管何时,“家”依然是最令人安心的地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名字均为化名)
(晶报供稿)
编辑 李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