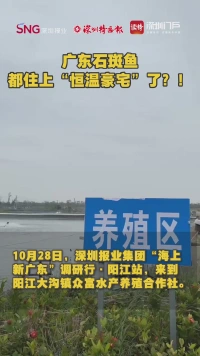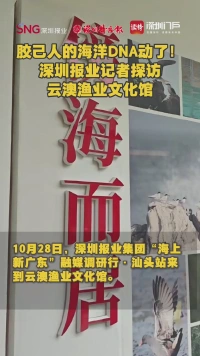今年的3月12日,是“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诞辰98年周年纪念日。和往年诞辰不同的是,今年也是凯鲁亚克作品在中国进入公版期的第一年。凯鲁亚克于1969年去世,而根据中国的著作权法规定,作家去世50年后,其作品即进入公共版权领域。
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1922年3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迷恋歌德、雨果等人的作品,自小生性腼腆却喜欢运动,还有携带笔记本记录周围人和事的习惯。
1939年,17岁的凯鲁亚克凭借橄榄球奖学金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大二时因为和教练发生争执而退学。此后他一边阅读、写作,一边在服装厂、修理站和餐馆打杂工,做过体育记者,在商船上做过帮厨。凯鲁亚克还加入过美国海军陆战队,但仅服役了8天,就因为“强烈的精神分裂症”倾向,因此而被遣散。
从部队退役回到纽约后,凯鲁亚克结识了一群思想独立、放浪不羁的年轻作家,其中有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代表作《嚎叫》)和作家威廉·巴勒斯(代表作《裸体午餐》)等,他们构成了“垮掉的一代”的核心成员。这群年轻人性格豪放,大胆不羁,他们疯狂纵欲,沉沦于性爱和酗酒,还一起横穿全美一直流浪到墨西哥。
这段流浪的经历,让凯鲁亚克创作出了《在路上》,小说中的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迪恩、玛丽露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国大陆。一路上狂欢滥饮,无休无止的纵欲和性爱,从纽约到旧金山,又到达墨西哥,最后回到纽约。
1957年,《在路上》问世,凯鲁亚克一夜成名,被封为“垮掉派之王”。巨大名声成就了凯鲁亚克,也变成他很大的负累,而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酗酒。在随后的几年里,凯鲁亚克创作了《达摩流浪汉》《孤独的旅人》等几部作品,但由于纵酒过度,他陷入了神思恍惚的状态,文学产出不断减少。
1969年10月21日,他因腹部大范围出血与世长辞,死时手中还拿着笔和本子,终年47岁。乔伊斯·约翰逊说:“对于凯鲁亚克,写作是一场反抗虚无感和绝望感的战争,它们经常淹没他,无论他的生活看上去多么安稳。他曾经说,当他老了后,他绝不会感到厌倦,因为他可以捧读自己过去的所有冒险史。”
作为“垮掉派”的灵魂人物,凯鲁亚克在中国也影响深远,其作品也广受出版商和读者青睐。近期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五种以上的新版《在路上》,包括读客、99读书人、博集天卷、果麦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多个版本。
本文从《在路上》开始讲起,回溯凯鲁亚克的文学之路。
凯鲁亚克版权大战·《在路上》不同版本

读客版 姚向辉 译 2020年1月

博集天卷版 何颖怡 译 2020年1月

湖南文艺出版社 陈杰 译 2020年1月

世纪文景版 陶跃庆 何小丽 译 2020年1月

果麦版 杨蔚 译 2020年3月

99读书人版 秦传安 2020年3月
“在路上”进行的三次测绘
“……我只觉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有如鬼魂附身的幽灵人。我已经跨越半个美国,站在人生的分水岭,身后是我在东部的年轻岁月,前方是我在西部的未来时光……”很少有美国作家尝试将东部和西部并峙在一起谈论,凯鲁亚克是一个例外。在《在路上》中,迪安用喜剧性的口吻讲道,“东部厕所都是一些插科打诨、淫秽的文字与图画;西部人只会在厕所写自己的名字,到此一游,某年某月某日……”它所讲不止于地域。如果你用心倾听,你会明白它讲出了渴望,去寻找去征服的渴望,这样的渴望联结了欲望和梦想。
凯鲁亚克将讲故事的尺度扩大到了流动的美国版图,而不再是既定地追随密西西比河,像马克·吐温那样,他不再将自己视为作家,而是地理测绘师。
《在路上》便是凯鲁亚克对美国(最后一次有墨西哥)进行三次测绘的成果,它讲述了萨尔在往返于纽约和旧金山或者墨西哥城的旅途上的所见所闻。与主观视角下的第一人称叙述不同,它杂糅了日记和随笔的叙述方式,也从被美国文学本土化的成长小说中汲取了养料,但更随意和传统。
在很多故事里,主角是迪安,而不是萨尔。迪安是萨尔痴迷的“垮掉的一代”。在萨尔的心中,迪安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兰波、丹佛市长,但迪安也被卡罗尔戏言“俄狄浦斯·埃迪以饱受折磨的阳具扛起所有苦痛”。作为萨尔的那喀索斯对象,迪安对于女人、毒品、飙车、爵士乐和任何一种自由狂野都有着旺盛的欲求,他结了三次婚,现在却在玛丽露和卡米尔之间周旋,他把皮箱放在床下,随时准备被扫地出门和闪人。他在同伴中扮演着先知角色,就连随口而出的漂亮话也有着浪漫奇幻的召唤力,他这样说道,“烦恼乃上帝存在之处的总称”……“我们都了解时间的奥义”……
迪安之于《在路上》,就如凯鲁亚克之于“垮掉的一代”,海明威之于“迷惘的一代”。中国对于“垮掉的一代”的想象抹除了“Beat”作为至福的含义。在“垮掉的一代”的坐标轴上,“自由”作为定点,“垮掉”和“至福”作为另外两点,构成了“垮掉”的抛物线。
“垮掉的一代”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联系着“愤怒的一代”“回归的一代”,联系着二战后的文化政治现实、后殖民现实、后工业现实和革命现实,它通过将年轻人挤出既定的秩序而将自身置于生存和政治之间,而借由它,后现代潮流流布世界,尽管它不再与梦想和自由有强关系。毛泽东如是形容那个年代,“我们的民族像一个原子。当这原子的核被击碎时,(积聚的)热能将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全球的墒增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第三世界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对于革命的好感和需求转移到生活之上。“精神在先,生活在后”的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先,精神在后”,人们带着非凡的野心去生活,民权运动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例证。

通过旅行,重新诠释自由
凯鲁亚克的公路旅行和文学写作正是其时一种能量流溢的路径。通过旅行,通过迁徙,通过爱,他重新唤醒了美国英雄。他重新诠释了自由。他将他所认可的自由地生活的人们塞进了这本他寄予厚望的作品里,除了迪安和他的两位妻子玛丽露和卡米尔之外,还有流浪汉吉恩、服务员丽塔、黑人雷米、采葡萄工特丽、传奇人士布尔、作家欣厄姆,以及众多在频繁切换的场景中闪现的美国公民。
丽塔和特丽和萨尔都有过一段爱情/婚姻生活,但没有涉及承诺、责任,爱情浮现在日常之中,然后将空间和光彩留给新的爱情。他这样写和特丽的恋爱,“我们就像两个疲惫至极的天使,绝望地搁浅于洛杉矶的礁岩之上,突然间,一起找到了生活中最亲密最甜美的东西……”老布尔或许是凯鲁亚克为“垮掉的一代”所安置的一个灯塔,他将“垮掉的一代”又往前追溯了三十年,且置于世界的舞台之上。老布尔的足迹遍布世界,他在芝加哥策划抢劫土耳其澡堂,在纽瓦克替法院送过传票,在大学时代因为宠物雪貂射出了一个巨大的洞,在1930年代和国际可卡因走私集团合过影,他热爱吗啡、大麻、傻瓜丸、安非明、烈精,在一个暗夜,他就着卡夫卡,吐露着对于官僚、工会的憎恨。
凯鲁亚克的描述并非幻想。在战后,随着战争和阴霾消失,人们的道德热情和传统信念与站前相比松动了很多,也真诚了很多。自由主义还是一个新生儿,冷战还没有到来,这时的世界有一种乌托邦式的乐观精神。青年作为一种崭新的力量得到了更广泛的确认,甚至可以说,青年成为了社会的主导。人们成立了“共在会”“共爱社”和“群居村”,在里面的人们秉持着最自由最富友爱的准则,“所有的女孩都是我的太太,所有的男孩都是我的兄弟,而婴儿都是我的,这就是爱。”与此同时,早期在文学中呈现出来的波西米亚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实的游荡者和反叛者不再享有它们的荣耀,反叛被分发给每一个角色。
这位自称“奔跑的普鲁斯特”的橄榄球手也并未在作品中过分地夸耀自己,甚至将自己的身价放低,退隐在热情奔放的群像之中。这位冒险家看起来甚至有点蹩脚,他常常为了旅费而窘迫,在营区值班他醉酒把国旗倒挂了上去,因为无处投宿在影院的烟蒂堆、垃圾里睡了一宿,直到第二天黎明被清扫现场的人吵醒。这些故事很显然窃取自传统,或者现实中的素材。然而也正是在这有点呆板、古老的文体之上,一种新鲜带有锐度的乐观情调和故事激情发生了,一种与冉冉上升的世界一同加速的文学产生了。
和几乎同期发生的存在主义不同,凯鲁亚克展现了世俗生活所能激发的力量和可能。艾伦·金斯堡、鲍勃·迪伦处在同一个位置,处在美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如特里林所说的“强悍、凶猛、自信和好斗”。1955年,他们用由此发扬开来的诗歌朗读,将一种融合了神秘、政治和欲望的诗歌推广了出去,复兴了旧金山诗歌,复兴了集体体验,复兴了口头文学传统,也复兴了惠特曼的文学传统。而今,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世界再也不是那样了。我们不再那么自然而无畏地接受壮举和虚无。凯鲁亚克对于未来的猜想和许诺也失落了,过去成为一个被诅咒和被遗忘的过去。再也回不来了。

改变了文学,却与最好的想象背道而驰
凯鲁亚克所处的美国文学史正是第二代现代主义作家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未来的时期,他们没有因循T·S·艾略特和海明威的踪迹,而是各自寻求,开创了一个多元和丰富的文学局面,这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最为汩汩的时期。凯鲁亚克既是传统的,又是激进的;他的传统表现在文体和叙述,他的激进表现在精神,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这是“一种新感受力”。从此后和当下的文学向前追溯,凯鲁亚克所表达的并不是一个乍现的潮流,而是一个文学的新的开端。
凯鲁亚克如是改变了文学,文学不再是一种世俗化的故事演绎,而成为一个改造意识、塑造新的感受力的工具。文学再一次地被前置,但并不是大陆学者所宣称的后现代之杂粹和狂欢。这一点可以从凯鲁亚克的写作方式上看出。写作之初,他将稿纸粘连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卷筒纸,保证在写作中不被打断。在写作中,他调用了一种被称作自发性波普爵上乐写作法的写作方式,用近乎禅修和爵士乐的方式,不加句号、用思维速写、跟随节奏演奏,打出了120英尺的长度。在三个星期内,他非理性的贪欲席卷了他的记忆和灵感,他编纂了“狂野的,混乱的,纯真的,从心底里涌现的一切”。类似的信念伴随他一生,他在一篇文章里引述了《首楞严经》,“若指望理解更多至高启示,务必学会本能回答问题,不要寻求援助,歧视思维”。这或许就是当下文学在表层中流溢速度和美的原因所在。
而这连接着“beat”作为至福的一面,也连接着由禅出发的“因为我一无所有,所以一切皆归于我”( Everything belongs to me because i am poor),同时还连接着“地球乃印第安人所有( The earth is An Indian Thing)”。他设想了一种非凡的人类存在,瓦解掉了殖民问题、族裔问题、身份问题,这或许是有史以来文学对于人类作出的最奇妙、最美好的想象。
然而,凯鲁亚克却与他的想象背道而驰。就在完成《在路上》不久,这位法裔加拿大人就猝然终止了婚姻,强迫琼·哈弗蒂堕胎,并四处逃窜,拒绝妻子的抚养费诉求。他对毒品没有瘾,但他酗酒,酒后好斗,连金斯堡也招架不住他了。他是他的朋友中最不幸的人,孤苦伶仃,他从始至终都幻想着生活在大农庄里。他越来越不认同自己是“垮掉的一代”,而将自己看作是天主教徒,尤其是在晚期生活中,他的绝望让他依附于十字架,他画了很多基督主题的画作。他喜欢在深夜写作,当整个世界都在沉睡时,他独自一人在灯光烛火里畅游到清晨,但他逐渐厌弃了写作,也丢掉了寒山。他搬去了佛罗里达,安置了母亲和新的妻子,时间轻而易举地打发了凯鲁亚克。在最后的文章中,他写道,“我在午夜醒来时,我意识到他说的是对的,存在中肉体的痛苦是一种十分敏感的痛苦,这种感觉比政治上的愤怒和希望更加强烈,就像我正躺在床上慢慢死去一样……”他死于1969年10月21日,没有阳光,只有从收音机里播放出的大音量的《弥赛亚》。
就像历史中的那个年代的人们一样,凯鲁亚克被异化、孤独的人群、文化产业封堵在一个窘迫的现场中,来自俳句或禅或任何其他的智慧并没有让他活得足够长。和托马斯·沃尔夫和普鲁斯特一样,他将文学书写成一种包容了人生和未来的长卷。正如金斯堡在阅读他的《墨西哥城布鲁斯》所意识到的那样,凯鲁亚克开创了一种反对修改和未经修改的美学,而如今我们越来越继承了这一“存在即诗”“呈现即诗”的美学。后世的读者在追随凯鲁亚克在路上自由地游荡和生活时,总是会这样说,“我们突然觉得世界是个牡蛎,等着我们打开,发现里面的珍珠,珍珠就在里面。”他们分不清这是凯鲁亚克的话,还是他们自己的。
作者:后商
独家原创内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晶报供稿)
编辑 李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