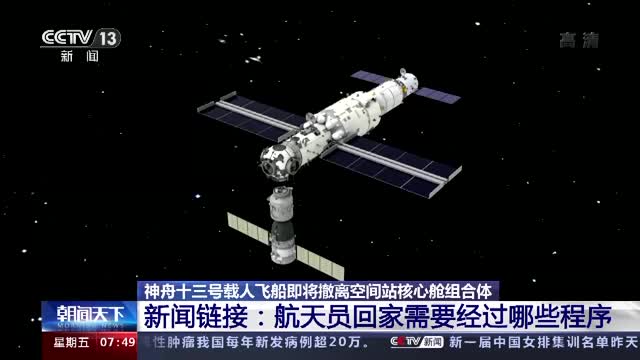阅读《云游》并非轻松的事,感觉像一次太空漫游,文本、叙事与指涉都被剪裁细碎,116篇文字如星群般散落,看似各不相干,也没有清晰的时间轴与情节主线,随便拾起一篇皆能独立成章。在这团混沌的文字星云中人很容易迷失方向,阅读成了一场考验耐心与想象力的冒险探索,但当你持续移动,拉开距离俯瞰时,会发现篇章间的深层联系,彼此的互文、映照和拼贴如无形的“引力波”把它们统摄在一个动态整体中,非线性的无序实质是更高维度上的有序,破碎、混杂与多元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本身。
《云游》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于2007年出版的作品,英文书名为“Flights”,中文版译作《云游》。此书荣膺2018年国际布克奖,评委会称其为非常规化去传统化的叙述,能让读者进入一个如星轨环绕的想象世界,小说“在机智和快乐的恶作剧之下,发掘出人类真正的情感结构。”至此,“星群小说”成了托卡尔丘克的一个鲜明标签。她更早的作品《太古和其他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即显示出这种碎片化写作特征,尤其是后者把小说、散文、传记、书信等各种文体糅合成一部意涵丰厚的小说,叙述主题多样,修辞风格混杂,主旨隐晦,全书看似没有明显的结构主线;然而当把这些短篇稍加整合,却又透显出一股内部的聚力与逻辑联结,仿佛是状若离散实质运行在同一星系中的星群。
与《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以下简称《白天》)相比,《云游》在观察视野和思考主题上都有了变化,呈现出更纯熟、更国际化的时代气质和张力。如果说托卡尔丘克在《白天》中的角色是一位隐居荒野,执着于梦境、历史与神话的神秘主义者,以家乡下西里西亚所象征的文化寻根为其创作核心,观照波兰的历史与现实生活。那么《云游》里她则走出家乡,化身世界公民,穿梭在各大机场、城市与人体博物馆里——不断探索运动与生命,形而上与科学,时空结构与人体内部的互文关系,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下人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成了她新的书写对象。

《云游》 于是 译,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年1月。
境遇
《云游》仍沿袭了《白天》的碎片化写作模式,托卡尔丘克解释是为了顺应互联网时代人们碎片化阅读和处理信息的习惯,但撇开这个因素,从更深层的民族历史背景来说,碎片化叙事也许更契合托卡尔丘克的文化语境。托卡尔丘克是波兰人,波兰是多民族混居国家,其版图千百年来始终不断变化,二战后,波兰从德国手中收复西部和北部的疆土,却以丧失东部疆土为代价。国境的断裂,人们的流徙都给予托卡尔丘克对自身历史、文化及世界的强烈不稳定感,混杂、移动和碎片成为她理解生命的一种方式,正如她在书中所写“无需试图让人的生活有连续性,哪怕是近似连续的状态。生活是由各种境遇组成。”
托卡尔丘克的认知或许并非仅是个人感受。事实上,在波兰隔壁的德国,自东西柏林墙倒下后,整个德语文坛也经历着巨大的“裂变感”,“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曾经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具有高度整体性的意识形态散裂了。现实的剧变引发新的文学思考,传统的历史宏大叙事让位于个人化的小叙事,碎片化的拼贴书写和“破碎现实主义”成了新世纪德语文坛的潮流,按乌尔里希·吕登瑙尔的话说就是“身处一个已散裂成千个碎片的宇宙中,个人已无法进行宏大叙事”。像列维恰洛夫、赫塔·米勒等德语作家的作品,皆呈现出强烈的碎片化风格,以记忆的“碎片”寓意历史真相的断裂和离散,以个人生活的“碎片”寓意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总体性”的虚假表象,而拼贴“碎片”不仅是还原历史的整体性过程,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挖掘世界真相的体现。
由此看来,托卡尔丘克所秉持的文学宇宙观“星群组合,而非定序排列,蕴含了真相”仿佛是对上述文学思潮流变的一种呼应,也仿佛是地理与文化接壤的两位“邻居”对近似生存境况的某种共识。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易丽君 袁汉镕 译,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但必须指出的是,碎片化若只有“碎”而没有联动,没有供整合的可能性,没有更高层面的共同指涉那只是流于形式的文字游戏。托卡尔丘克一再表达:作家的头脑应是整合的头脑,顽强地把所有微小的碎片收集起来,试图把它们再次粘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碎”是文学的生存现实也是解构手段,但整合才是最终目的,在《云游》中托卡尔丘克大量使用互文、复制、增殖、拼贴等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对几个论述主题多维展开并衍生关联来实现主旨的整合。
像“人体解剖和塑化标本”“旅行心理学”“移动与时空”等叙述主题,它们反复出现在不同章节里,由不同的人物与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持续衍生出新的涵义与勾连。有时,某章节里某句话会成为另一章节的标题或引语;某章里的梦境会成为另一章的现实;某章里的提问会被另一章解答;某章故事的叙述者会成为下一个故事里被讲述的对象。甚至像是调皮的恶作剧,托卡尔丘克会故意中断故事叙述,隔开好几章才再续前文,而中间隔着的章节里往往隐含着对这个故事的“注脚”与“提示”,但需要读者的细心阅读才能体味。通过频繁地对语义和结构的复制、增殖,《云游》的文本时空呈现生生不息,无限裂变,犹如多重宇宙般的浩瀚感,一种卡尔维诺迷宫式的深邃奇崛之美。读者在阅读过程里会面临挑战,需要不断整理信息片段,才能还原事件的连续性,最终拼贴出完整面目,而拼贴的过程本身就是拨开表象,发掘事实与真相,重组真实世界的表征。
移动
除了重构真实世界,整合对托卡尔丘克来说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模糊边界,消除隔阂。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的演讲中,托卡尔丘克表达了对文学市场商业化导致文学作品被过度分类的不满,认为过度细分如同竖立藩篱,会限制作者的创作自由,阻碍新的叙述方式的诞生。而她本人一直践行多种文体及题材相互糅杂渗透的复合写作,多样性、无边界是其主张的文学审美。
因此《云游》不仅在文体上丰富多样,内容上也涵盖历史、现代生活、生物学、心理学、神话、寓言等诸多领域,但不同的领域实质上也为相同的几个主题服务,托卡尔丘克让它们彼此互文来达至对自我世界观的概括整合。在托卡尔丘克的世界里,万物皆可互文,不仅历史与现实,旅行与心理学,生理学与神学,甚至人体与世界都是一场互文。书中好几个历史人物故事,皆围绕人体解剖的主题进行,加入对意识本源的哲学辩思,表达出人体结构与天体运行相似相通的宇宙观。这种人体与宇宙互文,类似道家“天人合一”的意象屡屡在书中出现:“词语,对后宫的迷宫来说毫无用处。可以想象一下蜂巢,弯折的肠子,身体的内部,耳洞的蜿蜒;”“也许,整个儿神话世界就在我们的身体里?也许,就在人体内部,存在着某种大大小小万物间的彼此映照——传说和英雄,神明和动物,植物的有序与矿物的和谐?”“人体的突然自我膨胀之后就一扫众神,把神明往自我的内部归拢,为他们布置了一个安身之所:就在海马沟和脑干之间,松果体和布洛卡区之间。”……
托卡尔丘克似是要用文字消解人体与外部,神话与现实,科学与形而上的边界来达成自我宇宙体系的构建,探索一种万事万物间进行辩证对话的可能性。在她看来文学、医学、科技、宗教和哲学等领域并非对立,也无颠扑不破的界限,而是互为补充,同为解释世界本质的方法论的不同切面呈现,恰如书中所言:“我们互为互文,把对方转换为文字和大写字母,让彼此永生,将彼此塑化,将彼此浸没在福尔马林溶液般的长篇短句里。”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易丽君 袁汉镕 译,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
托卡尔丘克将人体内部视为世界内部的象征,这个内部又以情感和心理为表征;人在地球上移动或旅行是探索世界外部的行为,而人在旅行和移动中所产生的情感与心理则是连接内外世界的表现。所以她赋予移动和旅行颇为复杂的意涵,也成为《云游》另一个重要的书写主题。
《云游》的波兰书名是Bieguni,此词出自十八世纪俄罗斯东正教的某门派,其信徒相信一直处于移动状态才能避开恶魔的魔爪。托卡尔丘克着迷于这种对移动的崇拜,她相信世界不存在任何恒久之物,甚至都不是因果的,时间也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存在很多“平行时间”,人只有在不断移动中吸收新的信息和事物,与更广阔的时空发生联系,才能从“失去”和停滞中挣脱出来,以实现某种更高层面上的“不朽”。在世界日益互联网化和全球化的今天,移动和互通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便捷出行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飞机、火车、机场、酒店等不只是出行工具和设施,更是人们的生存空间,探究人们在旅途中的心理动能与精神状态实质也是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一种记录。
旅行
基于以上认识,托卡尔丘克为我们讲述了形形色色的旅行故事。故事的主角往往囿于现实生活,为图摆脱而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出行,他们乘搭各种交通工具,游荡于荒凉的海岛,衰败的城市街头,阴暗的地铁站,肮脏的小旅馆和酒馆中,或日复一日航行在一成不变的河面上,孤独、隔离与压抑的氛围无处不在。人物不断在回忆和现实之间穿梭,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境况和生存困惑;梦境和潜意识如影随行,与客观景物交织出浓郁迷离的精神风景,折射出世界的不确定性、荒诞性和断裂性。“追寻”“渴求改变”是这些人物的旅行动机,结局却是每每不同,有些人寻求到某些感悟和解脱;有些人则无论游荡到哪里,都逃不出精神上的“无物之阵”,深陷在因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所造成的异化中,像野兽般困顿于现实大同小异的风景里。
托卡尔丘克像是把旅行当作一种“显影剂”,借此将人复杂的情感结构,与外界产生互动的生发机制显像在我们面前,从内部摄照现代人的种种生命困境和悖谬,并以温柔而富想象力的叙述给予关注、抚慰,体现出社会人文关怀与书写时代的使命感。
为了更好地阐析旅行与人类潜意识精神底层千丝万缕的联结,托卡尔丘克在《云游》中引入“旅行心理学”的概念。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旅行是人类为满足个体自我完善的需要,为充分认识世界的手段,托卡尔丘克在旅途中不断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分割与错位,从而体悟到世界的不连续性,以此印证她的“碎片化”宇宙观。同时,她把旅行或移动的生活视为打破固化秩序的隐喻——无论在思想或现实层面中,用多元的手法在作品里不断对其拉伸、深化,表达出自我独特的,自由无拘的人生哲学理念,就连生死她都看作是一场旅行。
关于旅行、肉体、精神和生死之间的关系,书中有句精妙的比喻“你尽可舍弃墓碑,直接竖起深爱之人的遗体,墓志铭可以这样写:‘某某在此云游数年后,以几岁之龄离开了这具肉身。’”。至此,“云游”的深意从层层叠叠的语境中浮出水面:肉体是灵魂的逆旅,生是人的一段旅程但绝非终点,死亡不过是开启另一段旅程;人生的要义在于“摇摇,走走,摆摆。”,在不断地移动中领悟万物变幻的本质,顺应世界运动的节奏,获得生命在不同向度里的自由。

总的来说,《云游》是一部创作意识超前的作品。尽管仅从表现技巧与小说形式而言,它仍旧是行走在后现代主义框架中,并没有那么“非常规化”的跳脱,书中大量使用互文、复制和增殖来实现对几个论述主题的多层次展开,对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对梦境与现实的重叠、互构,对情节铺陈的故意“短路”等都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但与“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语言与外部世界割裂相比,托卡尔丘克投入更多对人类社会现状及未来发展的关注,尤其是对生态环保问题,依然存在的种族、性别歧视,以及全球化和互联网科技高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乃至地球生存的冲击都给予积极的探讨和反思,带有现实主义的批判态度。她曾说过:“现实主义写法不足以描述这个世界”,但她也写下许多基于事实基础的历史小说,可见“不足以”不代表“不可以”,如何进行融合创新以实现更好的讲故事方法才是她真正的关注点。因此,在《云游》中托卡尔丘克既娴熟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技巧,也重拾传统叙事的哲学辩思与再现社会现实的功能,把“新”与“旧”,虚构与现实兼容并蓄地组合出新的叙事策略,为21世纪欧美后现代主义文学流变的体现。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评价托卡尔丘克的创作是“富有想象力的叙述带有百科全书式的激情,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确实,《云游》一书所展示出来的森罗万象,腾踔横溢的生命力,俯瞰时空与时代的恢弘视野,以及对生命思考的广度与深度都令人惊叹。在托卡尔丘克的笔下,古老的寓言、神话与现代生活场景紧密联系;神秘主义与医学科学互文互映;人体与万物共生共栖;想象与现实,文学与生活,包括国家、种族、性别、宗教、文化之间的边界业已消失,所有生命体都在发展中“互相协助,促进彼此勃发”。她追求的已不仅仅是构建一个奇幻瑰丽的思想宇宙,更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文学生态系统,或者说是一种文学真正介入现实世界,与人类命运全然贴合的更高“生命形态”。
(晶报供稿)
编辑 周晓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