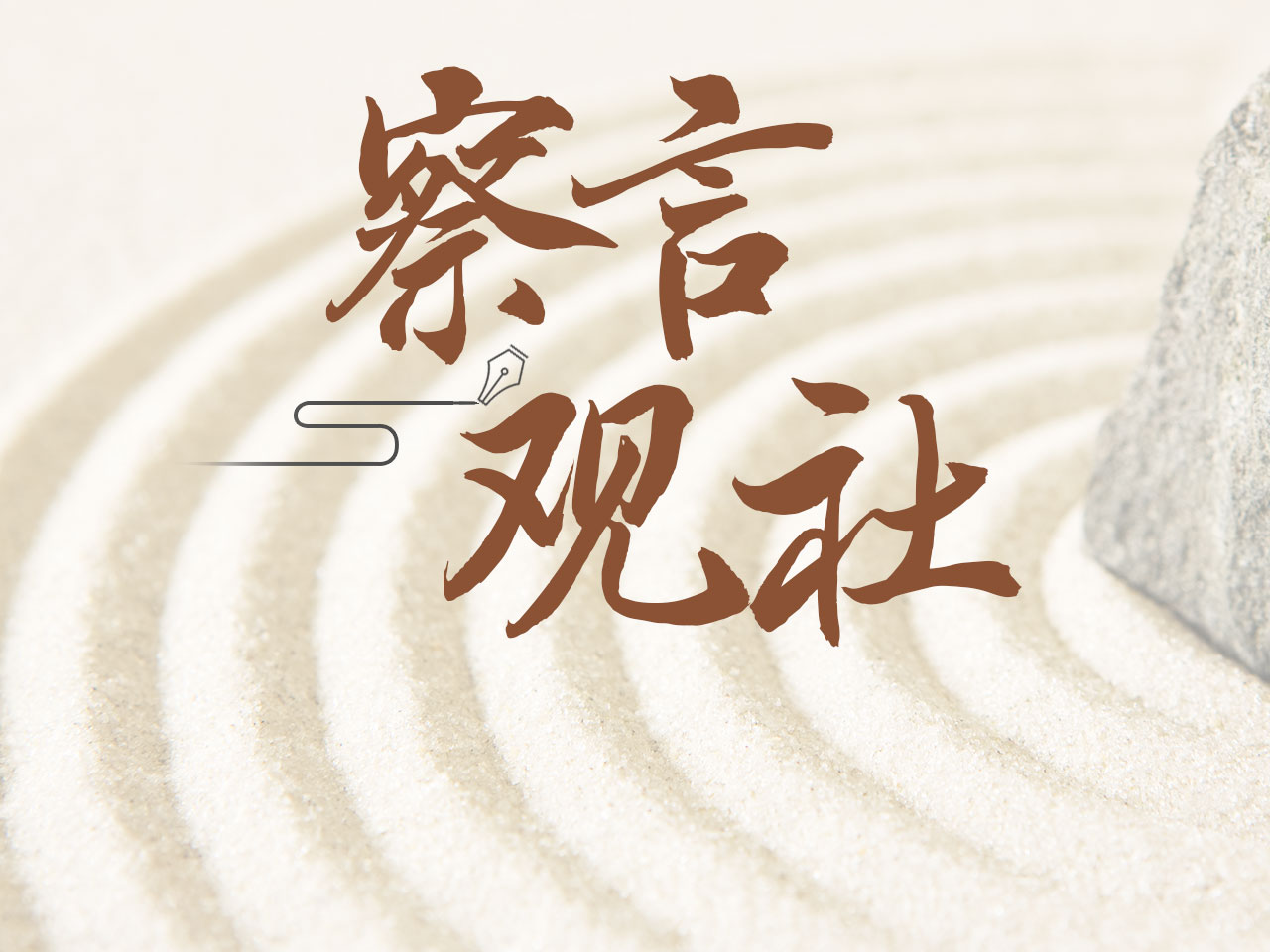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I期临床心试药采血现场。 徐亚特 摄
这是李琰第三次试药。
如果没有赌,今年30岁的李琰会生活得不错。两年前,他还是一名销售经理,手头积攒了一百多名客户,每月有近一万的收入,银行卡里存着几年打拼攒下的十几万积蓄。
他还有一位相恋多年的女友,按照正常的轨迹,接下来他会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为一名丈夫,再过几年,很有可能成为一名父亲。
然而因为赌,他输光一切。
在最落魄的时候,他甚至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为了骗一顿饭,他谎称手机在维修,身上没有现金买单,想要赊账。但饭店老板不信,他只好把身份证抵押在店,至今都没去赎回来。
2018年7月,走投无路的他为了赚钱,第一次踏上试药的道路。“那时候也没办法,要钱不要命了,有钱赚就行。”
在广东省庞大的试药人群体中,像李琰这样因为生活落魄,为赚取高额“补贴”而参与试验的受试者不在少数。他们曾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最后又沦落到一样经济窘迫的境地。
现在,他们走上相似的路,指向同一个目的——钱。
一
2018年7月,赌得身无分文的李琰,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中介瓜哥,瓜哥给他推荐了广州的试药项目。对方告诉他这个药没有风险,就是“吃两颗药,抽一下血”的事,“几千块钱就能到手了。”为了增加说服力,瓜哥还向李琰展示自己之前试药的照片。
李琰依然有些犹豫,在他看来,这就是“拿命去换钱”。但在试药的5000块营养费面前,他咬咬牙,报了名。
7月25日,他来到广州番禺中心医院进行体检。第一次试药,李琰显得格外谨慎。在集体知情的环节,他认真听着现场医生的讲述,一丝不苟地看着PPT上关于项目的介绍,还反复翻阅手中的《知情同意书》,“唯恐会出什么事。”
当天同样谨慎的还有陈德鸿。和李琰一样,今年31岁的他赌钱输了一百多万,还欠下一屁股债,现在在番禺当日结工人。
体检前一晚,在中介陈小姐的指引下,他入住了医院附近的左岸宾馆。这是一家试药人相当熟悉的宾馆,它和广州五、六家招募公司达成了低价合作,平时198元一晚的双人房,只收取招募公司60元左右。每当番禺中心医院有项目的时候,这家宾馆几乎住满了报名试验的人。
第二天7点,当李琰已经在医院排队等待体检的时候,陈德鸿还躺在宾馆的床上辗转反侧。他一晚没睡,眼睛红肿,布满血丝。他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了几千块钱当’小白鼠’,到底值不值?”
越想越害怕,他起床洗了个脸,连牙都没刷就匆匆离开了宾馆。在回去的公交车上,他在微信上和中介陈小姐谎称睡过了头。
而在医院这头,李琰顺利完成了所有的体检。第二天,他收到体检合格的通知,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后,他在规定的时间内来到医院,正式成为了一名试药人。这次临床试验一共持续了7天,试验结束后,他的银行卡很快就收到医院打来的5000元营养补贴。
这次顺利的试药经历消除了李琰的恐惧,他发现试药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恐怖,也不过是吃两颗药,抽一百来毫升的血,“比献血还少,一个星期半个月就回来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尝到甜头的李琰很快就想进行第二次。但按照规定,试药必须要有三个月的间隔期。为了保护受试者,广东省几乎所有医院都进行了“联网”,也就是通过查重系统来确认受试者的情况。
于是,李琰找到了中介瓜哥。
2018年8月,在瓜哥的帮助下,他进入了广州一家没有“联网”的医院,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试药仅过一个月。
和他相差5岁,同住广州黄埔东区的程朝也认识了P哥。他和最好的朋友讲了试药的事情,但是朋友不让他去,还狠狠地训斥了他“不要命了”。
于是,试药的事情被搁置到了一边。程朝依然找着装卸的零活,一天一干就是17个小时,赚得钱勉勉强强填饱肚子。
但是,装卸的活越来越不好做,在广州像他一样出卖力气的人很多,身高180,体重不足130斤的他在一群壮汉中并不具备竞争力。工头的价格一再压低,由原本的18块钱一个小时一直压到12块钱。
“太黑心了!那么大的箱子啊,得多重!”程朝双手往两边打开,比划着箱子的大小,语气特别激动。
找不到工作,程朝开始去献血,每献一次可以获得300元的补贴,两个月内,他去献了四次。在这期间,试药的念头又重新占据了他的脑海。同年10月和11月,他分别到广州两家医院参加试药体检,但由于频繁献血,他因为贫血,没能通过体检。
程朝不死心。
2019年1月,他又来到番禺的一家临床试验中心,这次他成功入组,成为一种名为二甲双胍的降糖药BE试验受试者。此时,他全身上下只剩下73块钱。
试验结束,程朝拿到5000块钱的营养补贴,还完花呗和欠朋友的钱,还剩000多。用剩下的钱,他在淘宝上给自己买了三双新鞋,还有两件新外套。
他准备再去献一次血,在春节前“干最后一票”。
二
2019年的春节,程朝依然没有回家。算起来,他已经四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1998年出生的他,今年不过21岁。当他出现在记者面前时,穿着一身军绿色的运动装,背着黑色的双肩包,扯着同伴的衬衫,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俨然一副稚气未脱、羞涩内敛的大学生模样。
但其实早在2015年,初中还没毕业的他就已经出来打工,在这5年间,他在各大餐饮店当过服务员,去技校学过电焊,也辗转于全国大大小小20多个工厂,甚至曾在外面漂泊流浪。
他的右手臂上有一条长达13cm的微微凸起泛白的伤疤,这是他在老家河南的一家面粉厂打工时留下的印记。当时年仅15岁的他被安排去擦窗户,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结果从二楼摔下来,地面上没有来得及清走的钢筋狠狠戳裂手臂上的皮肤,鲜血横流。
他对手臂上的伤不以为然。
相反,他很开心。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靠自己赚到了3000块钱,还通过QQ找到了一位女朋友。
在接下来的几年,程朝离开河南,辗转江苏、浙江、惠州、深圳等地。2017年初,在老乡的介绍下,他来到广州。
广州对初来乍到的他并不友好。
刚出火车站,长头发,扎着辫子的程朝想剪个清爽的平头,没想到被黑心商家“盯上了”。他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来到车站旁的一家理发店,谈好20元的价格。但最后老板以往头上“抹了原液”为由,硬要收他888元,还强拉着他,“不给不让走。”
当时在广州,程朝举目无亲,无人撑腰,这个从小就翻各家墙头偷樱桃,14岁就独自一人逃往青岛游玩的“混小子”也认了怂。他全身只有1千多块,给了钱后所剩无几。“没办法,你一个人也打不过。”他无奈道。
他用剩下的钱在广州黄埔东区租了一间单间,月租仅300块,暂时落了脚。房子很简陋,只有一盏昏暗的小灯泡,一张木桌子,一个垃圾桶和一张简易的铁床。他打趣自己的房子是《陋室铭》里面的陋室,和试药时医院的环境是“天壤之别”。
平时他最大的娱乐就是躺在床上用手机看电视剧。最近他在追《小女花不弃》,因为经常看通宵,他还特意买了两个超大容量的充电宝,“就怕看得开心的时候没电。”
他的床头还有一扇窗,但是常年都关着,拉着厚厚的窗帘。因为他住在一楼,窗外就是别人的后院,路过的人只要伸头一探,就能对他房间里的情况一目了然。
2017年4月,就在程朝吃着方便面刷剧到半夜时,李琰已经来到了云南的边境。微信上认识的中介联系好了人,帮他偷渡到缅甸,然后再把他送到中缅交界处的一家私人赌场。

云南边境挂着严禁出境赌博的警告牌。 网络图片
中介向他许诺,他可以在那借钱赌,“赢了还钱,输了就在那里打工还债。”
当时的李琰已经走投无路。他不仅输光了自己的积蓄,还骗了亲人朋友的钱,一样赌到血本无归,最终众叛亲离。带着“烂命一条,去就去”的想法,他来到缅甸的赌场,进行“最后一搏”。
中介所言非虚,赌场借给他3万筹码,就是电视剧上常见的那种筹码。那晚他手气不错,除掉要还赌场的钱,还赢了6万。之后,中介让他离开。他很开心,6万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他开始新的生活。
李琰计划着:先把钱还给父母,然后再找一份工作重新开始。
回去的路上,对方用毛巾把他的眼睛蒙上。他没有在意,因为他自认为也懂得一些“规矩”:“这是一家不合法的私人赌场,蒙眼睛是为了不暴露赌场的位置。”
他继续沉浸在“重新开始”的喜悦中。
十几分钟后,他被叫下车。扯下毛巾,出现在眼前的却不是回家的路,而是山顶的一间小黑屋。他内心一咯噔,心想“完了,出事了。”
回忆起小黑屋,李琰至今还心有余悸。他回忆到,在小黑屋里,十几个人被脱光了衣服,手脚都被厚厚的铁链绑住。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和他一样,过来这里借钱赌博,不同的是他们输了钱。
他也被要求脱光了衣服,铐上铁链,低着头跪在地上。有个男人拿着电鞭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脑子一片空白,说不出一句话。因为得不到回答,对方恼羞成怒,泄愤似地打了他一顿,然后把他和另外十几个人绑在一起。
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小黑屋里的另一个男人,因为输了钱,家里没钱赎他,每天被木棍、带刺的鞭子打得死去活来。
“打一下就出一声,不打就像死人一样躺在那里。后来我看到他,被折磨得很...很...很可怕,你知道吗?”说起这个画面,因为害怕,李琰嘴唇止不住地颤抖。
李琰被关了一天一夜,没睡觉,没饭吃,只能喝一点水。到了第二天,他就被放走了,因为他是这群人中唯一赢了钱的。但是离开的时候,送他下山的男人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话,他吓得魂飞魄散。
他说:“我送你去死。”
很显然,这只是一句恐吓的话。夜里,李琰被蒙着眼睛,坐上船,渡过一条小河,被扔到云南的边界。对方把身份证还有手机还给他后,转身离开。
云南当地淳朴的村民帮助了他,给他食物和几十块钱,还骑单车送他到镇里的汽车站。他坐大巴到了昆明,在微信上和朋友借钱,坐高铁回到广州。
直到现在,李琰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这段经历。他告诉记者;“当时真的以为自己会死。”如今,他仍然会感到害怕。刚回来广州的半个月,他晚上都没敢合眼。
后来他才了解到,小黑屋里的那些人是在赌场放高利贷的,像他这样的人,就是被骗过去的。输了钱,就让家里人把钱打过来,然后才可以离开。
他还在网上看到更多新闻,发现还有一部分人被骗过去,然后被毒贩强迫用身体带毒过境。“毒制成药丸,打在身体,搞不好,药一拿出来你人就死了。”
因为这些经历,李琰经常提醒其他试药人,不要去尝试特别偏门又来钱快的活儿,比如做公司法人之类的。他知道做这些事情的后:“如果不了解,觉得来钱快就去做,最后很可能会背上巨额的债务。”
三
从缅甸回来,劫后逃生的李琰开始尝试踏踏实实地工作,赚钱,然后还钱。
他最好的兄弟没有放弃他,给他资源,让他重新跑业务。生活慢慢起色,过了大半年,他攒下了几万的积蓄,还换了一部苹果7。
日子似乎在朝着可预见的方向好转。
可谁也没有预想到是,李琰又去赌了。他本以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自己能收手。但当他身上有钱的时候,他回想起过去的事,觉得“不服气”,便又到网上下注。结果,又输得精光,新买的苹果手机也卖了。
他描述当时的自己就像一个乞丐,连饭都吃不起。每天去网吧的厕所用毛巾简单洗个澡,就跑到天桥底下睡觉。饿了就借别人的手机,打电话骗家里人十几、二十块出来吃饭。带着“吃饱再说,明天再做打算”的念头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其实李琰曾有过更为艰苦的日子。
2015年他刚出来打拼的时候,全身上下只有3000元,就只身一人跑到了深圳罗湖。
他批发了一些包包首饰,把所有的货堆在一张大布上,在天桥上摆地摊。晚上收摊时再把所有东西卷成一个包袱,背在身后,然后找一个天桥底或网吧睡觉。
刚开始摆摊没有经验。第三天,城管来了,其他摊主卷起东西就跑,李琰来不及收,跟着别人一起跑,所有的货物都被城管没收了。
过了几天,他又想寻思着拿货去摆摊。这次他有了经验。在他身边摆摊卖首饰的小哥教他快速收摊逃避城管的“秘诀”:“那时候就一块布,他教我一抓这两个脚,一拉起来就一包,一背起来就跑。”李琰用手比划着动作,忍俊不禁,“那哥们还教我怎么跑,半小时再回来,一摊开又卖。”
李琰笑着说虽然这是一段很傻的经历,但是当时能感受到打拼的激情。后来他来到广州,在朋友的帮助下,做电信的销售,生活才慢慢步入正轨。
现在,一切又陷回了原点,但是他却没有了当初重新开始的勇气。
一而再再而三的赌博让他对自己感到绝望,他已经自暴自弃,觉得这辈子都无法逃离赌博的深渊。他说,“就算今年正常工作再赚10万,但是之后呢?再去赌怎么办?”
“我这种人,不值得原谅。”他苦笑着,黑框眼镜背后流露出悲痛。
今年3月份,他又去参加了试药。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试药,和前两次一样,为了“赚一点快钱”。
对未来同样迷茫的还要程朝。在李琰第三次试药期间,他把在黄埔东区租了一年多的房子退掉了,并在堂哥的介绍下,来到东莞的一家造集装箱的工厂学习电焊。
离开前,他还特意来到火车站,寻找当年骗他的那家黑心理发店。结果发现那家店变成了一家手机店,一问,原来是被人给砸了。他乐开了花,直言道:“其实我心里蛮高兴的。”
学习电焊的过程并不容易,刚去几天他的大拇指就被集装箱砸得淤青,还渗出了红血丝;眼睛也因为一直长时间对着电焊喷射出的火花,“疼得难受。”
他不愿意学习电焊,同在厂里的堂哥又给他安排了刷漆的活,每天就是给造好的集装箱刷漆。但是刚干两天,因为油漆过敏,他脚踝肿得老高。
于是,程朝想要离开。程朝想离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和四、五十岁的工友没有共同语言,“待在这里很孤独。”


程朝的宿舍环境,他和12名工友住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在外打工的这几年,程朝觉得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没有找到知心的朋友。他曾经以为,只要付出真心,就可以交到朋友。在广州做装卸活的时候,有人向他借钱,每次他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然而,每次到了还钱的日子,这些人就把他拉黑,或者直接跑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程朝挣了钱都用在这上面,“被骗了好多次,但我就是死性不改,还是借,我以为能交到,但是真没交到。”程朝谈起这件事,还是很难过。
现在的程朝自诩成长了很多,也懂得了处理人际关系。不过,据他透露,所谓的处理不过是“不和他们交往了,也不再主动和陌生人说话,偶尔的时候想想初恋。”
因为这些因素,程朝觉得在东莞的工厂待不下去了,他和堂哥透露了想离开的念头,大他三岁的堂哥却不让他走,要他收心待在工厂好好学一门技术。为此,兄弟俩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矛盾。
在KTV的一次聚餐,两兄弟又因为离开的问题争吵。激动时,堂哥把装啤酒玻璃杯狠狠砸到地上,指着他吼:“我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你爸把你交到我手上,让我带你学一门技术,别人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你说,你为什么不能做!”
程朝觉得家里人都没办法理解自己,他准备自己回广州。但他也很烦恼,他身上没有钱,到了广州也没有住的地方。之前的房子早已经退了,身边也没有朋友可以提供住宿或者借钱给他。
他又开始去找瓜哥,让他介绍试药项目。今年4月,他准备先试药赚几千块,再慢慢找工作。
至于未来,他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可能过两年就回家,帮家里人卖菜。”他笑着说。
编辑 刘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