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则臣
《北上》是作家徐则臣的长篇新作。从大的时间关节点来说,整部作品主要由历史与现实两条结构线索组合而成。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我们对于所谓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理解,或者说界定,其具体的分水岭乃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举凡发生在1949年之前的故事,就属于历史的范畴。而发生在1949年之后的故事,则属于现实的范畴。依照这样的一种标准来衡量,《北上》中的历史这一条结构线索,主要包括“第一部”中的“1901年,北上(一)”、“第二部”中的“1901年,北上(二)”以及“1900—1934年,沉默者说”共计三个部分。更进一步说,历史这一部分又可以被进一步划分为主次不同的两条结构线索。其中,前两个都被命名为“北上”的旨在描写意大利人小波罗在公元1901年从杭州出发,一路沿着大运河乘船北上的部分,可以被看作是主要的结构线索;而另外一个被命名为“1900—1934年,沉默者说”的旨在交代小波罗的弟弟——另一位意大利人费德尔·迪马克也即马福德在中国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的部分,乃可以被看作是相对次要的一条结构线索。同样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我们这里所强调的小波罗乘船北上的那两个部分,不仅可以被看作是本书历史书写中最主要的一条结构线索,即使与线索更为繁多的现实书写相比较,也更为重要,可以视作这部长篇小说的书写重心。质言之,徐则臣之所以要把这部小说命名为“北上”,其根本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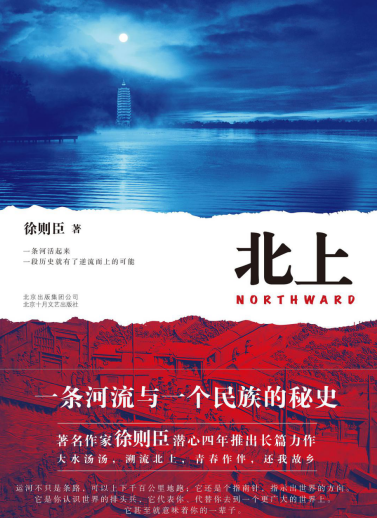
《北上》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正当谢望和为电视片《大河谭》后续资金问题所严重困扰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喜讯。如此一个利好消息,一下子就解决了谢望和的燃眉之急。在这里,徐则臣其实是在以“夫子自道”的方式,阐明身为大运河之子的自己,究竟为何一定要完成《北上》这样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写缘由。事实上,也正是作品如此的结尾方式,才让我们彻底想明白,作家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将这部同时关涉到历史与现实的长篇小说命名为“北上”。从写实的层面上说,“北上”的标题固然根源于历史中小波罗一行沿大运河北上之举,但如果从象征的层面上说,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大运河的实质,不过是自打隋炀帝开凿起始便一直流淌至今的一脉流水。面对这条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流淌至今的大河,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遗忘孔子面对大河时所发出的“逝者如斯夫”的那声浩叹。孔子的创造性天才表现在,他把那浩浩荡荡不停流淌的河水,与看不见摸不着有着突出抽象意味的时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样一来,抽象的无形的时间便获得了一种形象化的可能。如果说河水与时间之间,的确存在着如此一种互通性,那么,小波罗他们的沿大运河北上,其实也就有了某种回溯时间的意味。进一步说,假若我们把如此一种回溯时间的象征意味,与徐则臣这部《北上》中现实与历史相交织的书写结合在一起,那么,这“北上”也就拥有了某种沿着时间的河流上溯的意味。
推论至此,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既然自打隋炀帝开凿起始,大运河迄今已有长达1500年之久的历史,那么,徐则臣在《北上》中为何要把他的上溯时间确定为1901年义和团运动前后的那个时间节点?要想理解作家的这一选择,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时间节点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乃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换言之,这个时候,也正是以“后发”“被动”为突出表征的中国“现代性”发生并潜滋暗长的一个重要时刻。梁启超之所以会把这一时期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具体来说,徐则臣《北上》中曾经涉及到的诸如“戊戌变法”、义和团以及八国联军等,都是中国“现代性”生成过程中发生的主要历史事件。中国“现代性”发生与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只知道有“天下”而不知道有“世界”的中国人,终于打开视野,强烈地意识到在“天朝大国”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存在。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徐则臣才会在小说中特别写到意大利人小波罗兄弟,写到那些传教士,写到八国联军。所有这些,相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异质的存在。所谓的“现代性”,正是伴随着这些异质存在的到来而进入古老中国,并在中国开始潜滋暗长的。既然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那他们的到来,就必然会与中国本土的存在,发生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满清王朝、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这几种不同的社会政治势力之所以会生发出各种盘根错节的矛盾纠葛,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
关注徐则臣的读者都知道,他是一位拥有突出“世界”意识的作家。这一点,在他几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中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耶路撒冷》中,不仅小说的标题凸显着作者的“世界”意识,本书主要人物之一初平阳心心念念想要去留学的地方,就是遥远的耶路撒冷。《王城如海》中的主人公之一余松坡,回北京工作前曾经有在美国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他所携带着的,无疑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生存经验。到了这部《北上》中,诸如小波罗、传教士以及八国联军这样一些“世界”性因素的存在,就与那一历史时期“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北上》是一部书写大运河的长篇小说,反倒不如说作者的根本主旨更在于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关注与书写。徐则臣真正的着眼点,其实是梁启超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种地理与时间微妙转换的过程中,“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悄然无声地取代了大运河,成为了《北上》真正意义上的潜在主人公。而这也正是徐则臣把自己的上溯时间最终确定在1901年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我们既无法遗忘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的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也无法遗忘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主要是强调历史书写中具备一种现实感的重要性,有着强烈现实感的《北上》显然做到了。.
延伸阅读

《单筒望远镜》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1900年,庚子国难,在东西方冲突得最激烈的天津,一段跨国恋情悲怆上演。冯骥才先生以古朴精致的语言,行云流水般的叙述,展开了一幅真实、鲜活又影响深刻的历史卷轴,一百多年前的天津风貌和中西碰撞的惨烈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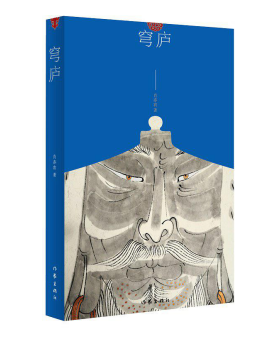
《穹庐》 肖亦农 著 作家出版社 2018年12月版
民国初年,以日本为主的协约国对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武装干涉,并妄图拼凑大蒙古帝国。其阴谋遭到了布利亚特部落的竭力反抗。布利亚特部落首领嘎尔迪老爹在多重选择后,率部经历了千辛万苦,一路八千里征战回到祖国。
编辑 刘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