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利普·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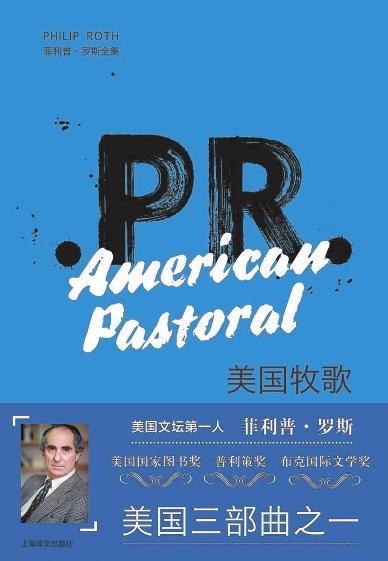
菲利普·罗斯《美国》三部曲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6月版 《美国牧歌》罗小云 译

《背叛》魏立红 译

《人性的污秽》刘珠还 译

约翰·多斯·帕索斯

约翰·多斯·帕索斯 《美国》三部曲 作家出版社·S码书房 2020年12月版 《北纬四十二度》 董衡巽 朱世达 薛鸿时 译

《一九一九年》 朱世达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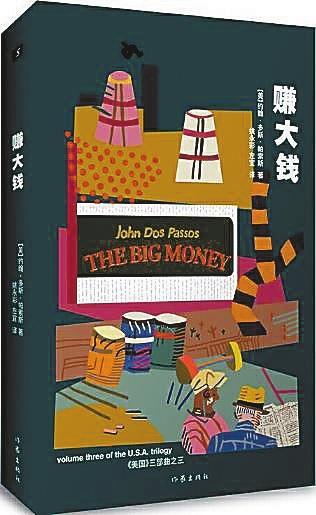
《赚大钱》 姚永彩 左宜 译
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说过:“在世的美国小说家有四个人的作品能够流传,菲利普·罗斯是其一。”当2000年罗斯创作的《人性的污秽》正式出版,他的《美国》三部曲终于创作完成,包括了《美国牧歌》、《背叛》和《人性的污秽》。这三部长篇小说虽然是互相独立的故事,却连接而成,完整呈现出当代美国社会的问题,以及美国人的矛盾与困境,彼时罗斯已经66岁了,可人们发现,他的愤怒和笔力以及尖锐的人性视力,仍是那么犀利而准确。
无独有偶,在美国文坛上,还有另一套《美国》三部曲,那就是曾与海明威齐名、同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的约翰·多斯·帕索斯的《北纬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赚大钱》三部长篇小说。如今,帕索斯已去世50年了,但他这三部作品依然可列于20世纪美国文学最高成就的杰作之中。著名文学批评家艾尔弗雷德·卡津曾评论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是“一部民族的史诗,是美国现代小说中第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日前,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这三部小说,国内读者在有机会与帕索斯代表作相遇之余,也可以借助文学作品进一步读懂美国这个国度。
他发现美国人的苦难 有它的秩序和等级
菲利普·罗斯的“祖克曼系列”第一本《鬼作家》出版于1979年,那时罗斯46岁。此后,内森·祖克曼这个人物或当主角,或当旁观者叙述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在《美国》三部曲(《美国牧歌》《背叛》《人性的污秽》)中,祖克曼都是叙述者,一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我”。
如何形容罗斯的行文风格?用罗斯在《鬼作家》中的一个短语:美国的“俄罗斯式”作家。请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21世纪的美国行走并言说。《人性的污秽》中,罗斯描写福妮雅的个人灾难史时,口吻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陀氏描写那个受辱的小女孩时是相似的。罗斯对陀氏(以及俄罗斯文学)的喜爱可见一斑:“你对人性的理解不会那么浅薄的,因为你看过太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出自《乳房》一书。) 他在很多书中都会写到寻找替身父亲这一主题,这与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弑父因素不谋而合。而《人性的污秽》开篇引用的《俄狄浦斯王》,亦是一个与弑父有关的故事。弑父意味着消除权威与唯命是从,这之后的自我探索才是更精彩的历程。
菲利普·罗斯对“鬼魂”这个词情有独钟。《鬼作家》(The Ghost Writer),《人性的污秽》里那个让主人公从此跌落的词,幽灵(spook),还有之后的一本《退场的鬼魂》(Exit Ghost)。这里的“鬼魂”并不是指鬼怪之事,而是对生活失去实感或是不要生活(亦即被生活抛弃)的人。生活也是物竞天择,有的人适应了生活,而有的人就是无法适应,因而被生活这个进化之轮抛下并碾压。《鬼作家》中:“不要生活!他就是从不要生活中产生他的动人的小说的!”《人性的污秽》中莱斯特这样说:“因为我死过了。因为我已经在越南死掉了。因为我是个他妈的死掉了的人。”而关于福妮雅:“这孩子的生活在四岁时变成一片幻觉,十四岁时遭恶变,以后便是一场灾难。” 生活如何在这些人身上成为幻觉与灾难,罗斯在《美国》三部曲中给出精彩叙述,在《人性的污秽》中达到顶峰。
力量(亦即权力)也是理解罗斯《美国》三部曲的关键。有力量的地方就有权力,就有强者和弱者,就有伤害。几乎可以说,每一处伤害都指向一个权力关系。无论这权力关系是家庭的、种族的、性别的,甚至是自己对自己的暴力(福妮雅未遂的两次自杀)。在罗斯的《美国》三部曲中,描摹了很多这样的权力图景。
拿主人公科尔曼来说,他在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从父亲的话选择院校时,是弱者。他在与母亲绝交时,是强者。他在抹去自己的黑人身份,扮演一个犹太人生活一辈子时,既是强者也是弱者。弱在服从了社会的种族权力规则,强在敢于强力改变自己身份与生活。不同时刻不同人际关系里,一个人在强者与弱者的光谱上位置不定。而强与弱之间的微弱摇摆左右人生。没有人可以永远是强者,永远神圣。“要让他人将你看成神的代价就是使你追随者的梦境永不消减。”(《美国牧歌》)
当科尔曼决定“擦去”自己的非裔美国人身份(他的肤色很浅),他的母亲说:“你像个奴隶似的思维。你是的,科尔曼·布鲁特斯。你白得像雪,但却像黑奴似的思维。” 科尔曼的母亲察觉到了他的局限之处。纵然成为白人(科尔曼在参军时谎称自己是白人),可以享受一些社会优势,但这优势是骗来的,这种自我欺骗让他成为奴隶。“每一天你醒来扮演你创造的自我。” 与科尔曼有同样困境的,是德芬妮。德芬妮是一名年轻教授,法国人,只身来到美国发展,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教授,成为系主任。她是抵制科尔曼的中坚力量,换言之,一个落井下石的人。科尔曼和德芬妮都是为了自我而坚决与过去,与一切阻碍(包括亲人)诀别的人,然而到头来却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亦不是我。在他们的净化仪式中,自我已经变形,过去熟悉的一切也不复存在。一个玩笑,一场赔本买卖。
《人性的污秽》中,科尔曼由于用词“不当”,辞去职位,妻子也患突发病死亡,愤怒与哀伤环绕他。然而福妮雅看不上他的苦难。福妮雅不愿给科尔曼这个受难者头衔。因为在她看来,科尔曼所受的苦不值一提,不算是“真正的苦”。我们要正视的是,苦难的确有质和量的区分。在人类个体的受难中,我们时常说,苦难就是苦难,意思是苦难没有高低之分。但我们越来越发现,美国人的苦难有它内在的秩序和等级,比如福妮雅就站在苦难的金字塔尖,蔑视科尔曼,蔑视这个世界。
在外人看来,年老的科尔曼选中年轻的福妮雅这个不识字的清洁女工来发泄自己愤怒、失意与情欲是不道德的。科尔曼是强者,福妮雅是弱者。但真的是这样吗?在《背叛》中罗斯写道:“因为强者的能力是骇人的,弱者的能力也是骇人的,都是骇人的。” 强者与弱者都有自己的力量所在。福妮雅只是表面的弱者,她装作不识字。因为,“不识字是一种行为——某种她认为取决于她处境的行为。”在这里,识字对福妮雅来说,就是这个社会的礼数,是体面的一部分。同样,莱斯特(福妮雅的前夫)从越战回来后,也无法面对这个社会的礼数。“穿干净衣服,大家相互问候,大家微笑,大家参加派对,大家开汽车——我不再能衔接得上。我不知道怎样和任何人交谈。不知道怎样跟人打招呼。我在很长时间里自我封闭。” 在个人经历与美国社会规范之间,有了无法弥补的沟壑,也就是这个沟壑让人的生活失去实感,使得生活看起来总像是在彼岸。
女性在罗斯的书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像在俄罗斯文学中,女性要么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要么是清纯的初恋、逝去的梦幻这样的角色。在罗斯的书中,女性与男性势均力敌,他们是旗鼓相当的人生对手。罗斯评论耶日·科辛斯基的《暗室手册》:“描摹了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各种关系。通过心理上的手段,人和人互相征服。” 是这样的,罗斯的《美国》三部曲也充满了人与人相互征服的故事。三部曲中的女性都值得探究。女人总有女儿这一社会角色。《美国牧歌》中的炸弹客女儿,《背叛》中伊芙的女儿,《人性的污秽》中的福妮雅,以及科尔曼的女儿莉萨。她们以各自的方式完成了对家庭的反抗。
他描绘了美国社会杂乱无序的时代画卷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年出生于芝加哥,191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去西班牙学习建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加入法国红十字救护队和美国医疗队,参加战地救护服务,战争结束后担任新闻记者。1920年,帕索斯出版第一部小说《一个人的开始》;次年,同样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小说《三个士兵》问世,备受好评,是最早反映美国青年一代厌战和迷惘情绪的作品。
帕索斯笔下多为美国社会的失意者,表现了20世纪初动荡不安的美国社会。随着帕索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的加深,他参加了营救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樊塞蒂的活动,并因此而被捕入狱。他还参与创办左翼杂志,采访和宣传罢工斗争,公开支持美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背景之下,20世纪30年代,帕索斯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北纬四十二度》(1930)、《一九一九年》(1932)、《赚大钱》(1936),这三部作品合便是他的《美国》三部曲。
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规模宏大,匠心独具,全景式地展现了美国20世纪前三十年的社会变迁。帕索斯使用“群像小说”的写法,集中描写了印刷工人麦克、公共关系寡头摩尔豪斯、在飞机制造业中发迹的查利、积极参与工人运动的玛丽、成长为电影明星的女演员玛戈等各个阶层的十二个人物,但故事相对独立,各自成章,偶有交集。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三部曲中,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故事主线或主人公。人们偶尔相遇,大多时候各行其是。书中人物到处流浪或谋求事业的发展,有的寻找到生活的意义,有的则为时代的洪流裹挟,茫然游走。这显然具有现代性质的表现手法,更加真实生动地凸显了当时美国社会各阶层的“众声喧哗”和现代生活芜杂、偶然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这些游走于社会各阶层的不同人物,无论是富商、企业家,还是流浪汉、普通职员,抑或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罢工运动领袖,帕索斯都塑造得异常鲜活真实。对话、动作、神态、心理,无不描摹得妥帖自然,人物的性格呼之欲出。这显然得益于帕索斯的杰出才华、职业阅历以及其敏锐的观察力。当我们在脑海中,将这些人物的活动拼接成一幅众生相时,我们的确看到了彼时美国社会杂乱无序的时代画卷。帕索斯还运用了较多实验性技巧,加入“新闻短片”“摄影机眼”“人物小传”,来更加立体地表现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
这一类创新的实验技巧,显现出帕索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艺术功力。“新闻短片”“摄影机眼”“人物小传”即便单独来看,也非常富于艺术魅力。看似碎片化的叙述和意识流的描写,却并不枯燥,让人品之有味,再三遐思。比如《一九一九年》的最后一章是“人物特写”,帕索斯并没有写风云人物,而是以想象的笔触描绘一位一战中阵亡的无名士兵的一生。这篇题为《一个美国人的遗体》的特写,简笔勾勒出一位无名士兵的出生、成长、入伍、作战、死亡……他简洁的语句并置,一个又一个场景连缀,富有画面感,如在读者眼前;短句、长句和无标点的词组杂糅,参差错落,又显得摇曳多姿。
《美国》三部曲奠定了帕索斯在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上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并给予当时及后来的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同时代的著名作家海明威、辛克莱·刘易斯、福克纳,都高度称赏帕索斯的卓越成就和他为美国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萨特、略萨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深受帕索斯的启发和影响。杨仁敬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曾这样评价帕索斯:“他这些技巧在长篇小说《三个士兵》(1921)、《曼哈顿转运站》(1925)中进行了实验,在《美国》三部曲(1930—1936)中达到了成熟阶段,影响了欧洲许多作家。……他和乔伊斯几乎影响了30年代整整一代的美国青年作家。”
原标题:《两套<美国>三部曲呈现美国社会问题》
编辑 刘彦 审读 刘春生 审核 张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