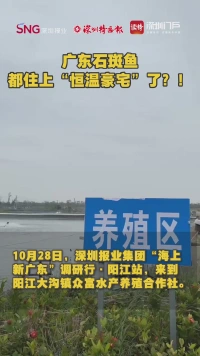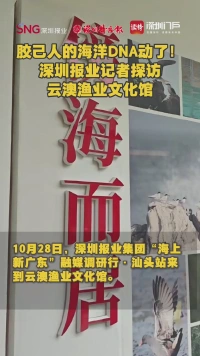钱穆故居位置图。
穿过台北东吴大学校门,沿外双溪向阳明山麓行去,经过林阴道旁一块镌刻“钱穆故居”字样的巨石,迎面一扇朱门,上题“素书楼”三字,正是钱穆遗墨。朱门后面,拾级而上是被绿树修竹环抱的两层小楼,钱穆曾在此隐居22年,写出31本著作。他一生所著的1700万余字、全集54本著作现在整整齐齐地陈列在二楼书房里。这些著作的稿费,收入钱氏在辞世前一年建立的素书楼文教基金,迄今延续着他无法割舍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教育事业。

钱穆(资料图)
7月30日是一代儒宗钱穆(1895.07.30 -1990.08.30)诞辰121周年纪念日。钱穆故居管理计划执行长秦照芬博士告诉记者,钱先生以“士君子”自况,生活简朴,忧国忧民,念兹在兹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年轻人中的传承,故居的使用希望能遵从他的“想法”,少儿读经班、古琴研习班、青年读书会是周末常设活动,而不时地,会有新人来此举办一个书香氤氲的婚礼。
学界传奇“北胡南钱”
秦照芬在钱穆生命的最后两年,来到素书楼担任他的秘书。她告诉记者,素书楼大致仍按钱穆居住时的格局陈设。一楼会客厅立有朱熹雕像,墙上挂着用朱熹所书的“立修齐志”、“读圣贤书”、“静神养气”的碑刻拓片制作的对联,可见钱穆对朱子和宋学的推重,以及他追步前贤的抱负。
在学界,钱穆是一个传奇,他中学都没毕业,从18岁开始在乡间执教小学与中学18年,其间勤学苦读,著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诸子系年》等文史著作,解决了当时聚讼纷纭的一些学案,令史学家顾颉刚大为欣赏,推荐他至北京燕京大学任教。自1930年起,钱穆先后任教于燕京、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等校,作育英才无数。当时学界将之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在台北素书楼授课。(资料图)
与当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不同,钱穆强调“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始终坚信“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治学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他认为今日中国自救之道,首在恢复国人之自尊自信;恢复国人自尊自信之道,在使国人认识历史文化传统。故救国之道,主要在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抗战烽火中,他费时一年专心撰写《国史大纲》,“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以激励民众奋发爱国之精神,这也是他书生报国的一个典型事例。
临终前三个月,钱穆以96岁高龄完成最后一篇文章《天人合一——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指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钱穆把晚年这一感悟视之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发明”。
被强行打断的“素书楼佳话”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资料图)
1967年,钱穆和夫人胡美琦由香港移居台北,欲寻一安静处所完成他晚年最看重的著作《朱子新学案》。由朋友介绍,在阳明山下外双溪旁觅得一块预留的坟地,因为便宜而且安静,遂决定在此盖楼隐居。此事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得知,为“礼贤下士”计,执意让阳明山管理局依照钱家的设计图,为他们建造两层楼的宾馆,
1968年7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入外双溪居住,钱穆为感念母亲恩德,特别以母亲在家乡无锡七房桥故居所住之素书堂为寄意,将新居取名为素书楼。1969年,钱穆受邀担任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每周于家中客厅讲课2小时,素书楼又成为史学青年的问学“圣地”。

“素书楼”三字为钱穆手书。
钱穆一口无锡乡音,讲课时神采飞扬,语速颇快,虽然口音听懂不易,但内容实在精彩,让学生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加上听课学生不受限于校内,吸引许多慕名而来的学子,或坐或站,把客厅挤得满满。许多学生一听就是20年,学生听成了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最高纪录曾出现“五代同堂”的盛况,也教育出不少知名的学者。当时已经成名的中青年学者如余英时、许倬云自海外回台之时,或专程或顺道,亦常来与钱穆讨论学问。
1986年,从教75载、已经91岁的钱穆决定从文化大学退休,于当年6月9日上最后一堂公开课。在课上,钱穆留下感人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那天学生环坐听聆教诲的情形,如今定格在故居墙上的大幅照片里,“其实之后还是会有学生回来听课,先生为他们多讲了两年的课,一直到身体状况不佳,方才停止。”秦照芬告诉记者。
也正是那时,93岁的老人突然被卷进了一场政治风波。1988年5月,台北市“议员”周伯伦、“立法委员”陈水扁指责素书楼“既无租约,又不付租”,是“非法占用公产”,要求收回。至1990年,风波愈演愈烈。虽然素书楼手续清楚,无“非法占用”之实,但钱穆以“余今年已95岁,实无精力与人争辩是非,生平唯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于1990年6月1日毅然搬出居住了22年之久的素书楼。

素书楼庭院里的树木多为钱先生与夫人亲手种植。
秦照芬忆起当时收拾搬家的情形,大量书籍捐赠给友人或文化大学图书馆,考虑以后会用得着而搬走的书就有200多箱,每箱20多公斤,可见有多么折腾。而搬家前,钱穆正在病中。搬家三个月后的8月30日,一代儒宗无言逝于台北杭州南路自宅中,享年96岁。
吊诡的是,在钱氏夫妇搬出素书楼仅1年零7个月,1992年1月6日,台北市政府又将人去楼空的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以纪念其学术贡献。到了2002年改以“钱穆故居”的名称开放参观,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亦公开道歉,澄清钱穆并未“占用公产”。
枯桐欣有凤来仪

晚年钱氏伉俪在素书楼庭院内留影。(资料图)
说起钱穆晚年的学术和生活,都绕不开他的第三任夫人胡美琦。秦照芬说,师母对先生的生活照料固然是巨细靡遗,而先生自80岁后几乎不能见字,写作也全靠夫人协助。“没有师母这样帮他读稿改稿,我相信钱先生晚年很多东西是出不来的。”
钱穆一生结过三次婚,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第二位妻子张一贯于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育有三子二女。第三位妻子胡美琦是他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学生,两人的师生恋颇有几分传奇。
胡美琦(1929-2012),比钱穆小34岁,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在民国时曾担任过江西省主席。胡美琦1949年来到香港,在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读了一年,就随父亲迁居台北。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邀来台到淡江文理学院演讲,不料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击中他的头部,几致丧命。此后数月,钱穆留在台中养病,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作为学生前来照顾,两人渐生感情。1956年1月30日,两人在香港结为夫妇。钱穆亲撰对联以志欣喜:“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素书楼内景。
钱穆1949年只身来港办学,环境艰苦,生活不稳定,自与胡氏缔姻,生活走向正轨。在港12年,在台23年间,生活与写作,悉赖夫人照料。1980年5月28日,钱穆在给幼女钱辉的信中写道:“你们继母,姓胡名美琦,今年五十二岁,我们结婚已二十五年,但未有子女。……我此数年来,双目失明,但还能写稿,都由你继母先誊正再改定。若非她,我此两年亦不能再写此许多稿。”此信表达了他对夫人襄助之功和悉心照料的感激之情。
秦照芬说,看到师母对先生照顾之细心用心,她是忍不住要哭的。钱先生生病不喜欢住医院,所以师母要很注意他的保养。请名中医配了膏滋药给他喝。费上一天功夫做一道点心哈士蟆炖红枣给先生吃了。师母完全按先生的口味做菜,为先生亲手缝衣服,为接送先生而学开车,“我觉得师母照顾他以后没有自己了。在我们历史学界很多人都很羡慕先生有这么一位贤内助。”秦照芬回忆,“当然钱先生人很好,师母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给他穿什么就穿什么,从来不会要求什么。”

钱穆先生著书立说的书房。
而两人的生活虽简单却也不乏情趣,他们喜欢旅游,到风景绝佳处喝一杯咖啡。钱穆擅昆曲,箫笛俱佳。住在香港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夫人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整条的长廊,盘膝坐在廊上,静听钱穆在月光下吹箫。
夫妻俩也时常在楼廊上观景闲谈,或社会,或人生,或文化,或学问,吉光片羽收录成《楼廊闲话》一书,让人得见这对学界鸳侣琴瑟和鸣的恬淡自适,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疼惜和执著。

钱穆塑像。
【读特新闻+】
他是真正的“士君子”
——对话钱穆故居管理计划执行长、台北大学历史与地理学系系主任秦照芬
“如果要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形容钱先生,我想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他是我们中国现当代真正的‘士君子’。士有道德要求,君子的要求就更高一些。”秦照芬如是说。
1988年,秦照芬从成功大学硕士毕业,准备考博士班期间,被推荐到素书楼为钱穆当秘书,直至钱穆去世。其间参与钱穆与夫人胡美琦用自己稿费建立的素书楼文教基金会,义务工作迄今。
晚年一直在修改发表过的文章
记者:您当时为钱先生做秘书,主要做哪些工作?
秦照芬:跟书僮差不多。那年钱先生94岁,我外公80多岁,我跟先生相处就像跟家里的长辈。倒不像听课的学生那么紧张。去的最重要目的,是师母时常要出去查资料或办一点事,要有人在,我和另外一位小姐作为秘书轮流去陪钱先生。
钱先生生活简单,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喝完中药,如果想写稿子,就到书房,如果不写稿,就在楼廊上坐,我们就给他读读报,陪他聊聊天,自己读书遇到的问题也问他。然后,偶尔也会帮忙读读稿,如果钱先生有写作的话,就帮他把稿子抄下来。因为他到80岁后眼睛就几乎看不到了。
那两年,钱先生精神好的话,就在楼廊上散步,每天走3000步,以前是走10000步的。以前是到外面散步,去故宫查资料用功的时候就在故宫周围散步。晚年不出去,就在楼廊上散步。
记者:先生晚年学术上的主要助理还是师母?
秦照芬:当然,因为钱先生写过的稿子,他一定会重复再读几次,即使已经出版。到晚年,尤其是从90岁开始吧,他觉得年纪大,有点急迫感。我在的那两年,这感觉尤其明显,钱先生一直在修改他发表过的文章,师母给他读一遍,他自己决定哪里要修改,钱先生过世以后,师母整理出版钱先生的全集1700万字,54大册,大部分都是钱先生有修改过的,改动的主要是他的看法,他觉得他年纪大了后,有些看法要修订。
先生过世后,全集出版的校对,虽然有学生参与,但大部分也是师母在做,每天熬夜到两三点,所以她后来心脏有点不太好。
非主流学者”为一般人写书
记者:翻看钱先生的书目,一方面他写了很多学术性很强的专著,一方面,他又有很多为普通读者写的随笔。
秦照芬:钱先生在台湾学术界不算“主流”,为什么不算“主流”?其实很多人都看他的书,“主流学者”的书不一定像他这个“非主流学者”的读者多。比如像他的《国史大纲》,所有历史系的学生几乎都看,他的很多著作,像《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朱子新学案》,都是掷地有声的,很少有人能超过他。那为什么学界好像把他当作“非主流”?原因是他在晚年很少再写这种专门的学术性的书,他晚年很多著作其实是写给一般人看的。在故居陈列的49本《中国思想史小丛书》,就是他生前交待要做的,是给一般人看的。因为大陆‘文革’以后,他觉得,可能文化会中断,他决定要编一套“人人自修国文读本”,以挽救文化中断的危机。这也是钱先生和夫人捐出稿费建立素书楼文教基金的缘起。
稿费捐建素书楼文教基金
记者:素书楼文教基金是如何建立的?
秦照芬:1977年夏,先生身染重病,几不治。第二年春,病稍愈,双目已不能见字。养病期间,以写《师友杂忆》一书遣怀。信笔写出,需待夫人为之抄录诵读,再逐字逐句加以修正。此一小书,竟先后花费先生伉俪五年时间,始得完成。先生自念年事已高,惟望弘扬文化之工作能永续推动,遂决定以《师友杂忆》一书稿费新台币15万元为始,此后凡有稿费收入,皆集存作为弘扬中华文化工作之基金,至1989年凑足100万元作为永久基金,申请成立“财团法人素书楼文教基金会”。此后先生和夫人的稿费陆续投入基金。我们工作人员则是义务为基金工作。
素书楼文教基金会除了遵照钱先生的遗愿出版《中国思想史小丛书》,主要举办两个活动,一个是在香港,有大陆、台湾及港澳等地人士参与的中学文史教师研修会,已经举办十五届,每年参加人数约四五十人;另一个是在大陆办的两岸中学生国学夏令营,到今年是第十七届,每年参加人数150人左右。这两个活动都由基金会负担大部分经费。
记者:这两个活动都是针对中学师生的?
秦照芬:是的。钱先生一辈子教书近80年,小学、中学、大学都教过,他认为中学这个阶段才是最重要的可以培养人的阶段。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宗旨,就是为中学的教师和学生服务。
大师小传(1895.07.30 -1990.08.30)
钱穆,字宾四,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公元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延祥乡。
1912年起出任乡村中小学教师18年。1930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言,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
1931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此后相继于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等校任教。
1949年,赴港创办新亚书院。
1955年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
1957年,与夫人迁居台北。
1986年 6月9日,正式宣布自文化大学荣休。
1990年,迁出素书楼,是年8月卒于台北市杭州南路自宅,享年96岁。
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中的西山。
重要著作
《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刘向歆父子年谱》《国学概要》《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晚学盲言》《天人合一》
(本文配图除注明资料图外,其余为作者拍摄)
编辑 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