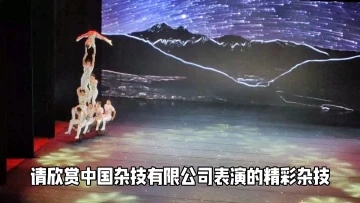傅世德/文
“浪浪山”这个词的流行,可以追溯到2023年《中国奇谭》出现在大众眼前时。那时人们用“浪浪山”来指代无奈的人生、窘迫的境况,自那时起,其实《中国奇谭》就抓住了当下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它谈不上负面,更难看作是正面,而是一种看破道不破的感受。而今天,看完了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浪浪山”这个词便突破了过往语境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感色彩,真正地向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反传统的英雄主义迈步。
《浪浪山小妖怪》的反传统,首先体现在它对西游这一经典神话的改编上。过往对《西游记》的改编,往往跳脱不出几种情节编排:挖掘五人主角团各自的故事,或是用更喜剧化的形式体现其本身,又或是追溯西游之前的经历。如果要罗列《西游记》相关的艺术作品可谓数不胜数,从《西游记》这本原著,到周星驰改编的《大话西游》,再到电视剧版的漫画版的动画版的《西游记》,又或是比较另类的《魔幻手机》,以及后来的电影《西游降魔篇》,以及前段时间比较有热度的《黑神话:悟空》,直到今天所谈论的《浪浪山小妖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则是今何在的小说《悟空传》,这部作品也对后来的《黑神话:悟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另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则是马伯庸的小说及由其改编而来的话剧《太白金星有点忙》。而《浪浪山小妖怪》则一反常态,用新的主角四人团来表现西游的故事,既是对过往改编形式的革新,也是对传统的英雄神话的颠覆。
最近流行一句话,叫:“今日欢呼孙大圣,只因妖雾又重来”。为什么中国人甚至全球都对《西游记》或者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这一文化经典如此关注,一方面来自于其原著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也因它对一些社会现象精准的揭露与巧妙的隐喻,当然这也得益于后世对其深刻地挖掘与解读。书中的五个主角,唐僧既是皇帝的好哥们又是如来弟子金蝉子的转世,猪八戒是天蓬元帅的转世,沙僧是卷帘大将的转世,白龙马更是东海龙王的儿子,只有孙悟空是一个石头里蹦出来没势力没背景的猴妖,人们自然会对这样的英雄更具有好感——因为大部分人都与他一样,没有关系也没有背景。但要深挖起来,孙悟空可怕的天赋与其拜入菩提老祖门下这两个因素,已经足以远超绝大部分人。不过,这不影响人们崇拜孙悟空,因为它生来就背负着一种期待,轻可谓斩妖除魔,重可说大闹天宫颠覆秩序。
在《浪浪山小妖怪》中,从野猪到蛤蟆到黄鼠狼再到猩猩,四个人没什么关系,更没什么修为,蛤蟆还算是因为有个二舅可以在浪浪山大王洞求得一职,野猪更是考了三年没考上大王洞的编制。如果不是唐僧师徒西行取经,或许四个人的命运都将在其难以改变的境遇中重复轮回。但也是这四个妖,从最初吃上唐僧肉再到冒名取经,让他们重新发现或是定义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要驯服一个甚至没归在九九八十一难当中的小妖都如此费力,为了打赢黄眉怪甚至损失了四人所有修为返变原形,却仍奋勇向前,其原因却不是那些假大空的正义,而仅仅是“善”。结合后来弥勒佛为黄眉怪修复法力的剧情可见,四位主角的努力全然是白费的,他们甚至没能撼动一点点,西行取经固有的安排。不过另一面也可见,《浪浪山小妖怪》也夹带着一些私货,正如《太白金星有点忙》中太白金星对所有磨难的设置,西行取经本质上不过是走一个形式罢了。
那么为什么说《浪浪山小妖怪》是朝着存在主义式的英雄迈进的呢,在过去我们读《西游记》,总有一种降妖除魔是师徒四人的使命与责任的感觉,进而忽视了“西游”这一行为背后的本质。而浪浪山的这些小妖怪,是自发地将帮助村民作为自己的使命的,他们甚至在后面不再追求诵经成佛,仅仅是为了一口气而奉献了自我。这一点与《长安的荔枝》也不谋而合,李善德明明可以敛财逃匿却仍要孤注一掷,同样是在贯彻自己选择的使命。因此,在意识到自己难以成为“齐天大圣”,或是“天兵天将”甚至仅仅是“妖王”之后,我们想看到的想听到的是,哪怕你只是一只无人问津的小妖怪,也可以勇敢地成为自己的英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