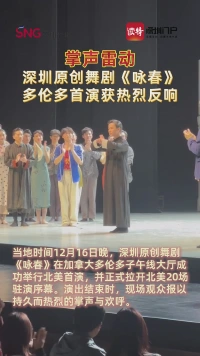王艺洁

20世纪80年代,卡尔·萨根在他的经典科普著作《宇宙》中留下了一行极富诗意的文字:“我们由星辰物质所铸,如今知晓了星辰。”这解释了一个天文学事实:构成人类身体的元素(碳、氧、铁、钙等)均源于恒星内部的核聚变或超新星爆发。也就是说,我们并非“生活在宇宙中”,而是“宇宙的一部分在思考自身”。这一将人类的存在与宇宙演化直接关联的学说,不仅打破了“人与星空”的二元对立,也令人类的“星尘”本质显得浪漫如诗。由此,我想到海德格尔的哲学核心概念——“人的‘此在’让存在得以显现”。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人不仅是“存在者”,更是“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此在”的本质是“可能性”,因为人不是固定的“实体”,而是通过行动、选择、理解来展开自身。如萨特后来所言:“存在先于本质”。“此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存在的“揭示者”,若没有人的追问,“存在”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就好像“美”需要人感知,“真理”需要人阐释,锤子在“锤”时显出了它的“锤性”,人在直面生命时明白了生命的有限性。正如知识不是静态的“真理”,而是“此在”与世界互动的产物,人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世界,而是通过科研、艺术等实践,不断“诠释”存在。薛定谔的猫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假设,而更像是一首充满哲思的诗歌:在确定性坍塌之前,万物皆是可能性的漩涡。梵高在《星月夜》中所绘就的旖旎星空既是物理狂想的湍流,也是人类在宇宙激起的涟漪。人类的求知欲或许正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触须”,以无数实验室中的思想实验来对人类认知的边界进行重构,埋下隐喻。所以,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是“此在”,是“星尘联结”的一部分,便无法逃避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也无法对“自由与责任”视而不见。如此,当我们仰望夜空,看到的不仅是光年外的星辰,更是自己的来处与归途。
其实,人是“星尘构成的生命”这一说法于我们并不陌生,因为这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堪称异曲同工。在宇宙尺度下,人类渺小如尘,却也不动如山,那些看似无常,实则既定的轨道,那些无法臆测,只能探索的法则,不可见,却又如此真实而具体。人在其中,经历着坍塌、爆炸、湮灭,在每一个不曾知晓的瞬息,又何尝不是“方生方死”?宇宙的熵永远在增加,一切秩序终将归于混沌,水会冷,星会熄,记忆也终将模糊。“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不过是熵增在人生命中的具象示现。这样,人又该如何在回视那命运早已标注的转折点时不唏嘘,不遗憾?毕竟,彼时曾浑然无觉。我选择乐观,选择相信生命其实是一场逆熵而行,选择不去撼动过往,而是创造新的意义。我会暂忘“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而是,用一滴一滴的固执,与很多很多的温柔,验证命运微茫而确定的可能,比如,一座山,移向另一座山,一个人,走向另一个人。
(作者系策展人、文化公司创始人、福田区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