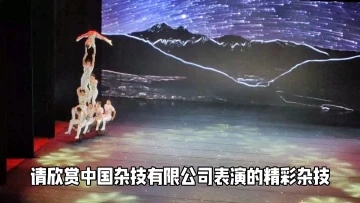西班牙内战(1936-1939)吸引了数量惊人的天才艺术家和作家,激发了他们的灵感,如巴勃罗·毕加索、胡安·米罗、玛莎·盖尔霍恩、欧内斯特·海明威、乔治·奥威尔和约翰·多斯·帕索斯等。当时的欧洲阴云密布,正日益滑向又一次世界大战,捍卫民主、反对法西斯的崇高理想和残酷的战争现实,催生了他们最优秀的作品,如《格尔尼卡》《收割者》《丧钟为谁而鸣》《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西班牙的土地》等。
这场战争也促成了军事和医学技术的突破。新飞机、新武器、新战术和新战略都在激烈的西班牙内战中浮现。炸弹像雨点般不分青红皂白地从天上落下,首次成为可怕的现实;而进步也在恐怖中产生,志愿为西班牙保卫者服务的医生和护士,推动了战地手术和火线输血技术的飞跃。西班牙内战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整个20世纪的实验台。
*文章节选自《地狱与良伴:西班牙内战及其造就的世界》([美]理查德·罗兹 著 三联书店2020-6)。

Guernica Pablo Picasso
苦难与死亡的海洋(节选)
文 | [美]理查德·罗兹
“当格尔尼卡城遭到轰炸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摄影家曼·雷(Man Ray)回忆起毕加索的反应,“他彻底地心烦意乱起来。自世界大战时起,直到这时,他还从未对世界和外部事务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毕加索找到了自己的主题。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飞机
投下的上千颗燃烧弹
使格尔尼卡城
化为灰烬
1937年4月28日的《人道报》大幅报道了这个消息,将其传遍巴黎。法国共产党新近创办、由毕加索的朋友路易·阿拉贡主编的《今晚报》(Ce Soir)于4月30日刊出了格尔尼卡的废墟上浓烟滚滚的照片。毕加索曾对他的一位摄影师皮埃尔·戴(PierreDaix)说,《今晚报》的照片是他将要画的壁画的直接动力。马丁·米恩乔姆指出,他也可能看过4月30日开始在巴黎发行的杜兰戈被炸的照片集。

毕尔巴鄂附近历史悠久的巴斯克小城格尔尼卡,成为第一个被燃烧弹蓄意摧毁的城市
那年年初,多拉·玛尔在大奥古斯丁(GrandsAugustins)街7号为毕加索找到了一处宽敞的阁楼工作室,是左岸一个封闭的鹅卵石院子后面的一幢18世纪建筑,步行不多远就可以到达塞纳河上的新桥(Pont Neuf)。西班牙政府租下了这栋房子供他专用。就是在这里,1937年5月1日,毕加索在对格尔尼卡遭到毁灭深感震惊,对佛朗哥栽赃共和军深感厌恶的情绪下,用铅笔在一张蓝色速写纸上迅速地画下了他对《格尔尼卡》的初步构思。
最初的草图上对作品基本要素的组织,与最终的形式几乎是一样的。从观者的角度看,自右至左为:屋子的角落,或者一座房子暗示有一扇敞开的门;一个人从上方的窗户里伸出头来,一只胳膊举着一盏灯;窗户的下方有一条曲线,向右、向前,然后转弯向左,接近纸的下缘,以表示前景;窗户的左方,一只已死或者垂死的动物的躯体充满了画面的中央,它仰躺在地,两条后腿抬起伸向空中;有某种水平的物体躺在动物的前面;在纸的左上部分,是一头较小或者较远的牛,其背上还有一个带翅膀的物体。
1935年时,毕加索曾谈起他保存照片的兴趣,“不在于照片的拍摄地,而在于画面的变形”。在陪伴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两个星期里,多拉·玛尔所开始做的,正是这样的事情—显然,这在艺术史上还是第一次。但是在他1935年的评论中,他又补充道:“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注意到基本上一幅画是不变的,尽管外观会有不同,但第一点‘视象’几乎是原封不动的。”毕加索在5月第一天手绘的第一张动态草图就将是这种情况:就其基本要素和空间组织而言,已经为随后将完成的巨幅壁画奠定了基础。
一个探索性的变化立刻就发生了:毕加索在5月那个星期六画的五幅草图的第二幅中,将牛和垂死的动物的形象移到了前景—纸面的下半部—垂死的动物已经明显是一匹马了,他横贯纸面画了一条水平的线,将下半部的前景和上半部的背景区别开来。于是背景中在建筑物的左边又容下了另一头牛,在牛和建筑物之间,他又以一条模糊的螺旋形的线,画出了可能是被炸毁的城市的废墟。
这种变化将画面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水平板块,并使前景中的动物与背景中的废墟分离,使得这幅画几乎要变成田园风光式。这样还要求将画面右侧的建筑物及其上方窗户中探出的举灯的人物后移并缩小,这将降低它们在画中的重要性。
毕加索显然对第二幅草图的安排并不满意。他立刻放弃了。当他画下一幅也就是当天的第三幅草图时,他放松了自己的主观控制,也让约束他的半现实主义风格随之而去。在这幅草图中,他画出了放纵、无技巧、近乎无意识的风格,也就是他教自己模仿天真儿童涂鸦的风格。
他在前景中平放了三个无技巧地勾勒出的形象:画面极右边有一匹直立的马,仿佛在挑战地心引力,立在面对观者的一幢建筑物的旁边;第一匹马左边的第二匹马,肚子上有一个大大的泪珠状伤口,里面画出了很多条曲线,表示肠子正在流出;占据着画面左下方的,是又一匹粗略勾画的马,有着粗壮的、弯曲的脖子,反转的头上眼睛在底部,耳朵在顶部,嘴向左边张开,脖子正面是像气球一样膨胀的身子,四条蜘蛛般的腿弯曲着触及纸的下缘。速写在左上部的第四匹马,像第二匹马一样更多地保持了现实主义风格,脖子和头均伸展开。在画面顶端君临一切的,是持灯者的灯,粗线画出的举灯的手臂是从右上方的角落里伸出的,那里流线型的、彗星一般的人头上长着罗马人的鼻子,似乎有些像玛丽-泰蕾兹了。
回归原始或孩童般笔法,那天像以往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对毕加索来说很奏效,使他从现实主义的拘束中解放出来。在第三幅草图中,他在部分解决了填充水平画布,又不用将其分为前景和背景的问题。从右边一直伸展到中央的持灯者,将画面的两个平面连接了起来。那匹痛苦的马也是如此。而且将最右边的马画成直立状,甚至付出让它违抗地心引力的代价,使毕加索产生了可以用垂直物体填充右手边的空间的想法—他立刻试验了这种想法,在第一匹马旁边又添加了一匹马。第一匹马受了致命的伤,疼痛地蹦跳了起来,龇着牙,一只可以看到的眼睛里还掉下了眼泪。
接着,仿佛是为了庆祝,毕加索又拿出了一张蓝纸,将其编号为“4”,画了一匹像是三岁幼童画的马。画面上,一匹马平静地立在用好几道铅笔线表示的地面上,还添加了一个小棍状的大步行走的人物,其手臂欢快地伸向了右下角毕加索通常签自己名字的地方。
毕加索在发现了可以走出死路、又能随心所欲地画自己的画的途径后,接下来又简略地画了一幅强烈现实主义风格的正在痛苦地跌倒的马。这匹马后腿着地,但向侧面扭曲着,前腿绊跌,脖子伸展着,又向后扭动着,马嘴张开着,仿佛在痛苦地嘶叫。这幅动态草图,本身就有令人震惊的力量。在此前画了那幅欢快的像孩子画的马之后,毕加索用阿拉伯数字将这幅草图编号为“5”。
当天那个系列的最后一幅画,毕加索用铅笔和油彩画在了一块长方形的画板上,总结了他迄今的构思:在前景中,一匹瘫倒在地的马肚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里面有一匹带翅膀的小马正要逃走;在垂死的马后面,一个戴着罗马头盔的勇士俯卧在地,显然是死了,他的手中仍然紧握着长矛;勇士的后面是一头异常平静的牛面向着左边,还有一幢有着瓦屋顶的房子,持灯人像先前一样从上方的窗户中探出身子,举着一盏灯。
然而仿佛一天做了这一切还不够似的,毕加索以一张大幅的油画结束了他第一天的工作——《沙滩上的两个裸女》(Two Nude Women on Beach)。这又是他的户外怪物场景之一,是用墨水和水粉颜料画在一张长27英寸、宽22英寸的木画板上的。

On the Beach Pablo Picasso
第二天,5月2日星期日,毕加索又完善了一下马头。在第5号草图中,马伸长了脖子痛苦地嘶鸣,但它张开的嘴里既没有画出牙齿,也没有画出舌头。现在,在蓝色的纸上马头的侧面像有了两种不同的画法。毕加索在检验着这两种方案,一种是将上牙画进马嘴里,另一种现实主义的成分更少,将上牙画在马嘴外,从口套里伸出来。他还将马头简化和风格化,为使马的牙齿保持立体主义的错位,又将马的两只眼睛全都画在马头的近侧。在两幅草图中他都给马画上了很突出的舌头,伸出嘴外以体现牲畜的惊叫。舌头是尖头的三角状,像匕首一样,是从他愤怒地画他那长着刀子嘴的失和妻子、芭蕾舞演员奥尔加·柯克洛娃的画中顺手借来的。由于他已经给持灯人赋予了玛丽-泰蕾兹的容貌特征,他于是再次挖掘自己的私人感情意象,以加强他正评估的画中形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力量。
星期日的第三幅草图画在一张不规则的棕色废纸上。毕加索画出了马惊叫的原因,粗略画出的马头上嘴里满是牙,马的下方用立体主义的手法描绘了一头愤怒地在战斗的公牛,一条前腿抬起,仿佛要刨地,匕首般的舌头颤抖着,竖起的尾巴尖上有一条像是冒着烟的火焰的螺旋线。他将在《格尔尼卡》中保留这条尾巴,并将表示火焰的螺旋线一直延伸到画的底部。
最后,毕加索在一幅3英尺长、2英尺高的画布上,以黑色为背景,用灰色和白色画出了马在嘶吼的头。
接下去的三天,毕加索没有为《格尔尼卡》工作。他大概因巴塞罗那爆发的政治派别间的暴力冲突而心烦意乱。巴塞罗那比马德里更像是毕加索在西班牙的家。他在那里上了艺术学校,在那里度过了青春,在那里最早展示了他的艺术,在那里逐渐形成了他的“蓝色时期”,也是在那里,他发现了《亚威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中的娼妓。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Pablo Picasso
接下来五幅为《格尔尼卡》所画的草图,日期全都写的是1937年5月8日,表明他正在探寻壁画的基本形式。第一幅草图中有牛;垂死的马;未戴头盔、手持一支折断的矛的已死的男性人物;画面右边有一位母亲高举双手,一个死去的婴儿垂在她的膝盖上,这是根据他从德拉普雷的报道中读到的情景衍化的;这些形象之后是一幢有窗户的房子,一条快速绘出的动态线指示了持灯人的位置;房子后面是另一条快速绘出的动态线和一条天际线,似乎在表示远处的火。
然后毕加索从先前的草图中探索了两个形象:那匹马和那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他全神贯注于马牙的位置,画了一匹有前后颌的马,不知为何上牙既在上颌也在下颌。继而他又尝试母亲穿上传统的西班牙服装,包括戴着一件头纱,向后张开,像披肩一样,以突出由母亲的位置向前和向上推所形成的整体的直角三角形。母亲的一条腿从蹲坐中抬起,另一条腿向后蹬去。丰满、下垂的乳房强调母亲在哺乳期,她的孩子还没有断奶就死了。
毕加索整个周末都在继续工作。他先前也这样度过周末。5月9日星期日,他重新画了母亲和孩子的形象并最终完成,是用墨水画的一幅详细的图。他画出了光与影,以用三维表现出两种形式:孩子显然是死了,所以用更现实主义的手法画出,母亲则画得显然极度悲痛。
继而,在那同一个星期日,他进行了整幅画布上的大构图研究,用铅笔在一张4英尺长、2英尺宽的纸上画满了人和物。从观者的角度自右至左为:一张半开的门,上方是燃烧的屋顶;一只肌肉健壮的胳膊举着拳头,从相邻的房子一扇较低的窗户里伸出;母亲和她死去的孩子;垂死的马;马的下方是死去的战士;马的后面是一只马车车轮;马车车轮后面是有瓦屋顶的房屋,持灯人从这座房子的上窗口伸出了她的灯;房屋的左边是一头牛,它身体的左侧面对着观者,但它回头观望着死亡的景象,显得很是吃惊;牛身后还有其他房屋,另一只举起的拳头从上方的一扇窗户中伸出;一个女人坐在门口,抱着一个死去的男人和一个死去的女人的尸体,表情绝望—人物和事件的混杂。至此毕加索可能一直在考虑在燃烧的小城设置一个人、物众多的场面。许多他将最终用于壁画的形象已经出现了,但是构图仍未产生聚合效应。
5月10日星期一,毕加索打磨起个体的形象—母亲和她死去的婴儿在草图上正从楼梯上下楼;已死的马身子扭曲着,头抵在了地上;马的嘴上和头上有了两处变化,旁边还详细地画了一条单独的马腿;牛头呈人脸状。
5月11日星期二,出现了重大变化。毕加索这时已对自己要画一幅什么样的画胸有成竹,他在一张巨幅的木质画框上展开了画布。画布高11.5英尺、长25.5英尺,在大奥古斯丁街7号宽敞的阁楼空间竖立了起来。这个画架实在是太巨大了,以至于不得不挤进坡状的阁楼椽子的翘起处,用长柄刷子来作画,有时还得站在一架折梯上画。画家用黑色颜料和一支狭长的画刷,在巨大的画布上画出了这幅画的第一个完整版本。毕加索的传记作者罗兰·彭罗斯写道:“毕加索画得很快,几乎是画布刚布置好,第一版的轮廓就已经跃然其上。”他派人找来了多拉·玛尔。她带着她的禄来福来(Rolleiflex)相机和灯来了,拍下了《格尔尼卡》的创作过程——也就是毕加索1935年提出的“照片的变形”—的最早一系列照片。她使用的一盏灯映射在画布上,表明最终的画面上方中央将出现一只灯泡。

巴勃罗·毕加索以其不朽杰作《格尔尼卡》对暴行做出了回应。他的情人、摄影家多拉·玛尔摄下了他创作的情景。1937年在巴黎世博会上,人们蜂拥而至,来观看这幅壁画。
大量的书籍和文章都描述过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的过程。不大为人所知的是毕加索在这幅作品中分层植入的许多对其他画作的视觉参考。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加深其暗示和隐喻的视觉效果,以使《格尔尼卡》笃定能名垂史册并流芳千古。这幅画中的几乎所有形象,在大量广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大师的作品中都有两三个原型,由此深化了其意味,就像给已有的词语增添了新意义一样。
对于这种分层植入过程记录最好的例子就是持灯人这一形象。她是女性——毕加索在窗户处添加了乳房,以确保这一点是清楚的—并且在最终的画面中肖似玛丽-泰蕾兹,尽管毕加索在此前的一些草图中,也曾给她画上过多拉·玛尔的头发和面貌特征。e这个形象的来源之一是私密的:在巴黎东北方布瓦热卢(Boisgeloup)毕加索的乡间别墅里,天黑后多拉·玛尔曾经从上层的窗户中伸出过一盏灯,看看是哪位客人在敲门。
由此,线索又引向了毕加索自己的作品,尤其是1935年的《挑战米诺陶》(Minotauromachy)——《格尔尼卡》的前身之一。画中一个纯洁无瑕的小姑娘举着一支蜡烛,拦住了刚刚用剑杀死了一名女斗牛士的巨头的牛首人身怪物。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绘于1638年的《战争的恐怖》(Horrors of War)是毕加索此画的又一个明显的前身。如果你把鲁本斯的画翻转一下,其自右向左描绘的是:一扇部分敞开的门,一个恐惧地举起双臂的女人,一个将手伸向左边、越过一个士兵的裸女,那个披甲戴盔的士兵高举的拳头里还扣着个盾牌,另外还有几个各种各样的士兵形象,或站立或倒下,其中一人举着一支火把。
毕加索显然将这个士兵高举的拳头与他画在《巴黎晚报》头版上高举着锤子、镰刀的手臂联系在一起,并将其纳入《格尔尼卡》的早期版本中。随着画作构思的推进,他将这种对统一战线的团结过于直白的敬礼,逐渐替换为某种象征物,先是太阳,继而是像太阳一样的眼睛,瞳孔中有个灯泡。这些象征物似乎源自画布上映射的多拉·玛尔的照相机的灯光,但也暗指一些西班牙教堂上的“上帝之眼”(Ojode Dios),绘于或嵌于教堂圆顶的内部,俯视着会众,表示在观察和审判所有人。

Horrors of War
Peter Paul Rubens
《格尔尼卡》所暗指的另一个持火把者,是皮埃尔-保罗·普吕东(Pierre-Paul Prudhon)大约绘于1805年的《正义和神圣的复仇追逐罪恶》(Justiceand Divine Vengeance Pursuing Crime)中代表“正义”的带翼人物。这幅画中画了一个倒在地上的赤裸男人,胸部的作品正流着血,画面左边还有一个罪犯正在逃跑。还有一个不太明显但很有可能成立的暗指,是雅各布·乔登斯(Jacob Jordaens)1642年所画的《第欧根尼寻找诚实的人》(DiogenesSearching for an Honest Man),在构图上与毕加索的画有相似之处—第欧根尼举着灯笼立于中央,左边有一人从上方的窗户探身向外张望,在抬头望的牛的地方毕加索画了一头公牛,画面也是横幅。乔登斯是一位佛兰芒画家,是与鲁本斯同时代的人,也是毕加索喜爱的艺术家之一。鲁本斯有时会雇用乔登斯为自己画复制品。第欧根尼大白天打着灯笼寻找诚实的人的故事,与《格尔尼卡》中持灯人的行为有共鸣之处——举起一盏灯,将格尔尼卡遭到轰炸的恐怖景象展现给世人。
最后,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举着油灯、尖尖的手指搭在窗户上的持灯人,会令人联想到高举着火炬、头上有尖尖的光芒的美国自由女神像。这座雕像是在法国建造,于1886年捐赠给美国的。西班牙诗人和评论家胡安·拉雷亚(Juan Larrea)1947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举行的一次《格尔尼卡》的讨论会上指出了这一联系。他认为与自由女神像的暗通,在毕加索是无意识的,但在巴黎,至少有三座规模较小却仍然意义重大的自由女神像的模型。一座在卢森堡公园(Jardin du Luxembourg);一座在塞纳河的格勒内勒桥(Pont deGrenelle)附近,立于一个石头基座上,非常引人注目;还有一座是最早的石膏模型像,在工艺美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et Métiers)。这三座像很可能毕加索全都看见过,他的视觉记忆是非常强大的。

卢森堡公园的自由女神像
整个5月,毕加索都在紧张地为《格尔尼卡》工作。在多拉·玛尔记录工作进展的系列照片上,阁楼的地板上丢满了烟蒂。多拉·玛尔也参与了绘画工作,在受伤的马的身体上添加了许多短竖记号。二人读过同样的报纸上关于格尔尼卡、马德里和其他共和军守卫的城市和小镇遭到轰炸的报道,那些记号会令他们想起其中的语句。皮埃尔·戴指出,毕加索在其早期的报纸拼贴画中,也使用过同样的标记技巧。
塞特回忆道:“当西班牙馆开馆的日子就要来临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在举行开幕式时能否收到画布。有一天在咖啡馆,毕加索对我们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画完。也许永远画不完了。你们最好是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来取吧。’”
5月当中,马克斯·奥布提议西班牙政府为这幅画向毕加索付酬。毕加索则提出捐献这幅画。奥布希望以付酬来换取政府对这幅画的法定所有权。毕加索同意了。5月28日,奥布向他的上司、西班牙驻法国大使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Luis Araquistáin)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报告了他与那位画家达成的协议:
今天上午我和毕加索达成了协议。尽管我们的朋友不愿因完成了《格尔尼卡》而接受大使馆的资助,他想将此画捐献给西班牙共和国,但我反复强调了西班牙政府希望至少要补偿他因这件作品而承担的开支。我最终说服了他,因而给他开出了一张15万法郎的支票,他签署了相应的收据。尽管鉴于这幅画不可估量的价值,这笔钱只不过是象征意义的,但就实际而言,这仍然代表着共和国一笔同样价值的采购。
1937年的15万法郎,价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9.8万美元。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毕加索在内战期间向西班牙共和国的捐赠要数倍于此,此后他也曾私下里向其难民捐过款。因此,以这笔法郎确立了对此画的所有权,应当说是仰仗于奥布的影响力。

加泰罗尼亚画家胡安·米罗也为1937年的巴黎世博会创作了壁画《反抗中的加泰罗尼亚农民》,这是与《格尔尼卡》对应的作品,可惜后来这幅画在战乱中丢失了。
同样是在5月,毕加索首次发表了关于他的政治信仰的政治声明,对巴黎流传的他支持佛朗哥的谣言做出了回应:
西班牙的战争是反动派对抗人民、对抗自由的战斗。我作为一名画家的整个人生,无非是同反动派和艺术的死亡所进行的不懈的斗争。怎么会有人产生一丝的念头,认为我能与反动派和死亡达成妥协呢?当叛乱开始后,合法当选的西班牙共和国民主政府任命我为普拉多博物馆馆长,我立刻接受了这一职位。在我正在创作、我将称之为《格尔尼卡》的画作中,在我近期的所有艺术作品中,我都明确地表示了我对军人集团的痛恨,他们使西班牙陷入了苦难与死亡的海洋。
皮埃尔·戴在评论毕加索的画,也就是对格尔尼卡轰炸时写道:“实际事件的标志,在那匹马身上,是形成错视的报纸拼贴画;也在那巨大的画布上,像当时的画报杂志一样,几乎是没有颜色的。”这话说得很对,但不全面。画布像电影屏幕一样大,投射在其上的形象—在1937年,像当时的电影,当然也像当时的纪录片一样,是黑白的—并不是正常大小,而是大于实际尺寸,正如电影要映出移动物体的形象。毕加索很喜欢动画片。他认为动画片不仅仅是娱乐,而且是一种新技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他借鉴动画片,正如他借鉴他所遇到的所有工艺和技术一样。他想象中的捕捉《格尔尼卡》中的景象的相机是立在地上的,看不见天上穿梭来往的飞机。它记录的是地上的人们和动物的反应。
T. J. 克拉克写道,在《格尔尼卡》中,“女人的惊恐和好奇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她们甚至在毁灭的时刻都要扮演见证人的角色。她们仿佛是被固定和冻结在一种机制、一种框架上。炸弹是战争完美的抽象物—纸上的战争,作战室里想象的战争,作为‘政治的其他手段’的战争。当战争真正来临时,就是这个样子”。《格尔尼卡》中活下来的人全都是女人,毕加索曾在一次评论中说女人是“忍受痛苦的机器”,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这话冷酷无情,然而尽管如此,这话也揭示了一个秘密,当这位西班牙画家步入晚年,放松了足够的戒心后,他解释道:“我是个女人。”
女人,是的,但他也是个男人,一个艺术家:《格尔尼卡》中的公牛以一头野牛的原始而令人难解的目光抬头凝望着。皮埃尔·戴说:“在此一个高贵的对手,面对着令他感到羞辱的杀戮,厌恶地转过身去。”那头公牛有着一双毕加索的眼睛。
“5月和6月,毕加索继续[画着]他的画,”塞特回忆道,“有一天他带着画来到了展馆。我想那是6月下旬。我记不清准确的日期了。他把画带来了。他非常喜欢这幅画,当真认为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幅作品,是他本身的一部分……他把《格尔尼卡》带到了展馆,把它在水泥地上展开,然后又放上了一个绷画布的框架,然后贴在了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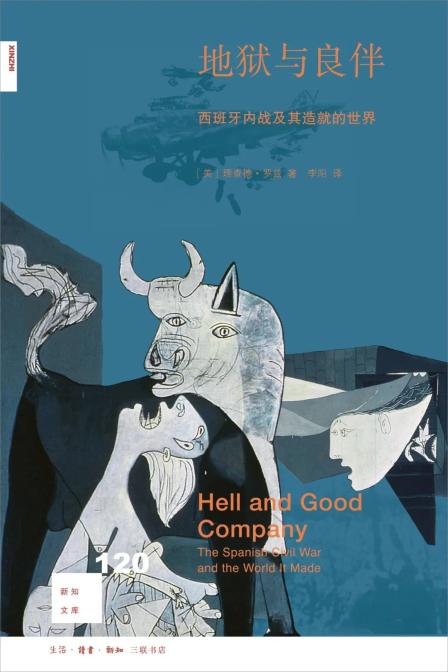
地狱与良伴:西班牙内战及其造就的世界
[美]理查德·罗兹 著 李阳 译
编辑 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