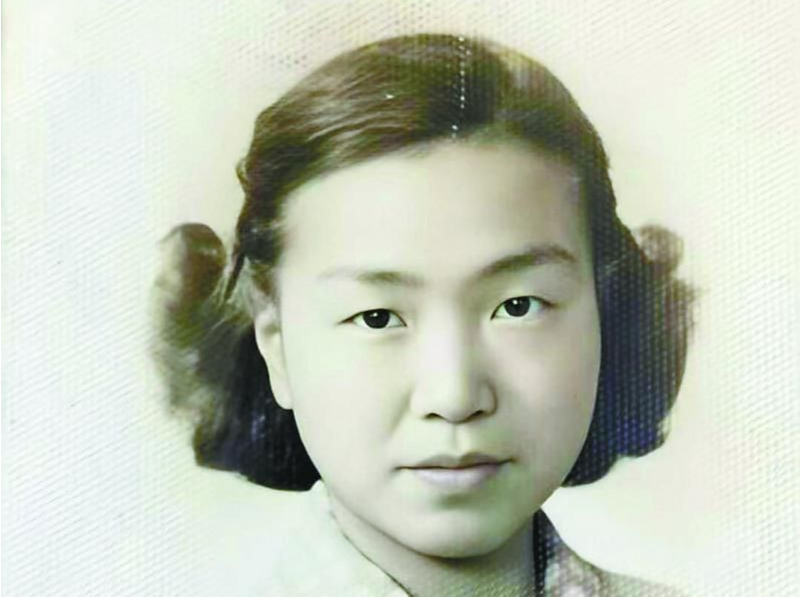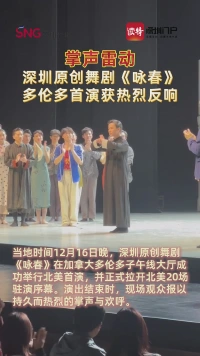文学作品的“成功”经常会伴随着诡秘的天助。由复杂的深圳经验凝练而成的短篇名作《出租车司机》就是这种超自然现象的见证。无法想象也难以理喻的神奇笼罩着它整个的生命过程。请允许我首先采用倒叙的手法从最近的神奇说起:时间是2013年5月19日的清早,地点是蒙特利尔皇家山西北面的一间公寓。
我通常是早上6点左右起床,这一天也不例外。起床之后,我通常要用大约一个小时洗漱和晨练,这一天也不例外。然后我会空腹在电脑上工作一个小时,这一天也不例外。例外的是,我通常会将每天最饱满的状态据为己有,用来写作自己的作品,而这一天我却在开机的一刻临时决定将其挪作他用,用来审读前一天收到的那篇论文。那是一篇聚焦《出租车司机》重写过程的论文。在论文的开头,年轻的学者遵循惯例,回顾了作品的“成功”之路。简短的回顾收尾于201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短篇小说卷》。这个权威的选本一共选出70位作家的70篇作品。在论文作者看来,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共和国70年来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我一贯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凸显时代的精神,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论文作者简短的回顾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世纪之交的激情岁月,也让我回想起那一位又一位将“出租车”锁定为“千里马”的文学编辑。怀旧和感恩不仅冲淡了审读论文的枯燥,也让我在审读完成之后决定拨打其中一位选刊编辑的电话。这当然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因为我交替着感叹和赞叹的话题与电话两端的现实都毫无关联。我感叹的是时间的流逝,我赞叹的是伯乐的眼光。而谦和诚恳的编辑一如既往,将功劳全部归于《出租车司机》……接下来是早餐。早餐之后,我通常会先做一些不需要特别用脑和用眼的家务,然后再回到屏幕前坐定,这一天也不例外。而重新在屏幕前坐定之后,我通常会先查看一下邮箱,这一天也不例外。接下来的剧情却完全超出了想象:邮箱里只有一份新到邮件,而邮件的内容只是一则“商品简介”。被简介的商品是一本名为《50:伟大的中国短篇小说》的书。它选出的是新文学百年历史(1918年-2018年)里最具文学价值的50篇作品。顺着“伟大”的目录看下去,不出所料,我看到了二十五年五个月零一天之前从深圳开出的那辆平凡的“出租车”。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即使我没有心血来潮地挪用“一日之际”来审读那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的论文,即使我没有接着又情不自禁地拨打那个关于《出租车司机》的电话,这一则与《出租车司机》高度相关的“商品简介”也会在2023年5月19日上午进入我的视野。但是惊叹之余,我还是宁愿将这两个“即使”改为“如果”,将接下来那一句的肯定变为否定,也就是将自己破例的行为与商品神奇的出现“唯心地”勾连在一起。我这样做的根据是:《出租车司机》整个的生命过程都笼罩在无法想象也难以理喻的神奇之中。

▲《50:伟大的中国短篇小说》收入从深圳出发的《出租车司机》。
首先是“生”之奇。1996年春天,在结束长达五年的休耕之后,我开始重返文学。具有象征意义的第一步从故乡迈出:《湖南文学》杂志在第七期推出了我的一组篇幅不大却充满诗意的小说。它们立刻引起了《人民文学》一位编辑的注意。来自北京的约稿信很快寄到深圳。我也马上选出篇幅相当的两篇现稿寄去。11月4日收到的退稿信实际上是一封更迫切的约稿信。第二组作品紧接着寄出,结果是其中的一篇获得留用。这对我已经是值得骄傲的成绩。而自信的编辑却不以为然,继续写来约稿信,还明码标量,要“五千字左右”。我回信坦言手头没有达标的作品。可是这坦言既不能息事也无法宁人。如下的回应在12月18日的下午寄达:“你不是作家吗?!你难道不可以现写一个吗?”这当然不是对我的嘲讽,却立刻引起了我的羞愧。晚餐之后,我被深深的羞愧推出家门,推出小区。我沿着深南大道往西走去,口里不停地重复着编辑的质问。在接近东门路口的时候,我看到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接着是一对关系好像不太融洽的男女下了车。刹那间,羞愧升华为美感:一篇字数达标的作品完整地出现在我的头脑里。我立刻停下、转身,接着小跑着回家……“写下一篇《出租车司机》。”当天日记里的最后这一句话已经成为现在的文学史料。
接着是“显”之奇。《出租车司机》在《人民文学》1997年第10期的刊登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当时因为沉寂多年的《遗弃》突然成为知识界的话题,而备受关注的《天涯》杂志又正在推出我的“战争小说”,我对此并不介意,也渐渐淡忘了《出租车司机》。三年转瞬即逝……2000年9月23日下午,一位学者从广州打来电话,说在新一期《天涯》上看到了我的作品。而我骤然的兴奋被对方说出的作品题目骤然凝固。这怎么可能?我年初就已经收到战争小说《首战告捷》的留用通知,已经苦苦地等待了八个月。这是怎么回事?我匆匆挂断电话,匆匆出门下楼,匆匆翻开在路边报亭里找到的《天涯》杂志……眼见之实刹那间将我推进两难的绝境:难堪不受待见的旧作神秘复出!难过异想天开的新作离奇缺席!我匆匆回到家里。我匆匆拨通主编的电话。我必须立刻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刊登已经留用八个月的新作,却刊登三年前就已经发表过的旧作。电话关机更增添了悬疑,也让我的恼怒迅速转化为白纸上的黑字。四天之后的清早,主编从海口打来电话,首先回应《出租车司机》是他在我夏天的一个附件里看到的,接着保证《首战告捷》会尽快刊登……天啊,这诡秘的“梅开二度”竟是出于我自己电脑操作的失误!这怎么可能?而接下来的剧情早已为众所周知:绕道《天涯》的“出租车”在很短的时间里开进了从最大众的《读者》杂志到最高端的《新华文摘》的“几乎所有的选刊”,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罕见的“雅俗共赏”之势。
接着是“变”之奇。这辆从深圳开出的出租车没有因2001年的狂奔而熄火,这是与它相关的另一个神话。2009年底,我受聘为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悠闲又优越的生活让我的身心迅速进入理想的文学状态。那时候,“深圳人”系列小说已经成为我可以看到的远景。一天傍晚,我意识到重读一遍现有的作品会大大利于后续的创作。我的重读自然从《出租车司机》开始。那是自1997年12月28日向《人民文学》投稿之后的第一次细读。那是将要改变我整个文学道路的细读。曾经有学者声称《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字都不能增减的作品,而我在第一段就看到了叙述和语言上的冗余与缺失,意识到有的部位必须增补,有的部位必须删减。母语语感在之前两年里的离奇突变终于落实为“中年变法”的具体诉求!我恍然大悟。就这样,痛苦苛刻的重读引发了激情澎湃的重写。经过重写的《出租车司机》首先于2012年3月20日到3月21日由《晶报》“人文正刊”推出,也成为随后所有选本的正选以及所有译本的底本。我的重写与那种出于各种现实动机的改写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纯粹的美学实践,一种虔诚的艺术探索。或者就说它是整“容”手术,不是变“性”手术吧。而更神奇的是,《出租车司机》的重写开启了我文学生命里规模宏大又旷日持久的“重写的革命”。这已经是学术研究的课题,在此就不再赘言。
再接着是“衍”之奇。《女秘书》于2005年8月14日在《晶报》刊出。主人公陪同烂醉的老板坐进一辆出租车的细节马上让不少的读者意识到《出租车司机》是一篇将要不断衍生的作品。“重写的革命”如同加大油门,大大提高了《出租车司机》衍生的速度。到2012年的秋天,十二篇“深圳人”系列小说已经全部到位,也大都已经在名牌杂志上发表。大半年之后,它们以《出租车司机》为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随后进入多种书榜,成为当年显赫的出版物之一。回望《出租车司机》神奇的衍生过程,我很想知道文学史上还有哪一篇作品具有如此的生育能力,更不要说如此的优生能力。另一个细节也值得注意:“深圳人”系列小说首次结集出版的时候,我在《深圳人》与《出租车司机》这两个书名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选定后者,为的就是突出“衍生”之意,也强调数典不能忘祖。
最后是“洋”之奇。《出租车司机》是“深圳人”系列小说里最早被译成其它语言,也是被译成最多语言的作品。除了英译之外,它还有已经发表的法文、意大利文和蒙古文译本以及还没有发表的韩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它有两个已经发表的英译:一个刊登在《人民文学》的英文版上,译者是后来因为翻译《三体》而知名的刘宇昆(他曾经在一个访谈里提及《出租车司机》是他翻译过的“最好”的短篇小说)。另一个版本则出自“深圳人”系列小说英译本的译者Darryl Sterk。“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都是相当幸运的作品,大获主流媒体的赞誉又深受普通读者的喜爱。我因为这两个译本接触到许多普通的“洋”读者,在纽约、伦敦、巴黎、悉尼、奥克兰、旧金山、渥太华、多伦多……他们将“深圳人”当成自己人,肝胆相照、感同身受。“走出去”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梦想,而《出租车司机》已经带领“深圳人”跨过梦想与现实的边界。
一辆“粤B牌”的出租车开进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史,这是1997年12月18日傍晚在深南路与东门路交会处被灵感击中的作者无法想象的,这也是2023年5月19日上午在皇家山西北面的公寓里与“伟大”同行的作者难以理喻的。对作者来说,这两个相距二十五年五个月零一天的场景好像都是幻影,好像都是错觉。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最“成功”的虚构人物突然充满了疑问:他是否已经彻底走出顿失妻女的惨痛?……他能否在故乡的土地上获得终极的救赎?
编辑:陈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