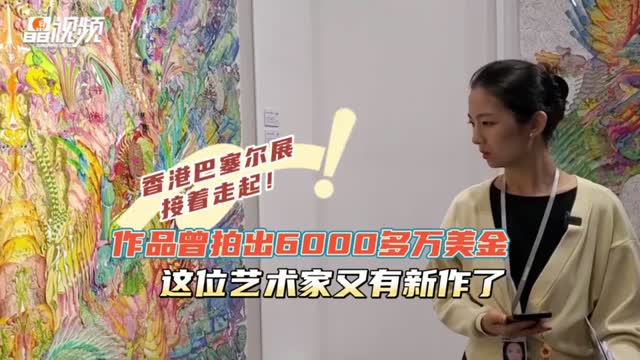■楼佳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社会语言学高级讲师

作家西西曾把香港比喻为一座“浮城”,“在浮城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要靠意志和信心”(《浮城志异》,1986)。这种“悬浮”的意象时常伴随着我在巴塞尔香港展的观展经历,引人思索的是:热火朝天的展馆内与展馆外的这座城市究竟有什么关系?

正在香港艺术中心展出的倪鹭璐油画《合掌》(2017,200x250cm)。
1970年由几位瑞士画廊经纪人在巴塞尔创立的艺博会现已扩展到迈阿密、香港和巴黎。虽然巴塞尔成功地在现代艺术和全球资本之间画上了金闪闪的等号,但它多年来与其主办城市的脱节成为许多学者和公共舆论批评的重点。2015年英国《卫报》曾撰文抨击迈阿密巴塞尔纸醉金迷,而对美国此起彼伏的社会问题却又无动于衷;2018年巴塞尔的组织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空降了一项大胆的城市公共艺术实验,旨在开辟南美市场,遭到了处于经济危机中的阿根廷人的质疑和冷落。知晓这些的香港艺术家也对巴塞尔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矛盾心态,他们甚至略带嘲讽地用广东话将Art Basel音译为“呃巴嫂”。可是作为一个游走在边缘的局外人,我也许没有那么多身份压力,可以相对中立地观察这些年来巴塞尔和香港艺术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样的变化。
向内的反省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早在1944年就指出“文化产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能够巧妙地吸纳对自身的批评,甚至将其转化为另一种文化商品。今届巴塞尔为这个论点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宣传海报的照片摄于具有香港特色的街头巷尾,并在展区中增加了不少本港画廊和艺术家。例如,安全口画廊展出的19位艺术家中有17位来自香港或是居住在香港的外籍画家。此外,前文中提到过位于土瓜湾牛棚艺术村的独立艺术空间1a space也受邀请在不收费的展区外开设特别的展位。在一场关于亚洲艺术市场的讨论中,与会者也都同意收藏家和艺术投资人有责任推动本地艺术。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艺博会充分表现出艺术市场对席卷全球的反殖民思潮的回应,着重推荐了不少来自东南亚和非洲的艺术家,并组织了一场关于收藏非洲和非裔艺术的特别论坛,可谓AI艺术之外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出生于埃塞俄比亚的美国艺术家安沃·艾力克更是在作品中采用了不少香港文化的视觉元素,比如霓虹灯和红烛台,与象征非裔历史的符号混搭,艾力克还在附近的太古广场装置了一个10米高的充气埃及法老雕像,成为巴塞尔在香港的第一个场外装置。
展会中最接地气的作品可能要属晶报记者谢晨星在直播视频里着重介绍过的《推车派对》。作为本年度“艺聚空间”展区的13件大型艺术装置之一,林岚的作品由六架固定在混凝土里的手推车撑起14米的蓝色拼布组成。这些从城市里收集的废品在展会中为观众提供一个可以聚集也可以休息的庇护所。他们抬头望到的布艺天幕是草根出身的艺术家和香港女工协会的纺织工人合作完成的,而撑起这片天的小推车则由林岚工作室楼下的冶炼师傅改造。《推车派对》不仅符合了“艺聚空间”的场域独特性,更是唤起了参观者对香港劳工的生存状态和物质消费主义的思考,而香港很多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也坐落于城中各处工业大厦。约翰·伯格曾说,好的艺术能改变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在林岚的作品之中停留片刻之后,我也开始留意在香港街头用小推车运送沉重货物的工人们,也许正是他们微不足道的身影撑起了这座浮城。
浮城的沃土
个人感受此届巴塞尔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香港艺术界对艺博会似乎少了一些对立的尴尬和拘束,多了一些主动的参与甚至友好的竞争。就好像一位画廊经理在预展期的一个论坛上所说,疫情之后,整个香港的艺术生态系统,从公共机构到独立艺术家,都联系得更为紧密了。的确,以往通常在五月才举办的巴塞尔今年提早了一个多月,与自1973年开始每年都是三月举行的香港艺术节几乎同步。同一个月中,从尖沙咀的香港艺术博物馆到黄竹坑的刺点画廊有无数大大小小的艺术展览开幕。

M+的特展《香港:此地彼方》。
就在同一个会展中心,紧贴着巴塞尔的是2014年创立于香港的Art Central(前生是香港艺博会), 主要合作单位之一便是香港旅游发展局。他们抓住盛会的机会主打本地与亚洲艺术,连展览区块都以粤语命名,而比巴塞尔便宜了好几倍的门票也在周末吸引了不少市民。今届的展会一进门就是中国内地艺术家杨泳梁长达18米的视频作品《极夜烟火》,漆黑的房间里,一朵朵绚烂的烟花在山水画般的大湾区夜景中升起,照亮了天空和观众惊叹的神情。这个创作于2019年秋天的作品诗意地强化了对香港地理的重新想象,又同时提醒观者反思城市的过度发展对我们生存环境带来的影响。
预展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巴塞尔便被朋友邀请去几步之遥的香港艺术中心参加另一个展览的开幕礼,其展出的是已被收藏的香港艺术学院校友的作品,其中不少名字也出现在巴塞尔和前文提及的其他展览中。借助着艺术月带来的人气,这次展览将校友、老师和收藏家们聚集一堂,集中展示了这所创立于2000年的非牟利学院在绘画、陶艺、雕塑和摄影多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学院也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与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RMIT)合作开设双学位艺术课程,为香港培养了大批艺术家。
关于巴塞尔的诸多报道中有一种说法:今届艺博会显示出香港作为亚洲艺术中心的地位不可动摇,可是我想这种活力不仅得益于运行顺畅的艺术市场,更是本土艺术家多年辛勤耕耘,内省反思,厚积薄发的力量。好像古老的榕树,即使生长在浮城的边缘,也可以紧紧缠绕悬崖边的石头,根深叶茂。
流动的边界
巴塞尔开幕前一周,我在中环某个电车站看到香港艺术家智海的作品《等海》(Waiting for the Sea, 2022)出现在宣传海报上。在陆地和大海之间,阳光与阴影似乎描绘一个人类学里的“临界空间” , 画中人物从一个时空过渡到另一个时空的过程中带着难免的忧伤与彷徨。这种临界感也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手法,比如画家倪鹭璐刚开始在艺术学院学画时,油画老师觉得她太东方,鼓励她去学水墨,而水墨老师又觉得她太过西化,还是劝她主修油画,于是成就了她意笔油画的个人风格。“临界空间”可能是充满了不安的,但也充满了边界的流动性。

巴塞尔宣传海报上智海的油画《等海》(2022,45.7x60.8cm,安全口画廊)。
巴塞尔结束后我又来到位于西九龙的M+视觉文化博物馆。周日的人流在前往草间弥生回顾展和M+主推的希克收藏展的电梯前排起长队,而电梯背后的《香港:此地彼方》略显冷落。这个免费的展览涵盖了曾经遍布香港街头“九龙皇帝”曾灶财的民间书法,1980年代《号外》杂志的封面,1990年代流行音乐的海报,还包括了汇丰银行的商标设计,美孚新村的建筑模型,和扎哈·哈迪德于1983年参与山顶俱乐部设计的建筑群构思方案,彻底打破了传统艺术与视觉文化之间的隔阂。令人疑惑的是这个深耕本土视觉历史的展览在M+的空间里却处于一个虽然便利但是边缘的位置。今年6月11日该展就将闭幕,访问西九龙的游客要去哪里寻找属于香港的艺术之源?
离开博物馆,细雨濛濛,我沿着人烟稀少的西九龙海滨走去地铁站。夜色中,M+幕墙上瑞士艺术家皮皮乐迪·里思特的作品《信手不渝》格外瞩目,它面对着维多利亚海港张开庞大的双手,但我觉得更能象征香港艺术的是暴露在海边用来填海的石头,多年来一直默默地扩展着浮城的边界,只是等着大海的到来。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