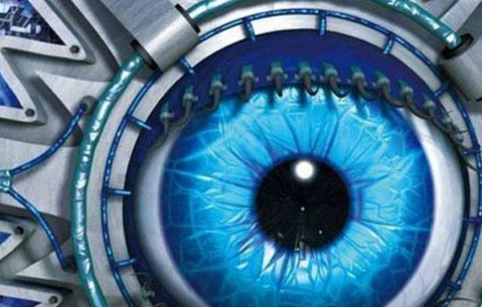盛祖宏
走进光明日报社
1960年8月,25岁的我,身穿一套褪色的旧空军服,留着平头,走出了北京张自忠路3号人民大学的校门,迈进了石驸马大街上《光明日报》油漆斑驳的红门,开始了编辑的生涯。从助理编辑、编辑、主任编辑到《文摘报》副主编、新闻研究部主任,一干37年,可谓“奉献了青春又贡献了一生”。当我提着一捆捆书刊资料告别《光明日报》七层大楼时,我已是一个年逾花甲的小老头了。
我的作者朋友
在我先搞副刊、后搞电影评论、而后又编辑副刊的那些年里,结识了一批青年朋友,有的至今还保持着联系。
记得我到文艺部当美术编辑不久,一个青年人来到编辑部,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一头乱发像一丛野草,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腋下夹着一幅白布蒙着的油画。他自我介绍,他是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画了一幅画想请编辑看看。我帮他把白布揭开,一看是一幅人物画,画面的正中是一个女邮递员,两手握着身旁的自行车把,画名叫《信鸽》,我觉得此画不错,人物形象美丽生动,心里暗想可以刊用,就请老美编、版画家荒烟(已故)来看,他也认为不错,就把画留下了。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这幅画就刊登在《东风》副刊上,我让画占了三栏半宽的位置,并且居于版面的中部,显得很突出。可以想象一个青年学生的习作,能够像著名画家的作品一样,堂堂正正地(不是补白)刊登在一张中央大报上,他的心情是何等激动。当他再次来编辑部取回原作和样报时,一再重复感谢我的话,把我的手都握痛了。此后还发表了他几幅油画。从此他走上了美术家之路,成为当代著名的舞蹈速写画家,他就是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士英。
在我搞电影评论编辑时,结识了一批有潜力而无名气的中学教师。那时奉命批判好几部 “毒草”影片,却难以找到理想的评论家,一些过去写赞扬文章的评论家“不宜”再担任批判的任务,于是我想到在中学教师中寻找新作者。我先后到北京男八中、女八中、三十一中、111中等校,组织语文教师成立写作组,集体撰写批判文章。
我最先去的是报社斜对面的女八中(现名鲁迅中学),我向语文组老师说明来意,他们都很乐意写稿。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从中宣部“批发”来的批判精神,然后请他们看有关影片。在集体讨论形成若干观点之后,大家推陈漱渝执笔。他写出的初稿,难免有观点“偏颇”之处,我提了些意见,他拿回去又认真地重写了一遍。对于中学教师写的第一篇重点文章,我格外看重,特别细心地从头到底修改了一遍,有个别段落进行了改写,使文章得以顺利通过,作为打头文章刊登出来,署的虽是集体名字,实际上是陈漱渝的处女作。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没什么价值,但却是一个业余作者在成长道路上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以后他通过我认识了学术部的编辑,写了若干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后来他把兴趣转移到研究鲁迅上,成为有影响的鲁迅研究专家。
在“文革”时期,需要组织一批评论好影片的文章。我从来稿中发现一篇评论《地道战》《地雷战》的文章基础较好,是右安门中学两位教师写的。第二天,我忍着隐隐的胃痛,骑车出了永定门,向西转弯,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骑了一阵子,才找到这个无名的学校。
两位作者听说我是《光明日报》的编辑,脸上露出非常意外和颇为欣喜的神色,在简陋的办公室甚至有点不知所措。我在一张旧木板椅上坐下,说明了来意:稿子基础不错,修改后可以用。我具体指出文章的缺点是观点淹没在对情节的复述中,必须把观点突现出来,材料为观点服务。
过了两天,作者之一的冯立三把改写稿送来了。我粗略看了一遍,还有观点不够突出的毛病,但鼓励了他几句送他走了。文章经我改写后很快刊登出来。处女作的发表,使冯立三非常兴奋,劲头很大,向编辑部要题目。我和姓赵的编辑又让他写评论《红灯记》的文章,帮他找好了角度。他的第二篇评论《一条围巾的妙用》又发表了。接着他又写了“批林批孔”的文章,我把它推荐给《北京日报》我认识的编辑,也顺利发表了。如果他自己寄去,可能会石沉海底。从此他和我成了朋友。粉碎“四人帮”后,他调入《光明日报》,逐步成长为文学评论家。
像陈漱渝、赵士英、冯立三这样通过稿子而认识的青年作者,后来成就较大的,还有儿童文学作家庄之明、《人民教育》总编刘堂江、杂文家司徒伟智和刘克定,还有一直坚持在教育岗位上的申士昌、滕云、李复威等。
我还曾在工人中发展作者队伍,请他们看戏或电影,告诉他们编辑部意图,让他们写歌颂或批判文章。当时最有趣的是联络信号。有的工人在电话上联系好了,但没见过面,要请他们看影剧,可票来得太晚,或双方的距离较远,就约好几点几分在某某剧场门口见。互相不认识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手头举着一张露出《光明日报》报头的报纸,就是联络信号,就像地下工作者接头那样。这办法真灵,屡试不爽。
这批工人作者中的佼佼者,后来有的成为《北京日报》的总编辑,如刘宗明;有的是《旅游》杂志的总编辑,如蒋国田;有的当了《中国艺术报》的总编辑,如张虎。退休后我们仍有来往,不过有趣的是,不是我向他们约稿,而是他们向我约稿了。
写到这里,我要声明一句,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己功,狂言我培养了什么人什么家,我只是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帮了一把而已。
我的作家梦
实现我青少年时代的作家梦,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事。
时代变了,像批判包产到户变为鼓励包产到户一样,对知识分子从批判“成名成家”逐渐变为鼓励“成名成家”了。我的写作劲头上来了,每天爬格子往往到深夜,休息日成了全天写作日。那时除了写杂文,还写科普小品、人物传记、文艺评论、报告文学、散文和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最早发表在《丑小鸭》杂志上,后在《河北文学》《牡丹》《春风》(季刊,辽宁出版)等杂志上发表,总共写了十余篇。其中《不是冤家不聚头》被黑龙江电视台改编为单本电视剧《小草青青》,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但影响不大。最有影响的是《第八任总编》,在《春风》上刊出后,报社同事纷纷到资料室借阅此杂志,因为从中可以看见报社的影子;此文也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作品与争鸣》杂志予以转载,该杂志同期刊出女作家杨沫对此文赞扬的评论和史乘批评的文章。
在人物传记方面,应天津新蕾出版社之约,为《科学家的童年》丛书写了林巧稚的童年、华罗庚的童年。
1978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出了我的通讯《一个压不跨的地质尖兵》。这是为知识分子平反的典型事例,刊出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予以比较详细的播报,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经过了什么都写时期后,我觉得要集中兵力,攻其一点了。于是我主要攻杂文了。因为写小说的人太多,我没有竞争优势;杂文,虽写的人不少,但写得好、有影响的作家不多,我在报社工作,处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得风气之先。于是我全力以赴,很快见到成效,几乎全国重要报纸,都刊出我的杂文。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求是》杂志、《北京日报》《新闻战线》,到《文汇报》《羊城晚报》《杂文报》《今晚报》《共鸣》杂志等,几乎遍地开花,很快扩大了我的影响。
当然,文艺作品主要是以质量取胜的。在我几百篇杂文中,在全国有影响的也只有几篇。1986年2月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的《尊重隐私权》,是在全国较早提出“隐私权”概念,被《读者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还有《官本位与“家”贬值》《“座次学”初探》等在《人民文学》等杂志刊出后,引起了众多读者尤其是知识界的共鸣。我的杂文《数字系祸福读》获《光明日报》《杂文报》联合征文一等奖,《导弹、圆珠笔及其他》《“半跪式服务”质疑》等共三次获《人民日报》金台奖。1989年9月,在作家、编辑雷抒雁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我第一本杂文集《隐私权·座次学·出国热》。2002年起,北京杂文学会为会员出版个人杂文集,每年选10人为一辑,我被选入第二辑中,因此我的第二本杂文集《“送礼学”发凡》得以在2003年9月问世。
1985年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选自盛祖宏《三十七年在光明》)
(作者盛祖宏系光明日报原新闻研究部主任)
编辑 黄泽霖 审读 李诚 审核 赵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