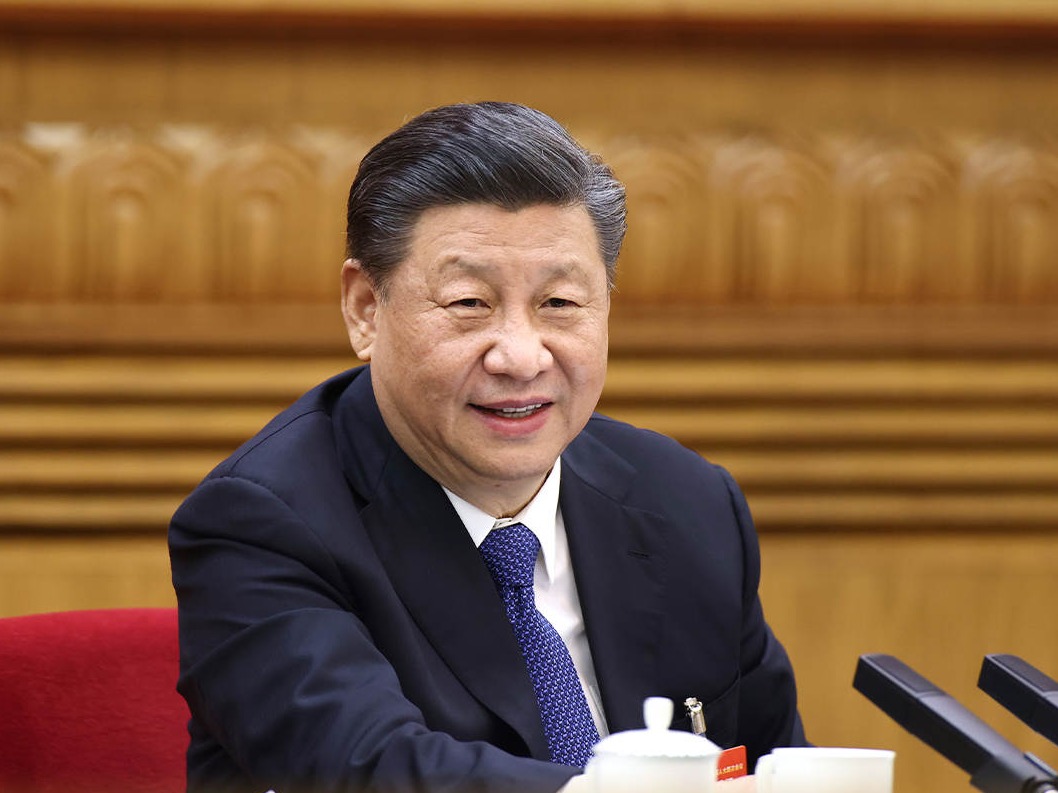阿伟(左)在排练演出节目《戒毒小苹果》,中休之余吸根烟。
阿伟的故事:热爱化妆事业却染上毒品
记者面前的阿伟,个子不高、眉清目秀、喉结明显,说起话来男声十足,如果换掉身上的戒毒人员服装,肯定是帅哥一枚。
“他平时见到男朋友,语气如女孩一样,如果只听声音不见人,一定认为是女的在说话。”阿伟的管教戒毒警察说,艾滋病同性恋戒毒人员已由之前的2人增加到8人,成为戒毒管教警察的新课题。
在“12.1”国际艾滋病日来临前夕,读特记者30日来到广东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专管区,聆听了两名同性恋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心路历程。
阿伟现年27岁,来自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小学、初中都在云岩区读书。”阿伟说,小时候就喜欢学跳舞、学钢琴,从不去踢足球、打篮球和乒乓球。到了小学6年级,性取向开始有了明显变化,自己以女孩的身份开始与男同学接触,每次能牵到该自己心仪男生的手,都会感到幸福无比。
到了初中,阿伟开始留长头发,穿女性化的服装。为此,他被迫转学。
转学后,阿伟与跨年级的一男同学成为好友,经常一起逛街,牵手、抱抱、亲嘴是常态。“那不是实际意义上的亲吻。”阿伟说,双方都没有想过将这种感觉深入发展,也不懂得如何发展。
初中毕业后,阿伟就不再上学。“因为别人看我的眼光很怪,”阿伟说,15岁时,他就在家帮母亲干起了杂活。
16岁那年,阿伟离开贵州,到深圳小姨家。在深圳玩了一年后,阿伟觉得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前往北京,到某知名形象设计去学习化妆。2007年,阿伟回到深圳,他利用一年的时间复习老师所教的课程,并进行创新;还到知名的化妆品专柜,了解化妆品的特性,最终确定自己喜欢的品牌是香奈尔和迪奥。
2008年,阿伟开始将自己所学的用于实践。
第一单生意是给夜场的小姐们化妆,每晚要完成20多位小姐的装扮。“成本低、速度快、钱到手快。”阿伟说,他与夜总会管场的分成,夜总会3成,阿伟7成。每月收入7、8千元。
能自食其力,阿伟很开心。“怎么会找与小姐接触的工作呢?”阿伟说,因自己是女性装束打扮,与小姐们相处融洽,自己很热爱这份工作。
2009年,阿伟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女性装束了,于是开始换回男性服饰。
在一个日本婚纱品牌的推介活动现场,阿伟与化妆师郭某分到一个组,当时30岁的郭某已是从事化妆行业多年的资深师傅。郭某详细地询问阿伟的个人情况和对将来的规划后,对阿伟将来的大致方向给予指引。郭某还经常介绍化妆客户给阿伟,让阿伟参加一些文艺舞台的化妆工作。“他是我的化妆和同性恋的启蒙老师。”阿伟说。
“你是不是‘同志’?”阿伟说,与郭某成为好朋友后的一天,郭某试探性问他性取向的问题。郭某敲开了阿伟的同性恋之“门”,给原本对同性恋懵懂、模糊的阿伟清晰的指引,带领阿伟迅速融入到同性恋群体中。
阿伟学会了“同志”间的专用术语;如何识别真假“同志”。“进这个圈子久了,身上就会散发某种特殊气质。”阿伟说。
2009年的秋天,阿伟与一位客户来往密切,这名客户30多岁,平时西装革履,衣服总是很干净、整洁。在客户的慢慢引导下,双方超越了界线,阿伟扮演了女性的角色。
“因为此前没有尝试过,第一次很不习惯,”阿伟说。然而十几天过后,阿伟就习惯了,不再抵触,还会很想,一发不可收拾,两人的恋爱关系一直持续了一年。
2011年,阿伟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30岁的“同志”,对方是一名设计师。阿伟与设计师的恋爱关系一直持续到2013年,是阿伟与恋人中相处时间最长的。
2014年3月,24岁的阿伟开始吸食K粉,常到深圳罗湖区的某酒吧,当时只要去这个酒吧,就能拿到K粉和摇头丸。
2015年7月,阿伟应邀到一“同志”家里与“同志”们聚会。期间,“同志”们开始吸食冰毒,一名“同志”手把手教阿伟。
“K粉、摇头丸吸食后,整个人晕、飘。”阿伟说,冰毒吸食后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人很“清醒”,很喜欢说话、聊天,不停地聊,聊一整个通宵也不困、不累、不饿。每位“同志”带阿伟玩冰毒的过程都不一样,阿伟很快就离不开了冰毒。
此后,阿伟通过社交网站,认识了第三任同性伴侣,两人吸食冰毒,发生性行为可持续一整个通宵,由于超强度接触,导致双方皆受损出血。阿伟因此而感染了艾滋病。

阿伟拿着播放器,指导其他艾滋病戒毒学员排练演出节目《戒毒小苹果》。
2015年9月,阿伟在某KTV吸食毒品时,遇到公安干警突击检查,被查出吸毒送戒毒所,随后因查出艾滋病被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专管区。
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之后,阿伟如五雷轰顶,对传染他的第三任性伴侣十分憎恨。2017年4月,阿伟戒毒期满出所,立即找第三任伴侣质问,对方承认自己是艾滋病人。
2017年6月,阿伟因复吸毒品被查,再次送到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
“一切只能怪自己。”阿伟说,回想自己的经历,已不再憎恨传染他艾滋的“同志”。
与此同时,阿伟对化妆事业的热衷却一直没停下脚步,他甚至考取了国际化妆证ITEC的职业证;2013年参加上海文化化妆大赛,获得了最佳创造二等奖。
阿伟的母亲知道儿子是同性恋时,好不容易接受了事实;此后,阿伟吸毒,其母亲一直不相信,后来被迫接受;2017年4月,阿伟离开戒毒所,其母亲知道儿子得了艾滋,双方冷战了一个多月。
此次进戒毒所,阿伟的母亲下了最后通牒,再复吸毒品,母子永不相见。
阿伟说,出去后他仍会继续从事化妆工作,与“同志”交往和性生活会做好安全措施,不考虑找女朋友,至今他没有和女性朋友有过亲密接触。

艾滋病专管区的草坪上,艾滋病戒毒人员在练习瑜伽。
阿从的故事:双性恋当中他还是选择了做“同志”
与阿伟相反,阿从则有过两任女朋友,并有亲密的性关系。
阿从现年29岁,来自湖北黄冈浠水县。2017年3月因吸毒被深圳公安机关查获,9月送到广东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
阿从小时喜欢和女孩们一起玩,但没有对男生有特别的感觉。大二开始追求同班的一位女生,最终同居。 “那时19岁,对男女之间的事无比好奇和疯狂,”阿从说。
2007年大专毕业后,阿从到惠州某公司实习,做仓库保管员,月工资2600,除了租房、水电、还要日常开支,倍感经济压力。女友的母亲反对这段姻缘,要女儿随家人到上海发展,阿从被迫与女友分手。
阿从努力地工作,从仓库保管员做到店长兼采购,工资涨到8000元。他的勤奋赢得一女同事的好感。
女同事来自河南,比阿从小2岁,每天都主动帮阿从洗衣服,慢慢两人之间擦出了火花,开始了同居生活。
谈及与两位女朋友相处时光,阿从说两个女孩都对他很满意。而此后同性恋的生活,阿从说是截然相反的,此前是自己照顾恋人,很辛苦;而后恋是恋人照顾自己,很享受。阿从与阿伟一样,在同性恋中都是扮演女方的角色。
2008年,阿从还与河南女友同居的期间,通过网聊结识一名男网友,时间长了,知道对方是“同志”。出于好奇,阿从与网友见面吃饭,发现“同志”与正常人没有区别,于是双方留电话。
此后,网友开始经常给阿从发信息,言词中充满了赞美和明显的示爱。阿从说,自己却一点都不反感,反而感觉很受用,觉得自己被人捧在掌心里、美滋滋的。
2009年春节前夕,家人要阿从回老家湖北过节,阿从说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一个人在深圳过节,自己要陪一下。阿从所说的朋友就是“同志”网友,他俩之间有约定。
初七将至,而自己日夜翘首以盼“同志”网友却没有出现,阿从伤心欲绝,他跑遍了自己所知的药店,买到30颗安眠药。
大年初六晚,阿从写好遗书,将自己与“同志”网友的恋情写清楚,自己的死是因为恋人失约所导致。随后服下所有的安眠药。
大年初七,回到深圳的姐夫将阿从送到医院抢救。阿从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回到姐姐家,在房间里躺了半个月,不吃东西、不说话、伤心欲绝。
家人理解阿从的苦衷,劝阿从别急着确定性取向,要慢慢搞清楚,等到了30岁再决定自己是“同志”还是娶妻生子。
自杀未遂半年后,阿从就与一个新认识的“同志”发生了性关系。
此后,阿从共交往了5个相对固定的“同志”男朋友,除了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外,还与20多位“同志”发生了临时的性关系。至今,阿从还不清楚自己是哪个环节感染上艾滋病的。

采访结束,同性恋艾滋病戒毒人员阿从返回习艺区。
2014年夏天,阿从又与一男朋友分手,空窗期孤独无聊,他通过手机交友软件,认识了比他小1岁的“同志”男朋友,此男友是某报社行政人员,负责薪酬统计工作,此任男友与阿从相处时间最长。
“时间长了,感觉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感觉弱了,性生活少了。”阿从说,自己患有艾滋病,而“同志”男朋友没有艾滋病,每次都做好防范措施。
2015年起,阿从就依赖在“同志”男朋友家里,全靠男朋友照顾,不上班,也不愿意出家门。最后,男朋友忍不住劝阿从找点事做,两人因此产生矛盾。
2016年8月,阿从与报社工作的“同志”男朋友分手。无聊之余,应邀到艾滋病病友家聚会,开始吸食冰毒。
回想自己历程,阿从说自己对不起家人,尤其是母亲。当年得知自己患了艾滋病,母亲第一时间告所有的亲戚朋友,几乎每天都有亲戚朋友约阿从吃饭,让阿从明白:艾滋病不会受到家人和亲戚朋友的歧视。“母亲可谓用心良苦。”阿从说。
为了回报母亲,阿从交了首付,在姐夫老家的城市供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20年的还贷。“万一自己死了,母亲去投靠姐姐,还有房子住。”
阿从目前已解除毒瘾,他希望自己能尽快出去,找份工作,继续还贷。
【读特新闻+ 】
戒毒场所的新课题
“扮演女性角色的同性恋艾滋病戒毒人员,大都渴望关怀和爱护。”广东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分所(艾滋病专管区)政委沈初军说,像阿从母亲这样动用亲情接纳同性恋艾滋病儿子的事例是很少的,大多数都被歧视,缺乏亲情和关爱。
沈初军说,此前的艾滋病专管区,同性恋艾滋病戒毒人员只有2名,今年增加到8名,形成4对。
这对于戒毒管教警察是新的课题,既要尊重他们的性取向,理解他们的生理需求;又不能让他们违反戒毒场所的纪律,不能在场所内有亲密行为;更不能硬生生地将他们隔离开,避免情绪波动和矛盾激化。
目前,8名同性恋艾滋病戒毒人员的都安排在不同的宿舍和楼层,平时可相见,但没有发生亲密行为的机会。
编辑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