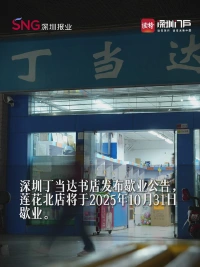■薛忆沩
我外婆名叫张先恺,出生于1915年9月29日(农历乙卯年八月二十一)。《外婆的〈长恨歌〉》是我关于她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发表的时候,我相信她能够将《长恨歌》一字不漏地吟诵到一百岁。可是,我的相信与现实有三年零十五天的差距。2012年9月14日夜晚,老人家平静地跨过了生死之间的边界。这时候,她的五位姊妹中还有两位健在于此岸:一位是她的大妹妹,一位是她的小妹妹。许多读者已经通过《最老的“魔方”》见识过我外婆的大妹妹:那位94岁的时候从县城的书店里买走那套多年无人问津的《沈从文文集》的乡村老妪。她名叫张先范,出生于1917年10月22日(丁巳年九月初七)。她是我外婆的姊妹们当中生活最苦的一位,也是唯一没有离开故土进城安居的一位。但是她的寿命最长:在读到《最老的“魔方”》将近三年之后的2022年2月14日,也就是她一百零四岁生日过后一百一十五天,才撒手人寰。而我现在这篇清明节当天开始动笔的文章写的是我外婆的小妹妹。她名叫张先怡,出生于1925年3月11日。我现在的心情与我写前面提到的两篇文章的时候大不一样。前两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主人公”本人读的,颂德之余还带有明显的祈福甚至励志之意。而我最小的姨外婆,这位一生都阳光灿烂、活泼欢快的姨外婆已经于2022年12月24日夜晚停止呼吸,距离她同样有足够实力去庆祝的一百岁生日还差两年零七十九天。

1
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看上去有点荒诞的题目?位于洞庭湖之南的湖南省距离横贯北大荒中部的完达山大约有两千五百公里,在地理上相去甚远,在气候上也大相径庭,是什么样的机缘或者魔力能够将两者扯进题目中的偏正关系?
答案就在下面这首现代人写的旧体诗里:
湖南儿女不知愁,完达山中雪作裘。
百日皆夸茅屋暖,一冬尽与赤松游。
大呼乔木迎声倒,小憩新歌信口流。
痒煞烹调能手技,替人风里煮猴头。
稍有文学修养的读者就能够判定这是既有功底又有特色的好诗,应该出自名家之手。而更有文学修养的读者或许会从这现代气息与旧体韵味完美的融汇联想到中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是的,这首诗的确就是那颗“天外彗星”上的亮点之一。
《伐木赠张先怡》是这首诗的题目。根据作者聂绀弩本人的经历,不难推测诗中提到的“一冬”指的就是跨越1958年底和1959年初的那个寒冬。在那个特别的寒冬,被周恩来戏称为“20世纪最大的自由主义者”的著名诗人之所以会夫妻双双把家离,与包括我姨外婆在内的一千三百多名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一起“伐木”于北大荒的完达山中,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不必讳言,也无需细说。
熟悉我姨外婆的人都会折服于诗人的慧眼和妙笔。这首诗的确将我姨外婆的个性和神态勾画得活灵活现、淋漓尽致。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段落如果有幸不被当成蛇足之笔的话,就算是我为这首名诗提供的一份旁注吧。
我于一九八一年夏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电子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八月中旬来到北京之后不久就见到了我外婆经常提起的小妹妹。她的谈吐比我想象的还要欢快,好像她一生经历的都是趣事;她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敏捷,好像她此刻面对的尽是游戏。而我对她的想象主要是基于两段他人的叙述。第一位叙述者当然就是她那位堪称“故事大王”的姐姐。在我外婆关于她小妹妹的故事里,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小妹妹在旧社会最后一次回湖南老家的经历。与她同行的是她当时的同学和未来的夫婿。那位出自上海富裕人家的革命青年是他们在南京就读的中央大学里的风云人物。可他竟然如此不谙世事,没有西装革履或者锦袍绸褂,而是穿着一身旧布军装前来“过门”,看上去既不像才俊,更不像阔少。家里的主人们因为深知“满小姐”(湖南习俗以“满”称排行最末的姊妹)独立的个性自然不敢质疑和多嘴。但是,家里的佣人们却忍不住了,纷纷在主人们面前埋怨“满小姐”的眼力……那时候,旧社会即将成为过去,新中国已经成为定局。身为中央大学英语系高材生的“满小姐”不仅具备敏锐的眼力,还充满青春的激情,已经跟上时代的步伐,投身革命的洪流。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现代与传统相冲突的生动故事。

▲回望人生的姨外婆
2
另一位叙述者是姨外婆极为健谈的长子。他在我进京的前一年来长沙出差。听说我喜欢西方文学,他激情澎湃地谈起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说那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作品,说作品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如何如何地成功,说作品里生命与金钱的对比又是如何如何地强烈……最后他告诉我,《热爱生命》是他母亲最热爱的英语短篇小说。那是我第一次听一位亲戚谈论我没有听说过的西方文学作品。我开始想象我最小的姨外婆是什么样子。我也开始相信血缘的关系有可能转变成精神的财富。
在北京的四年,我成为姨外婆家里的常客。我唯一的义务是偶尔充当一下劳动力。因为当时她的四个儿女都不在北京,而她的家又是在没有电梯通达的五层楼上,换煤气罐成为我的主要责任。回报是超值的:家常便饭也许不值一提,那海阔天空呢?
我们的话题的确很宽很广。从文学到科学、从汉语到英语、从历史到家史……与她的两位姐姐相比,姨外婆大脑中存储的古代诗文的数量毫不逊色(据说在去世前不久,在已经不认识家人的情况下,她还能接着护士给她起头的诗句轻松地吟诵下去)。而她又有极好的理科头脑,经常与我探讨科学方面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她有一段时间能够将魔方痴迷到半专业水平的生理基础(我笔下“最老的‘魔方’”其实就是她精心培养出来的)。我们也有过许多关于语言的讨论,比如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那四个灯谜(1983年的除夕我是在姨外婆家里度过的);比如我发现英语里的“here and there”在语用上更接近长沙话里的“各里那里”,而不是普通话里的“这里那里”,她完全同意,也觉得英语与方言的这种联系很有意思……我外婆经常提到她的小妹妹不仅天资很高,还从小就非常努力。有一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姨外婆承认这的确是事实。她说这是因为她从小就知道女孩子在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里没有地位,不加倍努力就会变成“泼出去的水”。而她不愿沦为泼出去的水。她要靠自己的努力融入时代、融入社会。
北大荒的生活自然也会成为我们的话题。而她那句充满喜悦的口头禅总将我的美学带往革命的浪漫主义,而不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关于寒冷的喜悦可略举一例:他们将刚洗好的衣服晾晒到低矮的茅屋顶上,衣服马上就会被冻僵而“站立”起来,“可好玩了!”关于收获的喜悦也可略举一例:有一天在深山老林里发现了一个特大的猴头菇。一片欢呼声之后,有人提议要将这罕见的收获送往北京,献给领袖。接下来当然是一片更大的欢呼声。瞧,那些本应该饱蘸冤怨的心灵的深处荡漾着的仍然是狂热的敬爱,“可好玩了!”
姨外婆这句好玩的口头禅充分表现了她的乐天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何处?它当然有一部分是来自遗传、来自天赋。但是它更大的部分无疑是来自后天的磨练。有日记为证。1983年2月23日,与我同样有许多精神交流的姑姥爷在他任职的《红旗》杂志编辑部里突然离世,生命的脆弱再一次对我脆弱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我第二天的日记里留下了一条这样的记录:“张先怡教育了我——用她被折磨出来的乐天情绪。”我已经不记得当天“教育”的具体内容,但是姨外婆“被折磨出来的乐天情绪”却从此刻骨铭心。

▲展望人生的姨外婆
3
在北京那四年,我进出最多的文化设施是中国美术馆,而姨外婆任职的冶金工业部就在中国美术馆的斜对面。因此,姨外婆的办公室也成为我挖掘精神财富和感受乐天情绪的场所。我想这是外地大学生很少有机会享受的“特权”。另一种特殊的享受是,姨外婆曾经两次到北航的学生宿舍里去看望我。还有哪位同学在校期间享受过祖辈的看望?要知道那个时候从北京城里乘车到北航的门口就已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从学校门口走到我们的宿舍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种看望除了必备情感的支持,还必需身体的保障。姨外婆两次来到我的母校不仅让我感动于亲情的温暖,还激起我对她旺盛生命力的敬意。
“母校”的情结还用另一种方式将姨外婆和我连在一起。我人生里最初的七年是在长沙周南中学(“文革”之前是女校)花园式的校园里度过的。周南中学是杨开慧、向警予、丁玲等人的母校,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有着广泛的联系。而周南中学也是我姨外婆的母校。她在母校的经历与历史关系最深的细节莫过于她与一对姐妹同学的闺蜜之情。这是我很早就从我外婆的故事里熟知的细节。那一对姐妹也出自宁乡大户人家。姐姐名叫“秦厚修”。这是一个现在偶然会在时事节目里出现的名字,因为这位大小姐后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马英九”。
家常可以这样越拉越长……还是回到我早就想好的结尾上来吧。姨外婆曾经与我分享过她生命中的一个小秘密。她说她经常下班之后独自去漫步天坛。从她的生动描述,我知道黄昏的天坛并不“好玩”,但是却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宁静、幽远、神奇……我相信,走进与天相通的黄昏是姨外婆面对孤独的方式,甚至是姨外婆应对孤独的方式。
姨外婆与我分享的这个小秘密让我对天坛充满了敬畏。这大概就是我在大学四年里游遍了北京城的风景名胜,却从来没有走进过天坛的原因。我好像是害怕自己平庸的目光和浮躁的呼吸会惊扰那应该只属于姨外婆美丽心灵的宁静、幽远和神奇。
我至今也没有走进过天坛。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