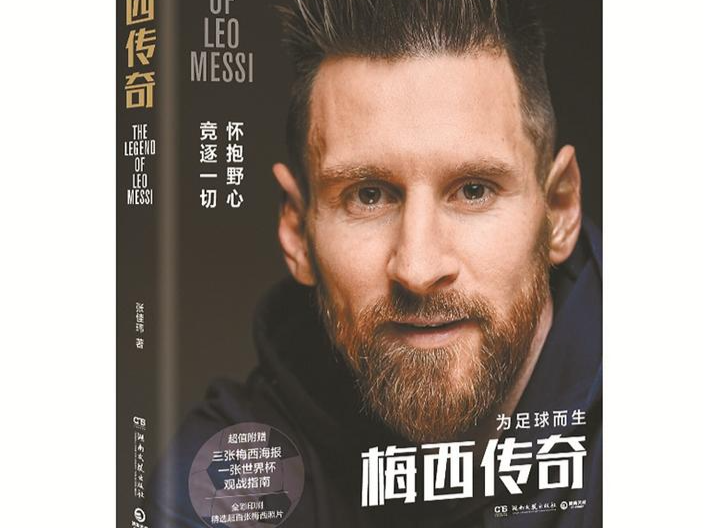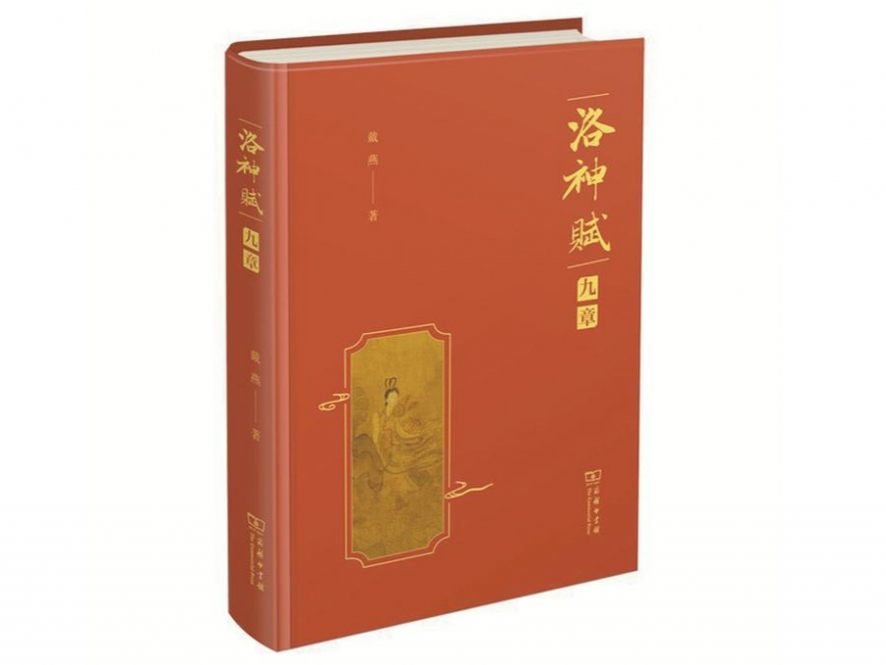杜拉斯的名字,中文读者并不陌生,即便没有看过她的小说,也大多知道梁家辉主演的电影版的《情人》,也一定在某处听过“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句话。“活着让我不堪重负,这让我有写作的欲望。”为了不遗忘,杜拉斯不知疲倦地记录下她的“一切”。终其一生她都在写作,用写作尝试抵达自身的真相。
今年3月,中信出版·大方推出四本杜拉斯的作品:《就这样》《战时笔记和其他》《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此次出版的这四本书并非杜拉斯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作品,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补足了杜拉斯的形象。

▲中信出版·大方出版的杜拉斯著作四种
其中,《战时笔记和其他》《就这样》是首次在国内出版;《外面的世界I》《外面的世界II》曾于1997年由漓江出版社、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引进过,此次出版是时隔十多年之后,它们再次与中文读者见面。四本书的译者谭立德(《战时笔记和其他》)、袁筱一(《外面的世界I》)、黄荭(《就这样》《外面的世界II》)三位老师都是国内法语文学界资深的译者和研究者。

《战时笔记和其他》是杜拉斯的早年作品,书的主体部分是杜拉斯在1943—1949年间写的四本笔记,晚年的杜拉斯在橱柜中发现这些笔记本,将其封在一个题字“战时笔记”的信封里,赠予法国国家图书馆。虽然取名“战时笔记”,但它们记述的范围超出了战争。在其中一些自传性质的叙述中杜拉斯提及了她人生中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印度支那的童年时光,其中更是出现了关于“中国情人”的最早的回忆版本,很多传记作家也将这些手稿上的文字当作她的故事的可能的真相。书中还收入十篇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字,完善了作家的早年形象。那时候杜拉斯的想象世界刚刚建立起来,殖民地溽热的气息、建筑堤坝的母亲、暴虐的大哥哥、温柔的小哥哥、“情人”、死去的孩子、集中营里归来的丈夫……所有这些在她后来的作品里常常出现的形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端倪。

如果说《战时笔记和其他》呈现了杜拉斯的早期写作,《就这样》则带给我们一个晚年的,临终前的杜拉斯。这本书收入从1994年11月20日到1996年2月29日(杜拉斯逝世于1996年3月3日)杜拉斯重病卧床期间口述或写下的文字,由她最后的伴侣扬·安德烈亚收集整理而成。文字按照书写的日期进行标注,每日写下的只言片语组成一首关于爱与死的长诗。
过去的人,说过的话,随口而出的玩笑,面对现实,哭泣。沉重的死亡就在眼前,绝望一阵阵涌来,迫近的虚空和失落让人恐惧。对死亡的执迷伴随着想要活下去的强烈渴望,杜拉斯在生命的最后,像她那个徒劳地建筑堤坝抵挡太平洋的母亲一样,企图用文字抵挡死亡。就这样,杜拉斯追求极致的写作和人生在这里画上句号。
书中标注的最后一个日期是1996年的2月29日,三日后,杜拉斯离开这个世界。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也是她终其一生都在写作的一个证明。


《外面的世界I》和《外面的世界II》则是热衷于私人写作的杜拉斯为身外世界所写。两本书收入了杜拉斯从1957年至1993年间写的报刊文章、序言、书信、随笔,有的已经发表过了,有的从来没有刊行过。有的是应邀所写,有的是自己有感而发想要写的。有的文章关于当时法国的社会事件,有的是因为一部心爱的电影,一帧看了良久的画作,一次相逢,一夜寂寞。
虽然是为身外世界所写,但其中依然融入了强烈而鲜明的杜拉斯的文字风格和情感。她自己也说,即使作为记者去报道那些当时发生的社会世界,她也不认为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她会明确地甚至带着强烈情绪地去报道,尤其为那些受到不公的人发声。
这四本书可以说呈现的是杜拉斯不同的但又同一的侧面,它们最终汇聚到那张被命名为杜拉斯的“备受摧残”的面容中。是自身的故事也好,是身外的世界也好,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这些都不重要,所有这些她不知疲倦地写下的,为了不遗忘而写下的,都只有一个真相——杜拉斯。
本期书评,我们摘选《外面的世界Ⅰ》译者袁筱一再版序以及作者前言,走入真相中的杜拉斯。

▲早慧少女玛格丽特·杜拉斯。
“外面的世界”,是内在包裹外在
文|袁筱一
今年的春节,在北京的冰天雪地里买过一本《电影花粉》。那是一次奇怪的不期而遇,作者在写芭铎的时候,引用了这样的话:
“她美得如同任何一个女人,但却像个孩子一般灵活柔软。她的目光是那么简单、直接,她首先唤醒了男人的自恋情结。”
小小的引号,小得几乎看不见。我终究没有耐心在书店里纠缠下去,看个究竟。以为莫名的熟悉感只是因为杜拉斯。杜拉斯真的是这样读的,不经意间撞到,撞在自己不知哪一根神经上,生生的有些疼。可是年龄越大,越知道这些疼是该忍着的。撇开自己做了这些年法国文学不说,站在一个纯粹的读者立场,她是因为这个才在中国流行的吧。就像《花粉》的作者,是因为撞到了“男人的自恋情结”这几个字。
书买下来,回到家泡上茶,在烟花爆竹声中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的文字,是经过自己手的,杜拉斯的文字。是自己在若干年以前译的《外面的世界》里的文字。这份确认让自己觉出一丝的欣喜来。文字照出了自己的影子,自恋,又何止是男人呢。
而在那个时候,我还在译序里写:一切终将冰雪消融。
我希望消融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最终一定会消融的,是什么呢?
这次不期而遇,却仅仅是个开始。没想到今年和杜拉斯的纠缠竟然要到令冰雪也无法消融的地步。这才相信,如果相遇是命定的,如果相遇被视为命定,自己是不甘心让一切如冰雪般消融的。
于是创造相遇,先是《杜拉斯传》在台湾付印,然后是在全校的法国当代文学公选课上再度讲到杜拉斯,再然后是没有轰轰烈烈,但多少有些声音的“杜拉斯辞世十周年”的活动,最后,在这年就要过去的时候,我重读了这本《外面的世界》。
几年前的回忆于是一点点地回来,当年读杜拉斯、写杜拉斯、译杜拉斯,当年的喜欢、震惊,还有当年那一点点因为疼痛到麻木的厌烦。
即便是在杜拉斯已经被译滥、写滥的今天,《外面的世界》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话题。因为它呈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被奉为中国小资必读作家的杜拉斯其实有大量的文字是关于“外面”的世界的。然后,再一点点地深入进去看,看她写的政治事件,看她写的社会问题,看她写的明星,看她写的艺术,会理所当然地发现,她的“外面”并没有那么外。她自始至终没有站在旁观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当她需要——如果我们相信她在随笔集开始所写的那段序言,当她结束一本书,需要挣脱自己,或者需要钱的时候——走到外面的时候,她仍然毫无保留地任自己冲入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裹挟。她观照这个世界的目光,从来不曾冷静、客观,她仍然是激烈地爱着的,激烈地爱着,所以恨,恨所有的不公平,恨所有的不可沟通;同时,也羡慕所有自己所不具备的品性:宽容和独立。
《外面的世界》因而还给了我们一个连带的命题:她的其他作品——尤其是所谓“自我虚构性”的小说——真的是如此内在吗?
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一定会消融,因为这个世界里所有的物质最终一定会走向结束。这其中,包括爱,包括文字。绝望来自这里,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抵抗这种绝望有两种途径:无知或是超乎寻常的,西西弗斯的勇气——那种走向灭亡,却充满幸福感的勇气。和大多数人一样,杜拉斯没有这份勇气,然而走进文字世界的人又回不到无知里。
在《美丽娜》那篇文章里,提到自己的《夏夜十点半》,杜拉斯说,于是,必须喝酒,对于爱情的结束,可以怀着同样的激情和乐趣去经历。
或者更甚于此,在杜拉斯看来,我们还可以成为爱情的作者,这是抵抗结束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办法。就像《夏夜十点半》里的玛丽亚,她说,你们的爱情会有一个作者,那就是我。
杜拉斯说,所有走向结束,以新的介入开始的爱情会有一个作者,那就是我。这才是写作的缘由。写作所包含的,是失去、绝望、孤独和激情。是面对存在的种种悖论,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高贵的选择之一。远远超过了“自我虚构”的意义,超过了一个十五岁半的法国小女孩和中国情人的故事背后的“真相”的意义。
不希望消融的,却明知道一定会消融的,是爱,以及因为爱而产生的文字。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用玩味绝望的方式抵抗绝望,只是,时至今日,杜拉斯的绝望已经成为绝望的酵母,弥漫在太多人的文字里。其中的原因,杜拉斯也在《外面的世界》里做出了回答。她认识的一个小女孩问她,如果没有人感到温暖,那么温暖又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感到绝望,那么绝望又是什么呢?
绝望是所有的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绝望是所有的美好走向毁灭的必然;绝望是这冬天的雨,而在这冬天的雨中,去年为你撑伞的人已经离去;绝望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虚构世界的人物混作一团,却无能为力的心情——固然有成为一切爱情始作俑者的奋争,可是对于个体来说,绝望在何时、何地成为过一件好事呢?
出乎意料,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是个很慢的过程。有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包括错误和我自己以为不再合适的文字。但是一定也留下了另一些错误和别人以为不合适的文字。这是译者的绝望,永远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有时有进不了门的尴尬,有对自身身份和存在的怀疑。只是但愿有人知道,没有第三者的存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爱情或许根本不会发生,更不能够继续。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在我重新看《外面的世界》时,我得知这本书里的《面黄肌瘦的孩子》被选进了某个版本的《大学语文》里。爱情发生了,这是作为第三者的译者所得到的最好的心理补偿。而作为作者,杜拉斯也该得到安慰,辞世十年之后,对于她在法国现代文坛的地位的肯定也没有更多的争论。是的,作为个人,我们可以爱,也可以不爱,但是,文字早已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摄影师伊莲娜·邦贝尔吉(Hélène Bamberger )与杜拉斯于1980年在特鲁维尔见面后成为了朋友,两人交往25年,直至杜拉斯去世。她拍下杜拉斯生活的点点滴滴,家中的物品、写作的桌子、最爱的风景和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
为外面的世界而写
文|玛格丽特·杜拉斯
没有不涉及道德的新闻写作。所有的记者都是伦理学家。这绝对无可避免。记者就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人,观察这个世界的运转,每天,站在很近的地方注视着它,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得以再度审视—这世界,这世界里的事件。从事这项工作就必须对所看到的东西做出判断。不可能不做。换句话说,所谓客观的信息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谎言。从来没有客观的新闻写作,没有客观的记者。我已经摆脱了许多加之于记者的偏见,而这一点,我认为是最严重的:相信可以理清一桩事件的客观联系。
为报纸写作意味着即时写作。不等待。所以,这样的写作应当让人感觉到这份焦灼,这份迫不得已的快捷,以及一点点的不假思索。是的,不假思索,我不讨厌这个词。
您瞧,有时我自己就会给报纸写点儿文章。时不时地,每当外面的世界将我吞没,每当发生了一些让我疯狂,让我必须窜出去、走到大街上去的事儿—或者我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有时的确会这样。
因此,我为报纸写文章的理由很多。第一点无疑就是让自己走出房间。如果我写书,每天都要写上八个小时。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写其他文章。我蜷缩在窝里,时间对我来说一片空茫。我害怕外界。写书的时候,我想我甚至都不读报纸。我无法在写书的间歇插进这样的事情,我不明白身边都发生了些什么。而写文章对我来说就是走出我的房间,那是我最初的影院。
还有别的理由,比如说我没钱了。所有应景之作都很来钱。要不就是我答应了人家的,例如我答应过《法兰西观察家》为它写定期专栏,于是我就不得不定期交稿,比如说在1980年,我为《解放报》写专栏。
我之所以写作,在报纸上写文章,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为各种运动所席卷,难以抗拒:法国的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反政府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以及反选举运动;或者,和你们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想要揭露某一阶层、某一群人或某一个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论是什么范围内的不公正;而如果一个人疯了,丧失了理智,迷失了自己,我也会因为心生爱怜而写;我还关注犯罪,关注不名誉的事,卑劣的事,特别是司法无能、社会允许之时,我会做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一种自然的评判,就像人们评判暴风雨和火灾。这里,我想起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我很愿意把它放在篇头—— 《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我也想起了《奥朗什的纳迪娜》,想起了《“垃圾箱”和“木板”要死了》,想起了公共救济事业局的那些孩子,还有在1958年,十八岁就掉了脑袋的人;而我与乔治·费贡的所有谈话亦属此列,他是我的朋友,坐了十四年牢才出来;我还想到了施瓦西—勒洛瓦的西蒙娜·德尚。
文章有的是为外界所动,我乐于写的。也有的是为了糊口不得不写的,比如我为《星座》写的那些文章,我都签上了姑妈的名字,苔蕾丝·勒格朗,这些文章早就找不到了。还有的是在战争期间,我们为年轻人写的连载文章,当时只是为了挣钱买黑市上的黄油、香烟和咖啡,而今也不见踪影了。
有不少文章都丢了,其中有一篇是写卡拉斯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去看过她的歌剧,但正是这篇文章养活了我一年的时间,我别无选择。
我忘记了不少自己写的文章。但是我不会忘记自己写的书。书是从来不会忘的。我忘记了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除了我的童年,还有那些我认为是超越日常生活规则之外的事。对于每日流逝的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我的孩子。
剩下来的,便是与我的生活同时展开的许多事件。写作的动机无非是上述那些,或者还有别的。每每有所不同,就像所有的相遇、友情、爱情或悲情故事的演绎都不尽相同。
当然,不是我自己想起来要出版这些文章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这要归功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名流丛书”的负责人让—吕克·海尼,是他动了念头要把它们辑在一起。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一下子竟有些害羞呢?如果我们只把今天写的东西拿出来,可能这世界上一个作家也没有,而如果我们只喜欢今天写的东西,不喜欢昨天写的,那么现在剩下的可能只是贫瘠,是的,现在,这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还有一点注意事项。我上过不少回当。我声明这本书的版权归我自己。
对这些文字,我没有做出过评价,我甚至没有再回头去读一遍。扬·安德烈亚替我做了这一切。我全权交给他去处理。这一切与我再无任何关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于1980年11月6日)
编辑 刘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