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的武汉日记还在连载,最新一篇,她反击那些揣测她虚构身边死亡案例的人,她是如此写的:“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一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字字都触目惊心,带着地崩山裂的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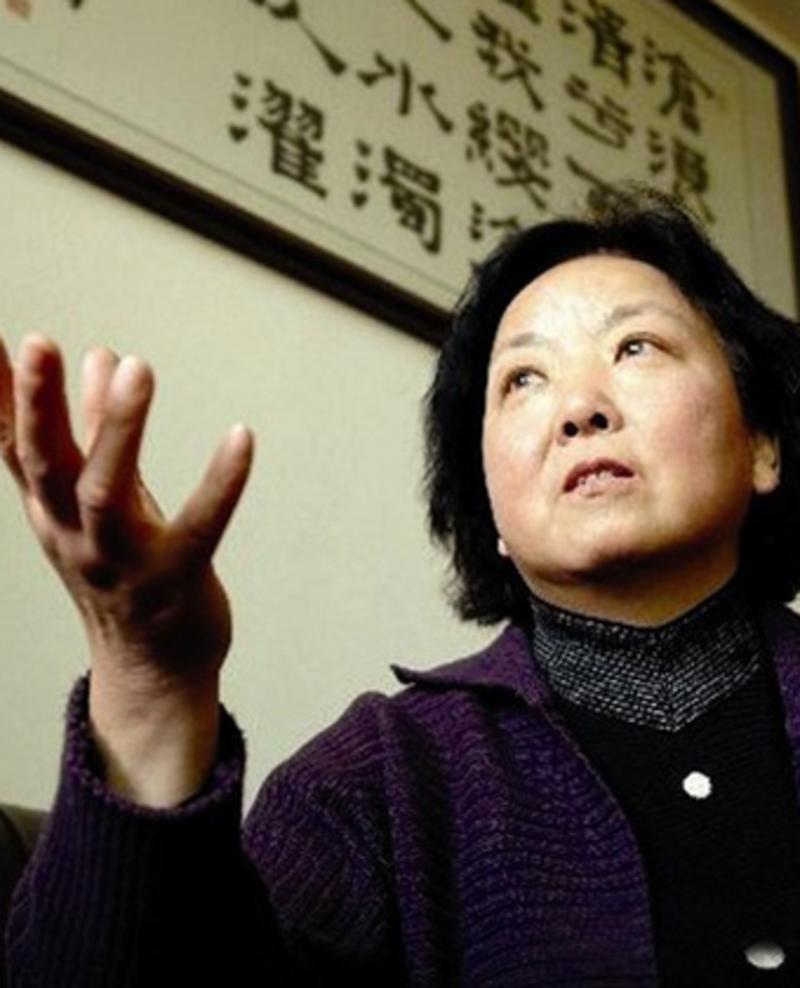
作家方方
但这样的文字带来的却是生的力量:是悲痛的,但闪耀着人性的怜悯;是愤怒的,但也是带着温度的;是书写黑暗的,但又像一盏灯照亮了人心。正如她自己所写:“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肝胆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文字惟有直面灾难的现实,“向死而生”,写下最真实哪怕是最黑暗的一面,才真正激发我们内在的生命活力。所以有人看过方方的记录,然后说,安心了。
我们该庆幸,我们还有愿意在这个山崩地裂的时刻敢写出这样文字的作家。这俨然已是稀缺品。我们不难理解,方方写下对某些文字工作者的批判:“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作家协会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我们正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瘟疫,可我们却害怕看不到这场瘟疫的真实面目,也害怕我们的记忆会慢慢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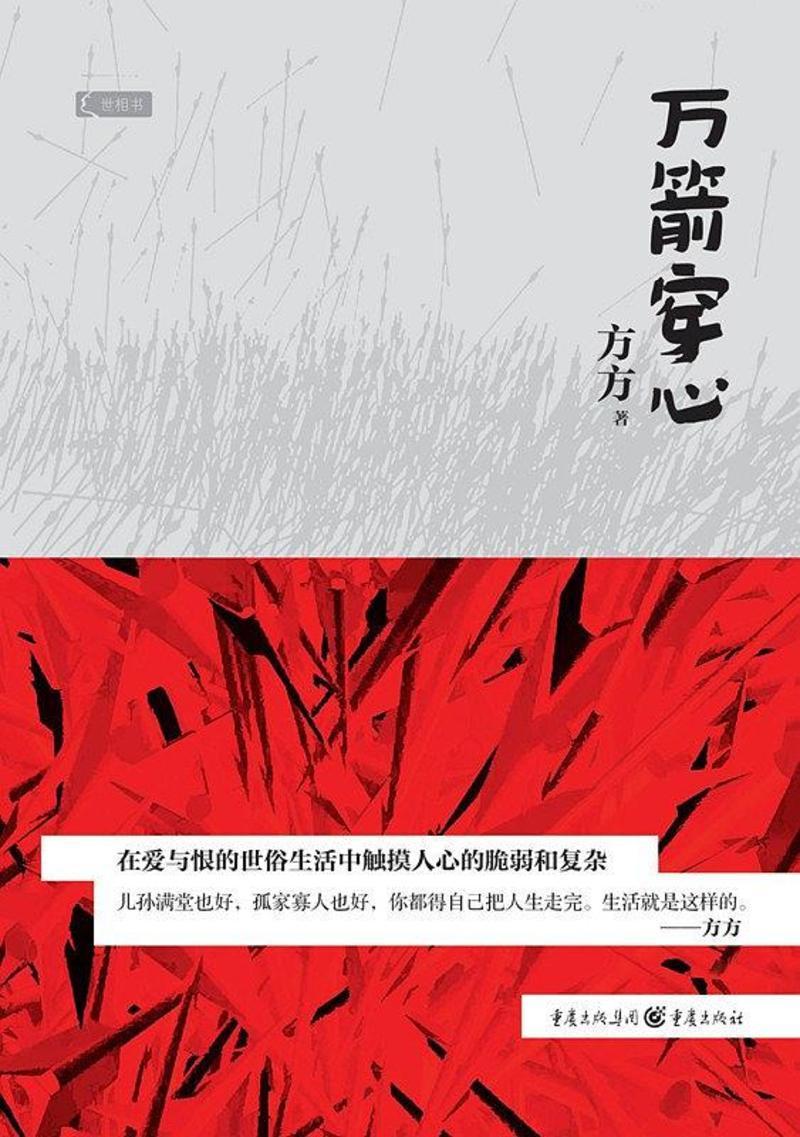
《万箭穿心》
方方 著
重庆出版社
2013年7月
毛姆曾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阅读有时候确实能让我们不管世事的纷扰,沉浸在一个被构建的文学世界里。但倘若只把作家都想象成坐守书斋的、脱离现实的人,则是一种误读。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太多啼笑皆非的文字与诗歌,太多口号式的、令人已经麻木的赞美与加油。如果我们把真正的作家视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视作人类最深刻的观察者之一,那此刻他们可以做的事情要比单纯喊口号要多得多。此刻,文字就是他们的武器,而沉默不是。
东北作家双雪涛在近日的撰文中说,在疫情当中最让他震动的是两件事:一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要遭此劫难?无数的普通人染病,绝望,死去,而大部分人成为客厅和卧室的囚徒。另外一些人高喊着口号,想要将此事引向一场胜利。它唤起了我内心的愤怒,很多时候,愤怒使人盲目,但是在一些时候,愤怒使人清醒,击碎假装沉思实际袖手旁观的外壳,思考文学本质上的活力和去向”;二是“所谓精英知识阶级的反应。更多的知识分子善于鼓励别人说真话,而自己从来不说。或者在等待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和更妥当的时机,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在这种语境中,发声的人反倒显得愚蠢”。
双雪涛最后说,作家应该要有“恨”——“作家恨一些东西,必然地,是因为他(她)爱一些东西。”

《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录1》
《巴黎评论》编辑部 著
黄昱宁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99读书人
2012年2月
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录》里,马尔克斯在接受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访谈时,被问到:“小说可以做新闻做不到的某些事情吗?”马尔克斯断绝否认:“根本不是。我认为没有什么区别。来源是一样的,素材是一样的,才智和语言是一样的。”接下来,马尔克斯阐释了记者与小说家身份的联系,他说在写完《枯枝败叶》之后,得出结论,“写那个村子和我的童年其实是一种逃避,逃避我不得不要面对的、要去写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现实。我有了那种虚假的印象,以为我正在把自己掩藏在这种乡愁的背后,而不是面对那正在发生的政治性的东西……可是当我写《恶时辰》《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新闻式的文学,我终于领悟到,关于童年的写作事实,比我所认为的更加富有政治性,与我的国家有着更多联系。”
一个作家不应该脱离真实,缺席见证,去生产无魂的材料。马尔克斯最后的总结是:“从真正的事实中去发现可能性,是记者和小说家的工作,也是先知的工作。我活得越久,过去的事情记得越多,我越会认为,文学和新闻是密切相关的。”
(晶报供稿)
编辑 曹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