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坚早期代表作《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完成于1990年2月)与布罗茨基写作《黑马》和史蒂文斯完成《观察乌鸦的十三种方式》一样,都通过“元诗”的方式在一个物象之上投注了诗人个体主体性的极为开阔、精深的观照。不同之处在于,《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几乎穷尽了一个诗人对“乌鸦”的所有常识、隐喻、语言、印象以及想象力。
从这一点上来说,于坚和布罗茨基在《黑马》一诗中做的是同一件事。《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也代表了此时于坚诗歌观念的调整与更新。这既与个人写作的转捩有关,也与当时整体性的时代精神境遇勾连。而早期的于坚,也不可避免和同时代诗人一样使用传统型的抒情性的隐喻和象征,比如1986年的那首《在漫长的旅途中》,那黑夜旅途中的灯光是“含情脉脉的眼睛”“黄的小星”,而灯光显然也是某种理想化的慰藉与精神呼应。而在《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中,于坚则显示了一个诗人综合处理事物的卓异能力。
多年后于坚解读了自己的这首前期代表作,“这是一场语言游戏,我与乌鸦这个词的游戏,它要扮演名词乌鸦,我则令它在动词中黔驴技穷。但是,这仅仅是语言学的游戏么,恐怕不是,这种游戏是富于魅力的,仿佛是为一只死于名词的乌鸦招魂。它复活了吗?我不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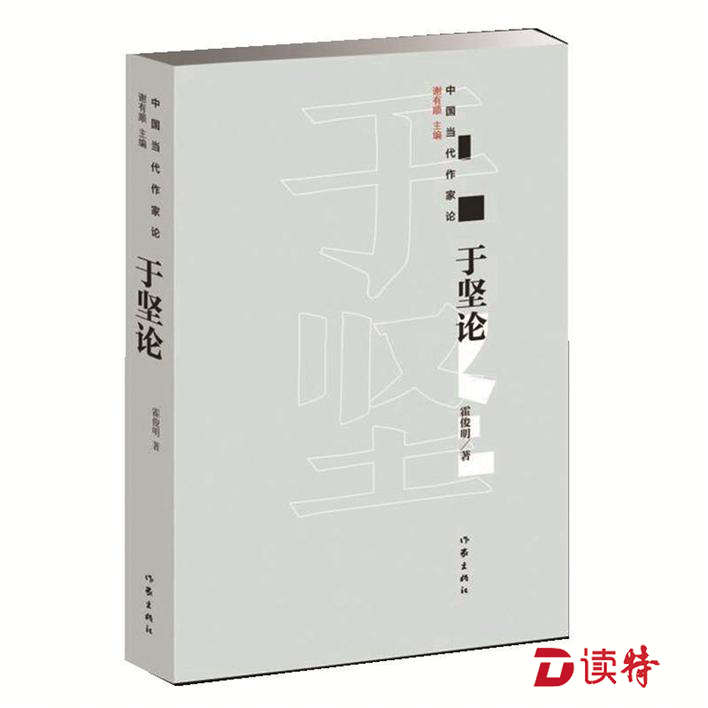
《于坚论》 霍俊明 著 作家出版社 2019年7月版
“词语的招魂”就是重新命名事物以及对词语的再度激活。这既与诗人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有关,与语言的求真能力有关,更与当时汉语诗歌场域中一个诗人精神主体性的庞大和智性的反思能力有关。汉语诗歌只有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开始了反思和检视期,尽管这一时期仍然伴随着大量的毫无意义的诗人之间的争吵和不团结的火气与怒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在那一时期具有一定的写作和精神的双重启示性的意义。诗人如何完成对事物和精神性现实的命名,如何在有效的语言方式中虚构出更深层的真实,如何在一个物象那里穷尽所有的想象力,这首诗都做出了示范。
“乌鸦”是词语叙述中的“乌鸦”,显然已经不同于纯身体构造的鸟类(“在往昔是一种鸟肉 一堆毛和肠子”),也与饥饿年代诗人所企图征服的鸟巢里的肉体的具体的鸟有别,而成为精神对位过程中与日常表层现实和惯性的语言构造所区别的精神征候和象征物,比如对“黑夜修女熬制的硫酸”“裹着绑腿的牧师”“是厄运当头的自我安慰”“对一片不祥阴影的逃脱”的语法的反讽。这样的带有“第一次”言说和命名的难度是巨大的,需要对常识和语言的惯性进行双重的去蔽。
这是一只“语言的乌鸦”,是经由词语说出的另一种事实,“从童年到今天 我的双手已长满语言的老茧/但作为诗人 我还没有说出过 一只乌鸦”。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语言的焦虑,这种焦虑显然不是于坚个人的,而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很多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已经定型和僵化,诗人的语言能力降到了冰点。为此,语言的焦虑一定会在特殊的情势下转换成为新的语言事实——对事物的重新命名能力的恢复。由此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将于坚的这首诗看作是一场八九十年代诗歌语言革命的一个并不轻松的诗歌语言学样本和案例。而这样一场语言的革命,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这种活计是看不见的比童年/用最大胆的手 伸进长满尖喙的黑穴 更难”。这实际上关乎以往整体性的象征、隐喻和神话原型系统。长满语言老茧的手要重新艰苦劳动,让那些老皮脱落,让那些新鲜的肉在阵痛中重新生长。于坚不是在与一只“乌鸦”作战,而是要与语言模式和思维方式作战。
乌鸦,成为诗歌代表的道德之恶与善之间的分界点。这种诗歌认识论的偏见显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吸附一切的黑箱,“乌鸦”正是那一只神秘难解的“黑箱”。诗人能否最终找到打开箱子的钥匙则未为可知,而打开黑暗的密钥只能靠那些真正具有创设性的诗人。就像乌鸦这只不祥的鸟一样,语言也是不祥的。据此,诗人就是那个对笼统天空的打洞者,他手里拿着语言的钻头。
(本文节选自《于坚论》,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辑 程思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