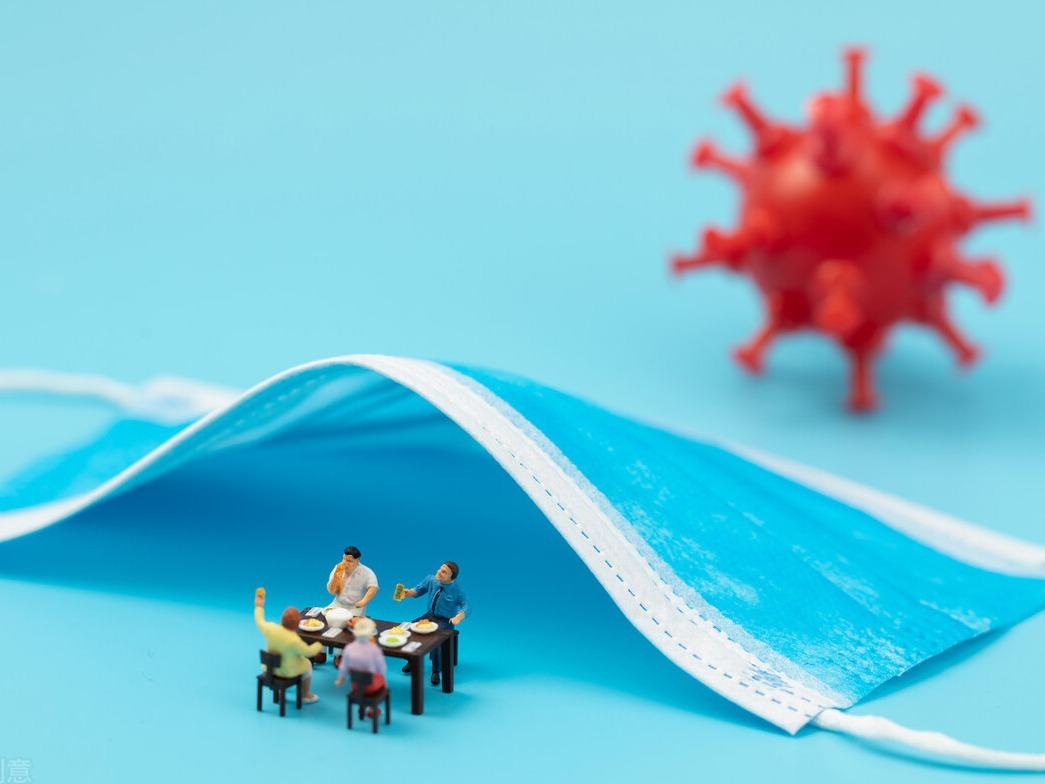洪天一和刘琪的生活每天如一:从龙华的城中村出发,在深圳北站进站口检查来往旅客的健康码。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护目镜,每天和上万人打交道,“不能放过一个红码”。
这是一项枯燥又需要耐心的工作,在这里,他们看到了世间百态,也重新认识了生活。
疫情以来,健康码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件,“见面互相展示健康码”被称为时下的问候方式。在所有公共场所里,人流密集的火车站对健康码的检查尤为重要。
春节即将到来,作为深圳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深圳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深圳北站的疫情防控愈发紧迫。数以万计的旅客在进出北站的时候,需要出示自己的健康码,显示绿色才会予以通行。为了更好地应对春运,深圳北站多招了两百多位检查健康码的工作人员。
洪天一和刘琪是站在深圳北站入口处检查来往人们防疫健康码的两位年轻人。
18岁的刘琪来自西安,他想通过检查健康码赚取下学期的学费。他的身体在略显宽大的执勤制服下显得有些消瘦,脸上的婴儿肥却尚未褪去,说话斯斯文文,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条缝,或许是因为北方寒冷,手上有很多细小的裂痕,说话时,一直搓着手。30岁的洪天一是一个中等身高,皮肤黝黑,性格爽朗,说话大声,身上有很浓烟草味的男人。经历过一次创业失败后,检查健康码的工作让他获得了“安全感”,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女朋友。
这是一项不容马虎又显得枯燥的工作,每个小时他们需要检查上千个健康码,红码进站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上级对他们的要求是:“不能放过一个红码”。有时,他们还要提醒那些匆忙的游人:“您好,请扫一下粤康码”,“请戴好口罩”。 老年人和残疾人是他们要重点关照的人群。据统计,全国共有2.54亿老年人,但有将近3/4的老年人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上网。 深圳北站东西广场上立着四顶显眼的红色帐篷,帐篷前的告示牌上写着:“温馨提醒/无健康码/老人机 手机没电/无微信 不会操作/无手机 等问题/由此通行”。这是无健康码人群的信息登记处,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只需要在这里登记他们的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上车点,下车点即可通行。

深圳北站无健康码服务点。图源边码故事
一些老年人听不懂普通话,很难沟通,他们就要求自己更耐心一些,一遍遍协助操作,或者找同事帮忙。 春运首日,刘琪和洪天一了解到,为更快捷解决因“无法出示健康码”阻碍出行的窘境,广州已经启用了刷身份证核验健康码的“健康防疫核验系统”。只需要将身份证放在识别设备上方2秒,屏幕上即可出现“粤康码”相关信息,显示绿码,旅客便可通行。 洪天一已在深圳闯荡14年,来深圳北站工作半年。刘琪刚来工作半个月。他们都认为,在很多人面临失业的疫情期间,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是幸运的。但同时,他们不知道明天过后会怎么样:这份工作并不需要过硬的技术,也没有可允诺的未来。
每天,刘琪和洪天一面对着背着大包小包、亟待归家的人群,然而,他们肩负着春运的重任,要在值班中度过除夕。来自广东潮汕的洪天一原本答应了妈妈过年会回家,现在也不得不滞留深圳。他已经想开了:“就算辞职回家可以个好年,那又怎样呢?回来还是要面对生活啊。”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每天穿九小时防护服,赚下学期学费
刘琪,18岁,来自陕西
我叫刘琪,在西安一所大学读大一。南下广东的动力来自于一位网友,他在贴吧里讲述了他在深圳的经历,勾起了我对深圳的向往:无论做什么工作,只要能在深圳就可以。 在求职app上经过几次投递后,我找到了现在这份检查健康码的工作。工资6000,包吃包住,虽然不多,但也够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非常满意。于是,我瞒着父母,背着行囊,踏上了南下的路。 春节前夕,深圳北站新招了两百多人,我们都被安排住在龙华区一个城中村里,我有室友,年纪都比我大很多。城中村的环境是可以想见的脏乱差,楼房极其破旧,楼与楼之间狭窄到只容一人通过,我甚至可以听见对面楼两夫妻的吵架声,还可以闻见炒菜油烟呛鼻的味道。一日三餐倒很不错,每顿四个菜,主食是米饭,馒头,面条还有红薯。上下班有专车接送,通勤时间大约二十来分钟。 上班时间是早上六点,每天不到五点,我们就得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二十分钟后,大家准时出现在餐厅,吃完饭,一起踏上接驳巴士。来到深圳北站西广场,已经能看到许多人在车站门口排起了长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好防护服,戴上防护手套,摆好铁栅栏,然后就开始一个个检查旅客的防疫健康码。
越是临近春节,起床的时间变得越早,最近两天,5点15分就要开始集合上车。要是起床晚了,没赶上接驳巴士,就得踩半个小时的单车去北站,遇上这样的时候,就特别累。 我做这个工作有半个月了,工作不难,要求却不低。“不能放过一个红码”,班长的话时时刻刻都在耳边响起,我不敢怠慢,眼睛像磁铁一样,“吸”在每一位乘客的手机上,生怕错过一个红码。当检查出红码时,我们要把旅客带到专门准备的红色隔离帐篷,并为他们讲述后面的一切操作和退换票事宜。
我把这些流程都谨记在心,紧张地等待第一个红码出现。随着春运开始,我开始每天检测到红码,这些流程都派上了用场。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科学,最近站里还进行了疫情防控素质考核,内容与我们的日常工作相关。 休息间隙,我抬头望望广场,熙熙攘攘,都是准备归家的人群。有的全家出动,背着大包小包,有的形单影只,看起来像是都市打工人。赶路的中年人似乎都皱着眉头,拿着手机,一脸彷徨和疑惑,年轻人倒是都很淡定,和同伴有说有笑,讨论来时的出租车价格为什么没有想象中高。

深圳北站等待进站的人群。图源边码故事
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可以观察到很多人,提高我的思维和认知。我也喜欢外面的生活,究其原因,也许和我家庭环境的贫乏有关。 我出生在西安农村,父亲在家务农,母亲五年前就不知去向,家里还有一个在读职高的弟弟和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几年间,母亲未曾回来过,也没有打过一个电话。父亲脾气多变,时而温柔宽容,时而暴躁易怒。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极度缺乏安全感。即使就在省城上学,我也半年才回家一次,一个月就和父亲通一两次电话。 十六岁起,我开始在外面打工,强迫自己把对家的依赖转换成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两年里,每个假期打工赚的钱,我都用来负担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我的花销不多,一周只用100块。平时的娱乐就是看看电影,或者在村外的公路上骑车——只要骑上车,我的心情就舒畅多了。 在学校里,我学习一般,性格孤僻,总是喜欢自己一个人。校园生活就像温水煮青蛙,我渐渐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每当面对第二天的考试和满满的课程,我总是很焦虑和厌倦,常常会想:学啥垃圾,我不想学了。但其实心底里我知道,学习是我改变命运一次重要的机会。 今天我已经断断续续站了九个小时,到了下午三点换岗时间,终于可以“解放”了。我小跑到车站门口的工作棚,迅速脱下防护服和防护眼镜,这时候正好碰到了同事。他给我递了一瓶水:“小刘啊,很热吧?”我摘下N95口罩换上普通口罩,大口喘着粗气说:“没关系,再热我也能站得住”。 这真的是我的内心想法。再辛苦,我也能扛住。工作辛苦,就会知道要好好学习了。 工作了十几天,对工作也熟悉了,班长已经开始让我带新人。新闻里都在播放过年的防疫安排,网上都在热热闹闹讨论过年怎么回家,而我,是注定回不了家了。接到领导通知,要求全体留深过年,照常值班。简单一句话,许多人心理最后的防线崩塌。而我不想爸爸,也不想妈妈,仿佛其他人的失落和感伤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留深,就留深吧。 我喜欢深圳。不知道未来,我将以怎样的身份回到深圳?在我的想象里,我会在深圳做金融,成为一位体面的白领。正这么想着的时候,车要开了,夕阳下,我小跑回到队伍中。我的深圳梦,就从这里开始吧。
创业失败,因检查健康码找到了女朋友
洪天一,30岁,潮汕人
我是洪天一,16岁初中毕业后就来到深圳闯荡了。我今年30岁,和刘琪一样,我在深圳北站做检查健康码的工作,每天工作9个小时。 这种打工的生活是两年前的我不能想象的。刚来深圳时,我在华强北修手机,因为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创了业,赚了钱,在老家买了房和车。那是我最风光的日子,那时候想到打工,只觉得这是没出息的人做的事。
可是后来我生意失败,赚的钱又全都亏了进去。我非常低沉,花了足足两年才把心态调整过来。这时,疫情爆发了。抱着只想在疫情期间找一份工作的想法,我偶然看见派出所勤岗张贴的招聘信息。面试通过后,我开始从事防疫工作。

健康码检查人员的工作状态。图源边码故事
半年前,我被调来深圳北站。每天早上五点,我抓起两个水煮蛋往外冲,小跑着赶上公司接送的班车。经过30分钟车程,5:40到了深圳北站,正是冬天,天又黑又冷。我坐下来把两个水煮蛋吃完,再泡个咖啡带去岗位上。吃完早餐,我穿戴好发的防护服跟N95口罩,站在岗位前给队员们布岗,安排队员们把栅栏摆好,再将负责内围、外围、查岗的队员吩咐下去。队员们很听话,不需要过多地操心他们的工作。交代完,站岗的一天就正式开始了。 我们组在深圳北站东广场的正中间站岗,旁边有一个红色的帐篷。红色帐篷是个专门服务没有健康码人群的定点,遇到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我们会将他们一律带来这里,登记身份信息、电话号码、上车点、下车点。过程难免是繁琐的,譬如很多老人不理解,会一直嘟嘟囔囔的,但我也只能“受着”。 “请问西广场在哪里”,“请问检票口在哪里”,“请问扫哪里”, 每天我都要在嘈杂的环境里回答数不尽的问题。与此同时,我还要机械式地重复着一样的话,睁开眼是“您好,请扫一下粤康码”,闭上眼是“请戴好口罩”。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已经慢慢亮了起来。 这是一份简单枯燥的工作,但也不能因此松懈:深圳北站是不允许红码进站的。做了这么久,看见红码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每次心里难免还是会咯噔一下。通常的一种情况是,旅客在疫情高风险地区隔离了14天,但健康码没有及时更新,才显示红色。我只需要跟同事交代一下情况,然后与旅客一起在旁边等同事过来。很多旅客都会担心是否能赶得上高铁,我会安慰他们:如果尽量快点配合隔离点那边的工作,还可以赶得上车。 中午一点,有同事拍拍我的肩,这是我们之间的“午饭信号”——终于轮到我吃饭了。红色帐篷后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子,还有一些红色的塑料椅子,我在这里坐下,开始吃公司派发的盒饭,四个菜,两荤两素,还不错。这两天人流量剧增,嗓子消耗太大,到下午嗓子已经哑得差不多,这时就该拿出“大声公”(扩音器),继续重复着一样的话,“请扫粤康码!”。
下午三点是换班的时候。我脱下防护服,站好队形,队长会对一整天的工作进行总结反思。今天下午的太阳很大,我穿了一天的防护服,只在广场站了十分钟,我就感受得到汗水顺着两颊流下来,只想快点上车回宿舍。 在车上,世界终于安静了下来,看着深圳的一条条街巷从眼前划过,我想到16岁的自己从这里出发,经历过身无分文到有车有房再到身无分文,到现在打工的日子。深圳可以说是个见证我成长的城市,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我还是很爱它。
去年2月,我在村里检查村民的通行证。就在检查通行证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女朋友。疫情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很残忍,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幸运。今年要是没有疫情的话,我应该马上要和她结婚了。这个经历常常让我想到这句话:人生就跟赌博似的,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会在哪里,也不知道会遇见谁。 除了找到了女朋友,我还可以用这份工资买我喜欢的东西——虽然这点钱连老家的首付都给不起——可跟身边的朋友们对比一下,我还是幸运的。也可能是从前大起大落的经历,让我更珍惜现在安稳的生活。 今年过年,我应该是留在深圳了。我本来答应了妈妈今年过年会回家,但就算辞职回家可以个好年,那又怎样呢?回来还是要面对生活啊。还是年后再请假回家一趟吧。车上特别容易感到困,即使车程很短,我都会小睡一会。迷迷糊糊中,我好像梦见了女朋友,希望她明年可以搬到深圳来。
编辑 关越 审读 刘春生 审核 李怡天 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