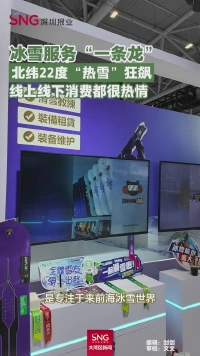2025年8月,南山区再次登顶两份分量不轻的榜单。一份是工信部下属赛迪顾问的“创新百强区”,南山已连续9年居首;另一份是赛迪“中国活力街道500强”,南山8个街道全部上榜,头部街道粤海位列全国第一,前100强中南山占7席。
南山再夺赛迪双榜,是由“量”及“势”的同向抬升。
十年纵览,南山增长轨迹清晰有力:2014—2024年,南山区GDP由近3500亿元增至超9500亿元,十年新增超6000亿元、为2014年的2.74倍,10年间跨越了六个千亿级台阶,已然逼近万亿城区。
同期,南山的区位能级与带动效应同步抬升——辖区GDP占全市比重由21.65%提高到25.82%,对全市当年GDP新增量的年均贡献约29%。近五年,南山对全市的增量贡献多次突破四成。
“抬升”具有内在逻辑。多家科创企业负责人在不同场合告诉笔者,与几个技术场域里的关键进展几乎是同时发生。只是,外界往往只看到科技进展的碎片信息,却忽视了背后的空间逻辑:知识是如何流动的?企业如何彼此作用?政策、资本与场景,又如何在一个区域中自洽共生?

初晨的南山。(南山区委宣传部供图)
【一】
一种“抬脚可达”的协作密度
答案,首先藏在“密度”里。
近十年,南山的单位面积产出由18.7亿元/平方公里增长至51.3亿元,研发投入强度升至7.66%,是全国平均的3倍。如大众所熟知的粤海街道,以深圳不到0.6%的土地,贡献了全市约11%的GDP,集聚了全市8%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在粤海,这里的工作半径很短:楼宇密、公司密,人走几步就能对上话。同一家咖啡店里,关于芯片、算法与物流的话题常在同一桌出现。
粤海街道一家市场占有率逾三成的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负责人告诉笔者:南山“如此高的人才与知识密度,在全世界都是十分罕见的”,这是他们创业成果得以持续涌现的根本因素。
当然,并非所有集聚都会起火花。在粤海、在南山,空间里的相遇更像“反应”而不是“叠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当年关于产业集聚外部性的三重作用——配套共享、劳动力池、知识溢出——在这里变成了可被验证的日常。
在粤海,“协作快”是可被度量的:同楼送检成了硬件团队的日常,工程师拉着样机过街就能进暗室,当天拿到整改建议,算法、固件与整机团队在同一街区可以完成评审—打样—送检的闭环。
“隔壁楼的算法”明天就能嵌进“这边楼的硬件”不是传说。“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到OPPO公司去,OPPO也全程参与模组的重新设计。”现已成为“3D视觉第一股”的奥比中光,在创业初期入驻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完成了从园区样机到消费电子的大规模导入验证。
从“有想法”到“有样机”的时间被压到一两周级别,形成粤海式的“短链路”迭代。叠加南山拥有全市最多的上市公司这一资本与治理优势,人才、资金与上下游协同被压缩在半小时生活圈。粤海街道提供的数据显示:街道内拥有103家上市公司(占南山区近一半)、10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家“独角兽”企业,以及209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因此,清华系硬科技独角兽企业中,约30%在深圳,其中大部分在南山,这样的数据并不意外。
当然,南山不止有粤海。西丽街道(此次位居街道500强第11名)已经形成构建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招商与蛇口街道依托港口和自贸片区,支撑对外开放与现代服务业发展;南头承载历史城区与基层治理,桃源和沙河则分别联动科教城与超级总部基地。这些街道如不同生态位的“细胞”,协同构成南山的加速器。

霞光中的南山区 (南山区委宣传部供图)
【二】
涌现时刻:“从0到1”→“从1到N”
城市思想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说,城市的活力与增长,来自密度之中的多样连接与由此产生的知识溢出。位于南山区北部、近来“出圈”的“机器人谷”,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一条以密集科研供给、快速验证通路与初创集群为特征的产业链,正在这里逐步显形。
谈起具身机器人,我们可以先看一项似乎毫无相关的制度:2015年制定的《南方科技大学章程》,其第二十四条规定,全职教师可每周一天在校外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2019年,曾任职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张巍全职加入南方科技大学,主攻机器人“仿真到现实”。后来,张巍创办逐际动力,专注人形机器人。去年,逐际动力推出6.98万元的双足平台,显著降低科研与行业测试门槛;今年,逐际动力的人形机器在零售、物流场景试点规模化落地。
逐际动力只不过是“机器人谷”的一个例子。这几年,南山区机器人产业迅猛发展。最新数据显示,全区已集聚机器人全产业链企业200余家,2024年产值超4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14家为上市公司,30余家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为什么是发生在南山?创业者们看到了什么?
时间回到2019年1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器人系统实验室完成一项被普遍视为具身智能拐点的研究:将仿真中通过深度强化学习获得的策略零微调迁移到真实四足机器人,实现场景行走与跌倒恢复。随后两三年间,围绕盲行越障、感知与本体融合、并行仿真训练、通用双足平台设计等方向,相继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些变化直接推动了南山本地创业热潮的涌现。”桥介数物正是其中代表。这家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初创企业,目前已为超过40家机器人整机厂商提供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其创始人尚阳星,正是张巍的学生。
“以前是基于建模(model-based),现在是基于学习(learning-based)。”尚阳星说,新一代方法通过深度强化学习,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习得动作策略并迁移至真实场景,这带来的是超乎想象的进步。在“看到了什么”之后,尚阳星果敢选择休学,在一无所有时白手起家创业。
也就是说,这条如今产值约400亿元的产业链,在2019年之前仍处于“0—1”的探索期。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突破出现,火花在南山被制度与场景承接,迅速完成从“0—1”到“1—N”的过渡,最终落地为产业链与产值。
笔者了解到,当前,南山区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一方向,依托南科大、深大、先进院等高校科研平台和广东省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完善基础研究链条,通过西丽湖和多家概念验证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配套设立多支科技金融基金并集聚戴建生、孟庆虎等院士和一批企业家与技术团队,形成从前沿攻关到落地孵化的全链条创新生态。

滨海大道南山全景 (南山区委宣传部供图)
【三】
无界生长:当算力、平台与场景在南山形成闭环
“无界之城”——这是近年南山区反复提及的话语,多次出现在形象标识体系发布会等公开场合。从科教融合到产城协同,从人工智能产业到企业服务生态,南山意在打破物理边界,更是要素流动的重组、平台能力的共享、制度与场景之间低摩擦协作的可能。
有科创企业人士告诉笔者,这种“无界”理念并非抽象口号,而是对全新技术周期的现实回应。
过去十年,支撑产业演进的技术底座正在发生跃迁。尤其是大模型的兴起,已不再是某一技术领域的边角革命,而是成为重构各行业产品形态与生产方式的通用技术。这也正在倒逼城市重构自身的要素结构与承接能力。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接得住这样的技术底座。
谈起这几年席卷全球的“大模型”浪潮,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它始于ChatGPT的横空出世。但真正的起点,其实要追溯到2017年。
那一年,谷歌团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交了一篇不起眼的论文,题目是《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它提出了一种名为“Transformer”的新架构,摒弃传统学习模型,把“注意力机制”推到了核心。论文既没拿奖,也不是大会主讲,只是在角落里贴了张海报。
但就像很多伟大的变革开始时那样,这颗“无人注意的种子”后来改变了一切。如果没后今天风靡的各类大模型,这项技术很可能在学术圈里默默无闻地消散。
但技术的命运并不只由论文决定。
决定其是否真正落地生根的,还有谁能为它搭建接收的结构——谁有算力、谁有数据、谁有容错的制度设计、谁能提供高频试错的产业场景。
南山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闭环。
早在2018—2019年期间,南山对“语言智能”的关注与应用已现端倪:2018年,港中大(深圳)—腾讯AI Lab机器智能联合实验室揭牌,自然语言处理进入产学研主线。翌年,腾讯团队将Transformer转化为工程底座,在WMT等国际基准上取得领先成绩,并稳定输送大模型技术与人才。
例如成一鹏,这位前腾讯AI员工,早早就意识到“粗放式算力的不可持续性”,很快辞职在南山创立新旦智能,成为深圳本土大模型公司的代表,并凭借“小而精”的技术路线在国际崭露头角。
这个变化,在南山也产生了实质影响:原本专注传统AI视觉算法的团队重写了架构;新创企业将Transformer架构下的推理优势应用于视频分析和空间识别;原本做消费级产品的公司转向To B市场,聚焦工业场景识别,叠加政策扶持后加速商业化。
2023年,南山区印发《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创新应用实施方案》,将“场景”作为牵引,明确要“抢抓大模型时代的历史机遇”。很快,“模力营”垂直生态社区在南山揭牌,这是大湾区首个专注大模型的孵化器,围绕算力、数据、合规、开源、硬件、融资、场景搭建七大公共平台。
算力基础亦同步跃升。截至2024年,南山区已建、在建人工智能算力规模达7300PFlops,辖区能耗许可支撑算力超6万PFlops,位居全市前列。同时,南山区正积极与克拉玛依寻求算力产业合作,探索“算力飞地”试点。
体量与结构也在重排。
2024年,南山区人工智能产业增加值达449.07亿元,占全市超六成;规上企业1351家。算法方面,深度合成算法备案342项、大模型17项,分别占全市七成和六成。深圳三个省级AI产业园均落在南山,涵盖从芯片、模型到场景的完整生态链。
这449亿元只是“可见”的直接产值,更大的重构正发生在行业深处——港口引入AI+数字孪生,妈湾作业效率提升近50%;内容设计赛道上,兔展与生境将视觉大模型与AIGC嵌入生产;自动驾驶道路开放里程达169.56公里,占全市10.8%,累计订单突破50万……
如果说近年“技术变革”更多发生在代码行之间,南山此后的故事,则是一段城区拥抱技术变迁的范本:有制度,才有转化机制;有平台,才有要素保障;有头部与新锐的“雁阵”组合,才有场景打磨与供给牵引,一条完整路径因此在几公里半径内闭环。

金色大湾区(南山区委宣传部供图)
【四】
制度与治理为抓手,把“可行”变“可复用”
1990年1月4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南头管理区与蛇口管理局合并设区,由此正式成立南山区。从一个偏僻小镇到今日的创新高地,南山走出了一条极具代表性的“制度变迁与产业跃迁”路径。
统计数据非常直观:从建区时GDP约78亿元,到2024年南山区地区生产总值超9500亿元,增长近122倍,年均增长超过13%,人均GDP也从4万元提升到约51.9万元,不仅进入国家高收入标准,更在全球排名前列。
从制度层面看,这座区域诞生时就继承了蛇口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基因——曾诞生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并在“管理、分配、用人、住房”领域率先探索出一套实践路径。
立足改革基因,南山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转化效率:围绕西丽湖国际科教城,把教育、科技、人才纳入同一制度图纸,构建“根系共生、养分循环、适地生长”的生态;以“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闭环为抓手,常态化运行“X9高校院所联盟+X-Day路演”,把政策、服务、基金与需求集中对接。
在源头侧,建立概念验证平台,形成“验证—中试—转化”接力机制,已面向全球征集、储备、跟进项目300余项;“一校一策”直达科研与人才培育一线,鹏城实验室发起“鹏城愿景基金”(10亿元)支持大装置与攻关平台,深职大、深圳科创学院共建未来技术学院,零一学院探索拔尖创新人才选育,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打造粤港澳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成果转化南山基地。
政策工具成体系发力。今年3月出台《支持创新创业“六个一”行动方案》,与“揭榜挂帅”“千亿计划”配套,聚焦机器人、AI等关键环节的“中段阻力”,在科研链、转化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等维度明确责任与支持路径,打通原始创新到产业落地的通道。
治理延伸至民生与基层。以“六新行动”(“百校焕新”“社康新韵”“文体新境”“绿美新城”“宜居新品”“党群新貌”)为经常性抓手,以“扎根行动”推进干部下沉、清单化治理,让制度供给转化为“日常可感”。
归结起来,南山以制度与治理为抓手,把“单点可行”做成“整链可用”,最终沉淀为可复制、可复用的操作路径。
南山的下一程,要把区域蓝图深度融入国家战略,全面建设全球一流现代化创新城区。8月23日-24日,南山召开“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务虚会,明确要以国际视野深化改革开放,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无界之城”,建设新质生产力示范高地,持续提升城区品质,以先行示范标准打造“民生七优”幸福标杆。
事非经过不知难。站在深圳特区建立45周年路口回望,这座城区的加速更是无数人的日常累积。正如《好风起》这首由南山区出品、周深演唱的原创歌曲所唱——“我信人啊,一关关地过不简单”,“没有比向前更美的姿态”。
编辑 李斌 审读 白珊珊 二审 王雯 三审 上官文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