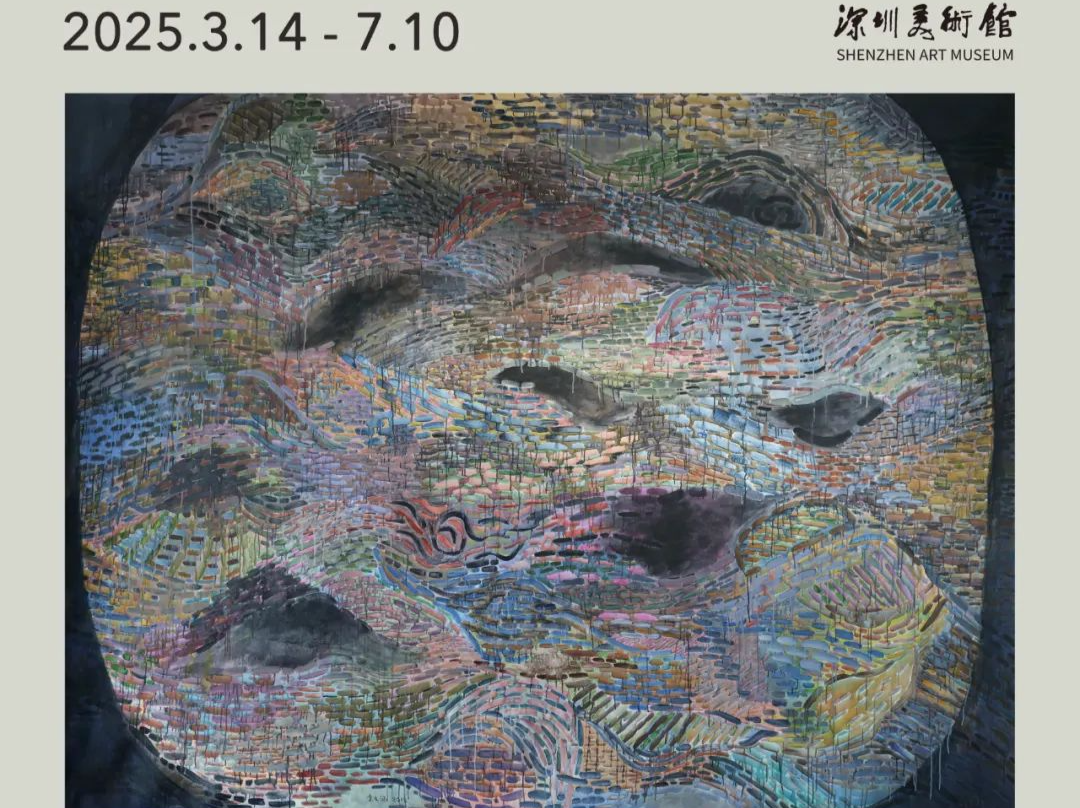王艺洁
人需要有几个朋友,不需多,真的几个就足够了。我指的是,可以在一起聊聊风花雪月诗酒茶的那种朋友,那种句句不谈情,但句句总关情的朋友,当你从一场聚会中抽身,该握的手早已握过一轮又一轮,想说的话却只能一句又一句咽下时,你想要即刻见到的那种朋友。
若谈风,你们既可以说李峤的“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也可以聊东坡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谁说风无形呢?明明所过之处皆有形,以飘荡,以摇曳,以翻卷,以摧折,留下笔触,抹去行踪。人口中的风,还要更加复杂无定,一丝浓稠往往夹杂于万千凛冽,谁又能洞悉所有不消说不堪言的隐衷?该是很久之后才能领悟,千帆阅尽之所得不在于观潮逐浪,而是听风者不必捕风。
若论花,可清丽,可绚烂,可隐逸,可颓靡。花事如人事,哪一朵兴衰不是掷地有声?哪一枝往复不够佐酒三杯?犹记那句“人道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遇春”,却依然不知际遇与规律,哪个更堪敬畏。宿命中若没有无常被歌颂或嘲弄,还能称得上是“宿命”吗?有道是“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恐怕越是漂泊无定,越懂凄与美本就相随。莫不如,敞开来做一朵难养的花,身在人海,心向远山,只懂得少许孤芳自赏的尺度。
若讲雪,有孤舟蓑笠,独钓寒江的水墨留白,也有暖阁红炉,笑分芋栗的人间烟火。空茫茫的冷寂,或扑簌簌的热闹,都很妙,妙在动静之间,盈虚相映。曾有片刻,立于雪怀,看夕阳缓慢沉没,望灯火渐次浮跃,瞬即懂得了“天高地迥,宇宙无穷,兴尽悲来”是怎样一种况味。人,终究不宜太冷,太清,太警醒,有心去偷半日闲,做白日梦,便是乐事,无谓计较真不真切。
若说月,便想到江畔张若虚此去经年,黄昏欧阳修泪湿春衫。从诗词歌赋到航天计划,月是永恒话题。1969年,阿波罗11号已经登上月球,而这个七月的某夜,露台边一棵晚熟的枇杷是如此迫近的一种抽象,仿佛只是无数绿色与黄色光影的堆叠,也香,也甜,但不真实。在它之上,遥遥的,是一弯不为你知的月亮,那么孤单,那么美丽,一如很多个千年之前的模样。今晚,我说它不为你所知,是因为,你并未与我一同抬头看。
若读诗,或许从周梦蝶的冷粥,破砚,晴窗开始,至辛波斯卡,橡树,针线结束。你知道,他选择紫色,而她偏爱绿色。他选择早睡早起,而她偏爱及早离去。他选择迅雷不及掩耳,而她偏爱有些保留。他们似乎拥有某种相近的智慧,跨越时空的灵光不必懂得地理,识清边界。反正写诗与不写诗都可能一样荒谬,又何必追问“还要多久”或“什么时候”?
若评酒,未及举杯,便想起那句“把你的影子加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能在文字间游刃有余的人,何尝不是另一种千杯不醉?总有夜色静默如你,新的谜语映在杯底,聪明人早已学会不问,而傻瓜不懂机巧,一口饮尽。微醺,尽兴,泥醉,或许从来都不是递进关系,人太执迷于未雨绸缪,反而更容易一塌糊涂。
若品茶,便珍视那点炭煮水的郑重,那投茶烹茗的斟酌,那注定难再现的“一期一会”。飞光如电,却将人文火煎熬,纵有钢筋铁骨,也难敌分分秒秒消磨。若有人愿共你安安静静饮几盏茶,令你舌间心田渐渐熨帖,便是极应珍重的缘分,千秋万岁,也尽可化作庭前半杯。
人,确实需要有几个可以一起聊聊风花雪月诗酒茶的朋友。至于找不找得到,则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