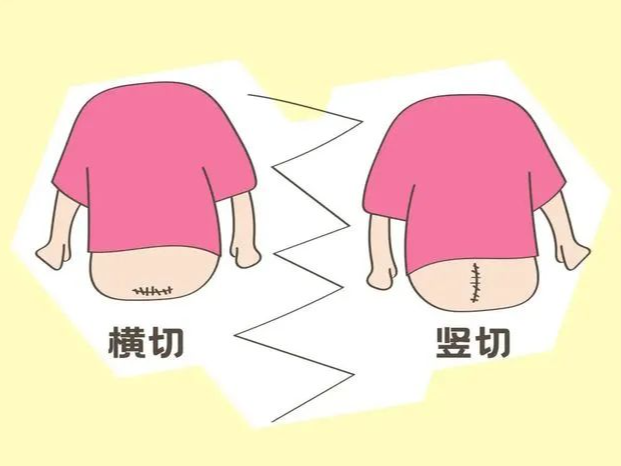雨势渐歇,栈桥尽头的导航灯忽明忽暗。海潮冲击在防波堤上,一阵阵低沉的拍打声惊醒了蛰伏的夜。远处杨梅坑的轮廓隐在雾中,鹿嘴山庄的悬崖如同宣纸上晕开的墨迹。一艘夜航船正犁开墨色海面,航迹灯指向雾气氤氲的远方。
今夜不再纠结于“既往”与“余生”的辩证,且枕着海浪声重读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倘若我呼喊,谁在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
晨起推窗,料峭春寒扑面。

六点三刻的潮位线正在退却,海面上蜿蜒的波浪纹路像某种未完成的草稿。浪骑游艇会的彩色桅杆在雨雾中没有了鲜亮,七娘山脉化作宣纸背面的水印,海天被浸染成铅灰色,潮声裹着雨雾润湿着窗棂。
我独坐案前整理课件,想起那些会场模棱两可的术语从唇齿间流出,纵使荒诞,自己亦是台下揣摩语气的聆听者。
这是倒春寒最后一场雨了吧?水杯沿腾起的热气里,我望见四十年前那个在吉兆海滩踩着自行车的青年——他的猎装口袋总别着两支钢笔,一支批阅学生作业,一支誊抄聂鲁达的诗。想起了洶洲岛海滩,某位同学在海边放声唱吟:“大海不会回答,但它允许所有答案存在”。
那时,灰色的天与海相接,而今雨还是那样下着,打湿的却是另一片海域的天空。
沿着游艇防波堤步道徐行。
七娘山的轮廓在雨雾中浮动,鹿嘴山庄的悬崖如同被洇湿的碑拓。一只白鹭突然从桅杆惊起,翅尖掠过水面刹那,竟与记忆重叠:那年春汛,我伫立窗前,看暴雨冲刷紫荆花,玻璃上的水痕像极了此刻海天之间的经纬线。
防波石正与海浪角力,交汇处泛起细碎的白沫,仿若被揉碎成纸团投向废篓的汇报材料。忽然想起整理书房时,从文稿合订本里抖落的一枚银杏书签,叶脉间还残留着之前随手写下的句子:“在书页的褶皱里豢养蝴蝶”。
行至杨梅坑村口,大排档老板正在拆卸防雨棚,塑料布抖落的积水打湿了写有“今日特价”的小黑板。我要了碗海胆粥,看老板娘将晨捕的海胆剖成金色的葵花。看着沸腾的砂锅粥,往事如烟雾般升腾,竟吟起清代丁元英的《卜算子·自嘲》。
雨丝突然绵密起来。咸腥的海风徐徐吹来,恍惚看见自己站在人生码头上——左边是泊满游艇的港湾,右边是尚未启封的帆船。某个瞬间突然读懂了自己的怅惘——如同海蚀崖上的石英岩,既渴望海浪雕琢出新的形状,又恐惧被冲刷成陌生的模样。七娘山的巨大投影已然消去,锚链也已拆解,那些未竟的抱负与遗憾,终究要化作重新启航的压舱石。
潮声渐隐,春雨留下的盐渍正在风干,黄昏的悬崖栈道是部未完成的自传。
潮水在礁石上书写年轮,在背阴处,成片的鹅颈藤壶——这些用石灰质外壳将自己焊死在礁石上的生物,竟会在涨潮时伸出羽状触手捕食。此刻却更愿相信惠特曼的诗:“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归程车过隧道,七娘山最后一缕云雾恰好消散在后视镜里。挡风玻璃上的雨痕正在蒸发,像极了自己正在淡去的人生印记。而前方,大鹏湾的海平线正被夕阳镀成鎏金。
编辑 刘兰若 审读 伊诺 二审 刁瑜文 三审 张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