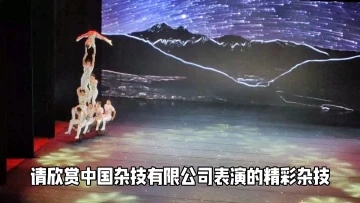《论诚信——执诚之手,以振中华》
作者:黄怡茹
学校(单位):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高中部
指导教师:胡旖航
君子曰:“国之信,重九鼎;人之信,诺千金。”诚者,即内诚于己,实求为;信者,外信于人,一诺千金。信之于己,坦之而无悔;信之于人,言必有果也;诚信之于国,心向往之。夫若失之信者,则为镜中,水中花去,坐而烟云,将散。故丘辈,当执诚之手,以振中华。
其一,信者,立人之本也。阅古者,句以信立警策入视帘:文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戒我以践行许诺之重;文曰:“小信成则大信立。”戒我以守信之重。自古以来,雅士皆能识诚信之重。秦末汉楚人季布以侠为名,重守诺,事必果,未尝失信。其正所谓 “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古人云:“处己、事上、临下,皆当如诚。”因斯说,吾可知矣:人无信,则无以取信,亦无以大事。东汉末,“三英战吕布”,可谓一段千古之佳语。布杀丁原而叛卓,见利忘义,无诚不信,卒死于操下。今食安辑相继,使民心口难慰,亦令之难问:人性之本何在?对诸利诱,或择失其信囊,或择诚信以守其良知之天。故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所以对人者,必以诚心为生之至要德之一,用之为人生之本,言有信,待人亦有信。
其二,信者,为政之基也。为政当取信于民,若民之信君,则将守封疆,听君命;智谋之士将自为君谋,而功是求太平;反心者不见,安君之治也,即如王安石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斤轻。”;反是若不信其上,则失足之鸟,浮而不定,终而民弃之,国无久安,犹古人所谓言:“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凡百元首,承天景命,皆守信成功。齐桓公为五伯一,九合诸侯,可谓天子皆取亡之计,鲁庄公与战,曹子为将,三战不胜,鲁庄公不得不割地,桓公许与鲁将兵。在盟之上,曹沫穿匕首抵齐侯,还鲁以败许地,桓公许之。其后,齐桓公无以曹沫非其地而背约也,真割鲁地而归鲁,其实以桓公之力,曹沫以此鄙取之地,足以无与也,鲁无以与也,而桓公信之,约与地,桓公能为五伯之冠,非偶也。由此观之,上无信不仰,政无信不威,国无信不立。
揆诸当下,殷鉴在前。使历代之亡者,以其不信也,非以天下之人也,嗟乎,若历代之君皆能守节,则民服之,国家至万世而为君,谁能灭之?此国家尚不暇自哀,但使后人而哀后人,后人而不鉴之,亦使后世而复哀后人也。故今吾必信,守于己,诺于人,践于行;国传其美,成其信,使信落地生松,天地之性也,而助国之强也,终执诚信之手,以振我泱泱中华。
总括而言,信之于人、政,皆一不可缺之美也。人不信,则文理乱,然后乎无穷。正如 《吕氏春秋·贵信》之篇,君臣无信,则民谤讪朝廷,国有无安:仕宦无信,则无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无信,则民易犯法,难施尤教:交友无信,则相亲结不亲,百工无信,则手工粗粝,以次长,丹漆好色不正。失信之害何大也!
吾将长,深知其重,乃作此文以彰吾志。
编辑 李斌 审读 徐恬 二审 李璐 三审 吴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