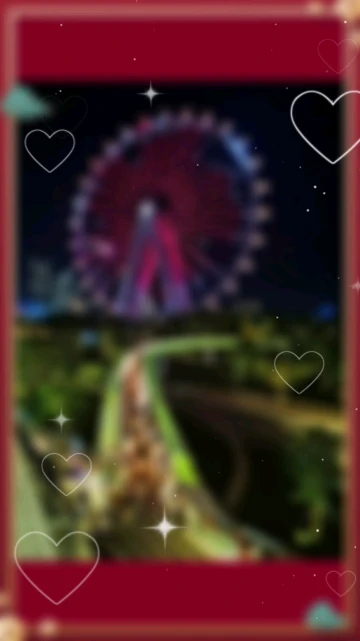引言
近年来,背靠敦煌文化所创作出的舞蹈类作品呈现出艺术效果斑斓,但思想性有待深入。这是一篇浅谈舞剧《敦煌来归》的个人感想,观众都说“瑕不掩瑜”,笔者在这里大家的分享一下“瑜”在哪里?
1、敦煌舞是敦煌舞,壁画舞是壁画舞
敦煌舞的本质是中国上个世纪从壁画中提炼出的一种新中国古典舞蹈风格;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构建出完整的教学体系。从历史角度来说它很年轻,只有45年的艺术实践;但近年来,它在全国的高等舞蹈教育里已经成为了一门必修课,其社会实用价值日益凸显。
作为一种新中国古典舞类型,敦煌舞可以概括唐代敦煌地域周边的舞蹈风貌。在舞蹈本体创作的发展规律上,它是从历史遗产中提炼出的现代“古艺术技巧”。在当下舞剧艺术的创作中,它是编创泛唐题材舞剧中最鲜明的“艺术手段”。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理论上,敦煌舞是不可缺少的。
舞剧《敦煌归来》中运用的敦煌舞素材典型且特殊。该剧“序幕”、“祈愿”、“呼唤”段落里的手臂之舞是典型的“后敦煌舞主义”。何为“后敦煌舞主义”?这就不得不得谈到敦煌舞的三种创作手法,即佛国天乐舞、壁画俗乐舞以及敦煌主题舞。其中,天乐舞是依托“经变画”创作而来;俗乐舞提炼自非“经变画”的其它壁画以及敦煌写本,包括了古代市井生活、民俗风貌和军事行动等。
后敦煌舞、敦煌主题舞则是从前两者发展中而来,在吸取大量程式化的标准动作后,将舞蹈表现的重点放在了现实的敦煌。形式表达上出现了一种对古宗教艺术视觉的反叛,创作素材选择上则更趋向于纯粹的“千佛形式”,最终体现出一种后敦煌舞独有的舞蹈运动行为观念。这就是当下中国舞剧肢体里渐显出的“后敦煌舞主义”,它甚至隐藏在当下很多热门舞剧之中,笔者也在舞剧《敦煌归来》中看到了对老一辈构建新中国舞蹈文化艺术家精神品格的尊重。
舞剧《敦煌归来》在对敦煌舞和现代舞融合传承方面交出了一份答卷。敦煌舞是古代佛教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现代抽象艺术,它包括但不限于莫高窟,提炼对象的特征是佛教汉化的历史物质遗迹。今天甘肃舞蹈高校的很多敦煌舞实验作品,已经不再向纯壁画内容靠拢,而是将提炼出的中国敦煌舞姿,融合现代舞运动方式去构建更多从属于当代性的舞蹈。可以理解为现代舞在今天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因为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有一种特别“味道”。这种“味道”在“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实在丰富的重要作用,就如同上世纪甘肃省对敦煌舞的开创丰富了中国古典舞一样。这种“味道”也出现在了由深圳当代舞团制作的舞剧《敦煌归来》中。
2、敦煌是敦煌,莫高窟是莫高窟
除了敦煌舞创编角度,舞剧《敦煌归来》的舞美设计也值得一提,笔者将从地区自然风貌和创编角度上谈谈。
不能将沙漠和戈壁混为一谈,两者间是有区别的。如果用极简来描述沙漠,戈壁就只能用荒凉与辽远来形容。他们的外部质感可以分别概括成“柔软的沙漠和锋利的戈壁”,内部质感则是“坚硬的沙砾和脆弱的黄土”。敦煌的自然现实就是这样,沙漠和戈壁的交汇线像是人为的“肃杀一笔”,方正地成为了古代地域行政的界限划分。舞剧《敦煌归来》舞台上采用的立体沙块,在移动中几乎完全体现出了“西北土”的特征。它既体现了土长城、土房屋等实体建筑单位,也演绎出了独特的地域气候特质。舞台上每一次立方沙块的变化,寓意着“信使团”前进所经过的每一块土地的史实,故在舞剧《敦煌归来》中看似不同的反派势力与“方块”的设计动线是一个整体,例如,两者在“祈愿”段的配合运用既典型也让人震撼,立方沙块配合反面角色行进移动,主视觉上不断挤压“百姓”的空间,演员们瘫坐在地上并向后挪动的舞蹈动作,将历史上敦煌区域(瓜、沙二州)的情况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完成了宏观叙事的描述,也将观众带入到该剧的情感场域中来。
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这部舞剧的基础已经成功了。 讲敦煌故事,绕不开莫高窟。莫高窟究竟是什么地方?对于历史上的敦煌百姓而言,简单来说,它就是百姓过节要去的地方。而且敦煌莫高窟与云岗、龙门石窟有很大区别,它不是皇家石窟,是更贴近于底层百姓的艺术、宗教甚至是社交区域所在。许多重要的敦煌社区行为,例如,私家窟营造、供养人壁画绘制、敦煌“女人社”的供奉活动,均是不同社会群体围绕着莫高窟所代表的文化而展开。从艺术发展角度来说,包括莫高窟在内的寺院等场所是封建时代底层百姓少有可以交流艺术并完成艺术创作的场所。这座由人民智慧和实践共同创造出的所在,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遗产的精神宝库。舞剧《敦煌归来》不见莫高窟,但处处都是莫高窟。笔者认为该剧在大胆地进行一种隐性表达,将莫高窟这一具体的符号交还给“敦煌百姓”。从具象的符号展示进阶到抓取本质,从平面的视觉艺术抽离出人性、人情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敦煌归来》中多处“灯舞”,除了反映古代敦煌“燃灯节”的真实民俗活动,导演也抓住了敦煌地区历史上的“人类群体行为”,赋予了“灯舞”更加真实的历史人文思想,并由固定地区节日延伸出该剧“信念守护,灯火延绵,爱与归思”的核心主旨。
如此可见,舞剧《敦煌归来》并没有常见的趋向于狭义概念的“敦煌形象”。作为传统剧院艺术,在尊重传统艺术科学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新时代“敦煌舞”尝试出一条可前行的路径。
3、高进达不止一位,凤归云不止一曲
要看懂这部剧,需要理解舞剧《敦煌归来》将故事背景定义设定在“抽象飞地”的概念上。它是暂时的、特别的地理人文现象,隶属于唐朝管辖的土地但不与中晚唐核心区域相连。“抽象飞地”的特殊性和外在压力造就主角一行人把代表“忠义和回归”的舆图送至唐廷,这批信使团需要穿越当时局势混乱、处处危机的西北区域。高进达是唯一被记录下来的人,但纵观归义军,他们的历程必然是由无数个“高进达”奉献一切才能走出来的。“高进达”作为主角是对这一历史客观真实存在的肯定。在舞剧《敦煌归来》一队人遭遇的矛盾冲突和牺牲并不是为了戏剧冲突性的故意设置,实际上是对信使团近四年的艰难行程以及归义军无数人的牺牲进行浓缩和概括。
如果说剧中男性角色是归义军的缩影,那么女性成员凤归云便是一个集合敦煌美感的戏剧角色。
“凤归云”是一个词牌名,原是唐代的曲名。“凤归云”注定了这个角色的多才多艺,“危机”一段中惊艳的琵琶舞,是那个时代敦煌女性魅力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凤归云琵琶舞段在剧情中的戏剧动机,还是今天在舞台上呈现出的观演效果,形式和内容的高度吻合产生出了巨大的能量。舞台上,该段用舞蹈本体推动剧情,提起观者情绪,完成对坚毅女性群体的概括性表达,其特征是鉴别舞剧艺术在形式上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
4、古今中外文化兼容并蓄,这很敦煌
引用季羡林先生的话“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古)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敦煌”从诞生之日起便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属性。基于此,敦煌舞乃至敦煌主题作品的内在也应是多元且包容的。
舞剧《敦煌归来》的“夜袭”段落出现了朝鲜刀舞和藏舞步伐。举个例子,从舞蹈造型特征上讲,敦煌壁画舞姿中有大量的西域泛鼓类舞姿,这些鼓的部分由西而来,传入大唐后继续向东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唐朝结束后,新的艺术风格逐渐融合和覆盖前一时期特征,而历史的潮流又将其带回,开始向新的艺术风格靠拢并反哺。最后在宋元明清经历了筛选、淘汰以及重新定型。
舞蹈艺术也遵循这一规律。舞剧《敦煌归来》“夜袭”段中的刀舞,就是传统艺术的再次历史轮转。盛唐时期,尤其是酷爱歌舞的唐玄宗时期,世界的歌舞艺术快速涌入大唐。而唐王朝也敞开怀抱,用中国的文化体系观不断吸收来自外国的歌舞;比如中国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它的前身是“婆罗多曲”,还有“龟兹舞”曾被换名“紫薇八卦舞”等等。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朝鲜族的《高丽伎》被列为《十部乐》之一。《十部乐》其它9部,即清商、天竺、安国、龟兹、西凉、疏勒、康国、燕乐和文康。《十部乐》能作为唐朝的宫廷宴乐,代表了大唐的鉴赏肯定。随着朝代更迭,社会日新月异,《十部乐》只为宫廷而演的时代早已过去。舞蹈艺术本体在规律中传承了它,自然而然地流淌在中国身体语言艺术家的身上。被刻进“基因”里的舞蹈本体的传承,散落在不同舞者的身韵里,散落在丰富多彩的中国民间的舞蹈中,被不同的主流艺术形式所承载。
胡沈员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收纳了中华民族民间的舞蹈精粹,组成胡沈员舞蹈的是56个民族的舞蹈精华。他的学习经历就如同一千年前唐朝音乐教坊里的舞者一样——汲百家之长,融会贯通。同时,胡沈员在国际舞台上的艺术交流体现出“互通有无 ” 的表现,与构成敦煌壁画中舞蹈的因素是四大文明的汇合特点不期而遇。
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舞蹈家崔承喜老师,走得便是一条“ 用西方现代舞技巧不断地探索朝鲜传统舞 ”的发展路线。今天,胡沈员就是不断的在用现代舞形式探索中国传统舞蹈。舞剧《敦煌归来》中的“夜袭”段刀舞,从形式上可以说是朝鲜民族舞的“盛唐归来,敦煌归来”。笔者认为这是一次在尊重艺术规律和古代劳动人民成果基础上,将理论付诸实践的积极尝试。
马克思提出,艺术的起源离不开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时至今日,“敦煌”的艺术传播也经过漫长的实践过程。就如公元六世纪那些一步步行走在大漠里的“何法师”们将心中的“净土”传播向各地,当今敦煌文化传播者以多样的形式赓续不断地将敦煌文化的星火洒向全世界,让世界瞩目于这座全人类文化遗产宝库的魅力。
舞剧《敦煌归来》本质是在讲好“敦煌故事”,而不是在重复敦煌的印象。
敦煌舞诞生于中国经典舞剧《丝路花雨》,正是它不止一面地展现敦煌艺术、敦煌历史和人文真实的丰满厚重内涵,带给了中国舞蹈研究以及中国古典舞科学建设的价值。四十五年未曾间断的传承,充分证明了敦煌文化的历久弥新和博大精深,才能让笔者能够更深度感受到舞剧《敦煌归来》的创新价值。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活力源泉,也是文明绵延繁盛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进行文化创新创造,涌现出一个个文化高峰。
舞剧《敦煌归来》切实找到了敦煌文化与艺术在创新创造上“历久弥新”的发展规律。笔者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们围绕“讲好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一使命,勇于实践、积极创新,多角度多维度的深入发掘敦煌,理解敦煌文化,发扬好敦煌精神。
作者: 罗志炜,甘肃省优秀青年文化人才,国家艺术基金青年民族舞剧人才,中国经典舞剧《丝路花雨》第十四位“神笔张”扮演者,代表作品《故园.1900》、《冰雪荧煌》等,新媒体ID:萝卜丝
编辑 吴诗敏 审读 秦天 二审 桂桐 三审 窦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