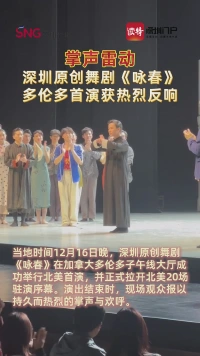非洲有一句影响全世界的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很幸运,我就生在那么一个村庄,我曾在那个有着黄土地、小山丘、小陂塘的村庄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村庄里,长有槐树、杨树、榆树、椿树……那些树,是我在南方求学及工作后再也没有见过的树,是我在他乡再也无法觅到的乡愁。我家院中有一棵高几十米的白杨树,树上有一个喜鹊窝,肥壮如大公鸡的喜鹊是故乡特有的鸟,那也是我走出故乡后再也没有见过的鸟。
某年春天,记不清我从什么地方带回了几颗蜀葵种子,随意扔到了庭院中。第二年,院中长出了两棵奇异的花儿,一枝向天,火红的花瓣怀抱着花秆儿盘旋而上。第三年起,院中长满了蜀葵。后来,我在多个城市、景区又见到了蜀葵,只是没有一棵有我家院中的蜀葵开得那么娇艳。
村后的西山上是一个苹果园,那是我的小伙伴晓晴家的,她的父亲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农民,开辟出了村中第一个苹果园。春天,苹果树开出了白花,西山变成了一个飘浮在白云中的仙山。夏天,苹果熟了,香气满溢整个村庄。等到晓晴的爸爸把苹果卖完,我与弟弟便在苹果树间徜徉,总在某个不经意间发现一棵熟透的红苹果挂在高高的枝头。弟弟如猴子一般爬上树,麻利地摘下苹果递给我,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甜的苹果。
村子东边,是一个小平原,那里是一片肥沃的良田。冬天,麦苗青青,那小苗儿与韭菜极为相似。忽地来了一场大雪,麦苗盖上了一层棉被,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我们躲在屋子里,烧上木柴,烤着火,火里“噼啪”作响地烤着黄豆和花生。暑假来时,麦子熟了,原野里金黄的麦浪翻滚,那是梵高也画不出的颜色。麦子的季节过去,田野里就换上了水稻,我们穿过田间小路去上学,不时可以看到几条长长的蛇游走在水稻间。水稻似乎成熟得特别快,转瞬间,稻穗由青而黄,压得稻身沉甸甸地低下头。几次稻子低头间,我就离开了故乡,那漫长而短暂的童年时光啊。
读本科、研究生期间,我没有回过故乡,在外乡打拼的岁月里,我似乎遗忘了故乡。一天,我独自一人在一个餐厅吃饭,忽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幅似曾相识的画:一个白杨掩映下的村子,村后是一座小山,似有白云缭绕,村前是金黄的麦田。我吃着饭,不觉哽咽:这不正是我那梦魂深处的故乡吗?这时,餐厅中响起了宗次郎的《故乡的原风景》,我不禁潸然泪下。
后来,与我同住的母亲耐不住深圳的“寂寞”,回了老家。那个深秋,我买了返乡的车票。当我站在村口时,我有了恍如隔世之感,曾经人声鼎沸的故乡,已空空如也,为数不多的老房子已被荒草侵占,村口的祠堂红漆斑驳。村中不过三五老人,是我不认识的陌生面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生如梦”,我在梦魂深处千百次回忆过的童年生活,似乎真的是南柯一梦。
那个黄昏,我在村子前立着,树满村庄,水绕陂塘。我在心里说,没错,这就是我的村庄,我就是那个自这个村庄中走出的孩子。我的村庄静静立于鄂西北的边陲,在记忆的无边麦浪里,时间老人挥舞着镰刀,收割着熟透的人生。少时眺望远方,成年缅怀故乡。提笔挥墨,墨水滴落之处,叫做“村庄”。
编辑 温静 审读 匡彧 二审 李璐 三审 潘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