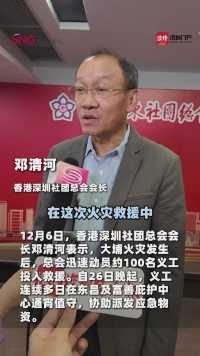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喜欢逛学校小卖部。没别的理由,就因为课间休息不让出校门,操场和教室也没啥玩的,所以全年级几百个学生都喜欢挤进十几平方米的小卖部。尤其刚下体育课,好多臭烘烘、毛茸茸的脑袋扎成一堆儿,跟赶庙会一样。

那是我们学校唯一一家小卖部,老板是个胖老头,一脸横肉,语气冰冷,据说是校长远房亲戚,经常算错账,还爱呵斥我们。但那里应有尽有:铅笔、橡皮、尺子、圆规、作业本、红领巾……虽然都比外面贵;一毛钱一个的茶叶蛋、一毛五一包的海带丝、五分钱一把的瓜子和两毛钱一瓶的桔子汽水儿……
我一天之内会逛十几次小卖部,光看不买,也特别满足;如遇见高年级同学,满头大汗,甩出两毛钱说:“来瓶汽水儿!”我会主动去帮他找瓶起子,目的是能闻到开瓶那一瞬间凉凉的桔子味儿。那时我常想:“有钱就是好啊,能天天喝汽水儿”。小卖部就是我的天堂,是整个世界,店老板是我最羡慕的有钱人。
暑假,店老板要回老家,会让他女儿来看店。除了语气冰冷,他女儿和他一点都不像,齐耳短发,微微龅牙,清瘦脸上有几颗小雀斑。人少的时候,她就躲在柜台后面看书,约略是《读者》《故事会》什么的。我那会儿写了几篇儿童征文,赚了点零花钱,就去小卖部里逛,经常见不到人,大喊一声“老板,买汽水儿!”等好一会儿,她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头发蓬乱,睡眼惺忪,带着一股湿湿糯糯的被窝气。她收钱递货也从来都不看人,只一刻不停在账本上写写划划。有一次趁她不在,翻了一下账本,发现用娟秀的小字密密麻麻写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几个感叹号!隔几行,“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又是几个感叹号!

毕业后再没见过那个姑娘,或许,真遇见也认不出来了。只记得小卖部是我曾经最美好最满足的世界;在那段时空里,还有个姑娘应该和我做着差不多的文学梦。她最后去哪里了,这世上应该不会有人关心了吧?如果她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表达欲,又足够幸运,她会成为另一个李娟吗?
所以,在观看或阅读《我的阿勒泰》的时候,我会有所触动,并非因为主人公叫李娟、李文秀,还是其他什么普普通通的名字;也不因为那是剧还是小说,甚至故事未必发生在阿勒泰还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重要的是从中看到了一个环绕着“小卖部”发生的故事(虽然那个流动的“小卖部”和学校的并不一样)。
我们都从同一个贫瘠而日常的年代而来,曾因为贫瘠而享有某种内心的纯净和真诚,曾因为贫瘠又做着一个更丰富的文学梦。不管这是不是事实,至少我们在暗暗说服自己,这就是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毫无疑问,无论你是否去过阿勒泰,《我的阿勒泰》都可以成为“你的阿勒泰”,它是《瓦尔登湖》,是《燃情岁月》,是今天许多城里人的“诗与远方”,这是这部剧首先给予我们的文化想象和影像奇观。在那个广阔无垠、风光秀丽的世界里,也许连人的时间尺度和感受都变了,所以,城里的斤斤计较和功利计算都不再那么重要,人们以另外一套规则与自然相处、与彼此相处,
但只见其大而忘其小,只见其美而忘其难,同样不是全面客观的认知与描述。美丽的景观再美好,如果与人无关,很难引起人的共情与共鸣。这些年,有太多表现新疆自然风光的大片,为什么唯有这部作品走入了我们的内心?因为它和原著一样,没有花费太多笔墨在怪力乱神,没有刻意制造太多的矛盾冲突,而是踏踏实实关注和记录了阿勒泰汉人与哈萨克人的生活日常。
日常多么难得,日常又多么难以表现!真实的日常没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虽然也许充盈着各种尴尬、困惑、妙趣、意外,但是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描述日常,从文体表达的角度来看,必然是一种散文化叙事,又必然是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所以,一个想要还原日常时空的导演、编剧或作家,就必须在传统线性叙事的时空里找到另外一种时间节奏,也可以说,他们(或她们)是在重构一种新的戏剧性。
在这套影视表达的符码系统里,我们只输入“宏大、美、苦难、冲突”等元素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需要在叙事肌理中铺陈足够多的“幽默”、“温暖”和各种连绵不绝的小小“惊喜”——它们根植于鸡毛蒜皮的琐碎和庸常,却能提供新的戏剧能量,并且更真实地折射人性光辉。
所以,我始终认为,《我的阿勒泰》是一部以“小”取胜的作品,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如此渺小,但人的坚韧、乐观和相互温暖才显得如此可贵。我们对日常世界的感受就像是身处于张凤侠和李文秀的小卖部,简简单单,扎扎实实,虽然种类未必丰富,却可以满足林林总总的情绪价值。
当然,这部剧被人追捧,就和我记忆里“小卖部”爆火的原因一样,一个是因为“稀缺”,一个是因为“真诚”。“稀缺”的在过去主要是“物质”,在今天也许是“精神”;“真诚”既是指创作者面对作品的态度,也是指社会的氛围、时代的风气。
我们为什么喜欢《我的阿勒泰》,因为“真诚”本身就是我们越来越需要的“稀缺”品了。
(作者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 刁瑜文 审读 张蕾 二审 张樯 三审 詹婉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