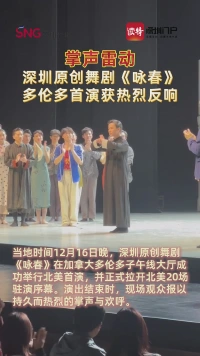■谈炯程
曼德尔施塔姆于1910年发表处女作,获得广泛赞誉,后自筹资金出版诗集《石头》一举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诗人的个人生活并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坚持创作,并且要求精益求精,所以终其一生,也没有出版几部诗集。尽管诗人留下的作品并不算多,但是几乎每首都是上乘之作,许多作品在当时都在诗人圈子内引起广泛的讨论。1938年冬天,诗人含冤而逝,他的作品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法与读者见面,所幸诗人的遗孀和亲友竭力保存了大量诗人的手稿和抄稿,这些不朽的诗篇最终得以重见天日。《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由著名翻译家郑体武教授参照多个同类俄语版本编成和译出,书中收录曼德尔施塔姆一生所作全部诗歌作品共590首,包括若干新发现的散佚之作和未竟之作,是名副其实的“全集”。

阅读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曾几何时,是一种极隐秘与个人的体验。他的死亡先是将他变成一个秘密,而后,又成为传奇。从1891年到1938年,诗人仅在世上活了47年,而他的笔穿透世纪末的阴霾与世纪初的大洪水,将那苦难时代结晶为崇高的诗艺,最终,后人搜罗他的作品猬集于此的,有这590余首诗。但这些诗,却是顽强地存留下来,作为其遗孀与朋友的私人记忆,作为不断从脑室剥落的声音,作为诗人圈子里秘密传抄的手稿,它们抵抗住了遗忘,一直到1987年,诗人获当局彻底平反,这些诗得以正式在俄罗斯整理出版,包括他的成名作,1910年仍带有古典印记的自费诗集《石头》与他达至巅峰的《沃罗涅日笔记》,甚至还有为儿童写作的极为标准的童诗,一个大诗人的各个面相终于得以向我们呈现。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卓越的天才诗人。著有诗集《石头》《悲伤》和散文集《时代的喧嚣》《亚美尼亚旅行记》《第四散文》等。另有大量写于流放地沃罗涅日的诗歌在他去世之后多年出版。
“对世界文化的乡愁”
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在诗艺上极为早慧的诗人。在诗论散文《论词的本质》最后,他引述了莫扎特与萨列里的一段公案——曼氏希冀的“属于客体词语的活生生的诗歌”,其创始者“不是理想主义梦想家莫扎特,而是萨列里这位严厉苛求的匠人。”在俄语文学及后世流行文化中,庸才萨列里出于嫉妒害死天才莫扎特的叙事已成为一则神话:其较完整的表述最早见于普希金创作于1830年,即萨列里去世5年后的小悲剧《莫扎特与萨列里》,又因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改编、谱曲的同名歌剧与1984年美国导演米洛斯·福尔曼的奥斯卡获奖电影《莫扎特传》而广为流传。实际上这两位杰出的音乐家关系并不差,萨列里亦十分推崇莫扎特的音乐。
曼氏藉此典故说明他的诗学要点不仅在出没于诗行的古典意象,还在于我们常会在其他现代派大师那里遇到的姿态:写作者唯有将写作视为一份智性工作,如同石匠修整石块一般打磨词语,并依照图纸将它砌入诗行之中。曼氏的意象,往往结着一层文化的痂,他敲开它们,在它们身上留下语言的凿痕,于是它们便如枯山水一般置入诗中,曼氏所言的“对世界文化的乡愁”,当我们凝神在诗歌富于修辞活性的表面时,便会逐渐显影:希腊、罗马、法国古典主义时期的主题,与让这拜占庭僧侣的语言趋向俗语的尝试一样,都如蜃景般镂刻在俄语的内部,而曼德尔施塔姆透过写作激活了它们。
他常用建筑术语谈论诗歌,诸如巴黎圣母院之类的哥特式建筑,是他心目中诗歌结构的典范。1913年,在《阿克梅派的清晨》这一文学宣言中,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语言公式:A=A。这里,他并不是说词会被拴在具有唯一性的所指上,恰恰相反,词即是词本身,诗人的材料,是词的能指——声音、色泽、形状与质感,而非意义。就像一块石头并不能独自构成建筑,只有当它们被一种超越时间的亲密感黏合在一起时,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空洞,才会发出无尽的回声。曼德尔施塔姆认为“萨列里值得尊敬和热爱”,因为他听到了“代数的音乐”与“活生生的和谐音”,诗人同样从词的缄默中听到了这份鲜明的生命力。由此,他寻求某种坚实、明确、固体样式的诗,以对抗俄罗斯象征主义宛如失血的流体风格。这也是为何他将其第一本诗集命名为《石头》。
他的最佳诗歌之一《页岩颂》的中心意象,也即是一片承载着生物印记的页岩。“岩石那强有力的分层”所拥有的横的结构,是一种空间性的乡愁:如同目击一次日落,我们的眼睛饮下黑暗,它如酒精般占满了天空的血管,而黑暗并非突如其来,它早已在时代昏昏欲睡的躯体中搏动,但我们此刻却像被捕兽夹夹住,只得目睹时代来到那必然的临界点,经过此处,便要放弃一切希望。我们唯有一种黑暗时代的人本主义,使我们相信人与人之间尚未丧失的亲密感,也使我们在内心深处怀有那被禁止的自由。因此,当“垂直线在向它们布道”时,便有横与竖的矛盾:不断延展的时代,与那刺破它的“同时代性”。我们在荷尔德林、阿甘本与尼采的意义上谈这同时代性,它意味着一种迟到感,一种“不合时宜”。当人们在时代的表层冲浪时,诗人看到波浪下的皱褶与深渊,以及海啸的可能,他的目光更穿透本时代的危机,觉察到一种根本性的无根状态,页岩同时作为诗与时代的喻体,既湮灭、融解我们,也浓缩、保存我们,将我们最本质的生命力压在石油黑色的笔划里,以便后世重新将我们点燃。而这同时代性的最终产物,便是诗人在流放期间所写的三册《沃罗涅日笔记》。

《我独自一人面对严寒: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全集》
(俄)曼德尔施塔姆 著 郑体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12月
以诗歌见证生命与自由
后期的曼德尔施塔姆发展出一种兼具厚度、密度与加速度的诗歌语言。在逼真到近乎让人窒息的画面中,现实的惊人细节与他的用典,没有一丝装饰性,而是径直融在一起,化作一块粗粝的合金。就像精雕细刻的金饰,他《石头》时期的诗作有着富丽堂皇的细节,但时代将它们掠夺一空,并重新熔铸成可供流通的金锭。“我用声音工作”,他宣称:“我没有笔迹,因为我从不书写。”《沃罗涅日笔记》中越来越多地出现诸如复沓之类的技巧,不单将情绪推向一个爆点,也让我们辨认出这些诗的口语根源。
《沃罗涅日笔记》中的诗通常只有一页纸左右的篇幅,有时甚至直接变成呼喊或与词语的缠斗,譬如这首写于1935年4月的只有四行的短诗:“放开我吧,沃罗涅日,把我送还:/你会失落我,或者错过,/你会丢掉我,或者找回,/沃罗涅日——胡思乱想,沃罗涅日——乌鸦与刀……”其中最后一句“沃罗涅日——乌鸦与刀”(Voronezh-voron, nosh),依照维克托·柯里弗林的说法,显然诗人“在地名Voronezh的发音中找到了某种依据:在这个地名中可以听到vorovskoy(强盗的)uvorovannoy(窃取的)以及voron(做贼的乌鸦)、nosh(窃贼的刀子)等词的回声”。而当时运送犯人的囚车也被称作“黑乌鸦”。因此,这句诗也对应着电影《夏伯阳》中的一句歌谣:“黑乌鸦……你不会得到猎物……/黑乌鸦,我不是你的!”诗人被权力的黑乌鸦俘获。1934年5月,他因一首嘲讽斯大林的诗被捕。传说斯大林曾为此事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尽管恐惧,帕氏仍告诉斯大林,在俄语诗歌领域,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他的语言光谱极宽,即使同一诗节内部,也时常糅合俗语与精密的修辞。在《沃罗涅日笔记》中,他用一种幽默的口语叙述解嘲:“这是什么街?/曼德尔施塔姆街。/这姓真是活见鬼——”从这姓氏中,他读出自己身上“缺乏直来直去”,第二节诗则说明,这街道也并未以他的名字命名,只有“这个坑”会以曼德尔施塔姆为名。
诗人几乎无力应对暴虐的大地,他只有让诗歌本身越来越尖利,如啸叫,如呼唤,从一个世界文明的召魂者,变成一个如奥维德、但丁那样不断诗化诗意使命本身的流亡诗人。《沃罗涅日笔记》由碎片的形式编织而成,看起来并非一个完成的作品,它是诗人的采石场与工具箱,保留着尽可能多的现实的棱角与诗人口述这些诗作时产生的声音与文字之间的裂隙,诗人的形象映照在这些闪着七彩光芒的碎片中,愈发伟岸,也愈发抽离自身。只是这些诗句带来的,如同直拳般的撞击,不单作为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历史的见证,也作为一份档案,证明人类这一生灵的勇气、生命与自由。
编辑: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