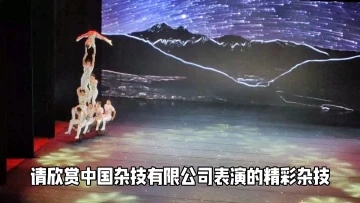在此之前没人会想到,所有电影院停业会是怎样的情景,可就在2020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们长时间与电影院隔离,至今已占据一年中的大半光景。我们既闻不到爆米花的焦甜味道,也无法在宽大的银幕前观赏科技、幻想、现实与人性的完美结合。但电影,永远都是电影院以外的艺术。它这种艺术,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在它发展之初,就因它特有的时效性和通俗性得到过承认。1913年的《美国杂志》便称赞电影是“人性在银幕上回归”,尽管它也遭遇过千夫所指,比如被粗俗、愚蠢、煽情、圆滑、政治宣传、怂恿消费、教唆青少年等言论所攻击,但它始终是大众文化中无法替代的,它承载的是一种精神愉悦,或者普通人对另一种人生的探索。
不可否认,电影史上出现过多个全盛时期(尽管短暂,通常不超过十年),所展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在社会、技术、历史和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创作成就。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创作的高峰时期还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和苏联、30年代的法国、40年代末英国和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法国新浪潮的再度崛起、60年代中叶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影、70年代的德国新电影与同时期马丁·斯科塞斯和罗伯特·奥特曼等“电影小子”所代表的好莱坞以及8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作品等等。电影的发展与不同国家的历史或现状息息相关,艺术的表现形式与风格也在其中变幻着不同的审美需求。

《电影通史》(第2版)
(英)菲利普·肯普 著
王扬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0年6月
今天(7月20日)是国家电影局规定的低风险地区电影院有序开放的日子,有多少家影院能成功开业还需观望,有什么样的影片会公映也仍然是个问题,但无论怎样,离别太久的电影时光正在归来,这是值得期许的。疫情改变了现实生活种种,它的破坏力之强大令我们不敢松懈,但我们能利用它所带来的停摆时光去回望与反思,包括如何看待电影本身。可能你不是电影研究者,但这不影响你在电影院里追逐商业大片,曾经没有时间去想电影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也不曾关心它的历史,不妨在此时了解一下它因何而存在,可能会为你下一次走进影院带来一种全新感受。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电影通史》,是一本全面的电影普及读物,它展现了世界影坛的重要时期、主要流派和经典作品,并以电影的高速发展反观社会和文化的演变。图文并茂的文章深入全面地阐述了每一种电影类型,从最早出现的默片到史诗票房大片,以及21世纪出现的电脑动画与视觉特效。翔实的历史年表让读者对电影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目了然。
电影史上这些重要时间点
或许你并不会有意识的将电影归于艺术的范畴,就像中国的民间曲艺相声那样,在小剧场里听和电视里听,都只是为了图乐,如果不是有人提醒“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你可能不会将它与“艺术”这个词语联系到一起。电影也同样存在这样的误区,可能院线电影在市场化的票房驱使下,让它看起来和相声的作用并无二致,但商业电影也依然有它的艺术价值。
可能同样一个故事,从银幕上搬到舞台上,你会觉得是艺术,而电影的呈现更多给你一种娱乐的体验。所以电影的艺术地位不单游离于“六大艺术”(文学、音乐、歌剧、舞蹈、戏剧、视觉艺术)之外,它更游离于世人的观念中。电影发展至今,从影像的表达到肢体动作,从无声到有声,从简单的情节到对生活与时代的捕捉升华,从粗放的布景到电脑特效的展示,电影都紧扣“人性”这个主题来讲述,和大多数严肃艺术一样,它放大想象和生活的局部,与我们一起探讨生存问题。它结合了其他六艺,又远远超越了单个艺术的局限。

电影在成为艺术的道路上经历了什么?我们一起来回顾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1895年,电影拍摄技术出现。最初的作品长度只有几秒钟,内容则是日常生活或魔术戏法。
1901年,一分钟短片《征服天空》上映,主角坐着奇怪的飞行器飞跃巴黎美丽的上空。这部划时代的短片让后人记住了三位走向电影前沿的电影人,他们是乔治·梅里爱、查尔斯·百代和费迪南·齐卡。
1900年,一部电影史里程碑的作品上映——《袭击中国使节团》。这部电影受晚清义和团运动所启发,描绘了一群基督传教士遭到义和团围攻的场面。英国先锋导演詹姆斯·威廉森利用一间废弃的房屋、几十名演员、爆炸和枪战的动作场面,展现了当时最为成熟的叙事手段。由此,该片也攻克了电影成为一门艺术的技术难题——如何利用一连串的镜头创造行为的延续性。
此后,电影中开始呈现出文学性,即改编自文艺书籍的作品。
1903年,美国第一部故事片《火车大劫案》上映,埃德温·S·鲍特革命性的动镜和剪辑、实景拍摄和西部片风格令当时的观众大呼过瘾。技术的进步让拍摄更长的电影成为可能,于是文学作品进入了电影的视野。
1907年,加拿大导演西德尼·奥尔科特拍摄了第一版《宾虚》。这部改编自卢·华莱士1880年的小说在电影中浓缩到只有15分钟,虽然它让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难以理解,并惹上侵权的官司,但却为未来的文学改编作品开创了先河。
1911年,早期的意大利电影就热衷于神话故事和壮观的场面。但丁的作品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一年,意大利的第一部长片《但丁的地狱》上映,被视为改编自文学作品的成功例子。
技术革新与文学作品的加持,不仅能让电影拍出长片,还给了它创造系列剧的土壤。
1913-1914年的五集系列片《方托马斯》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根据法国最著名的犯罪小说改编,每集长约一小时,以惊心动魄的悬念结尾。该片导演路易斯·菲拉德的惊悚片技巧还影响了弗里茨·朗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等日后的电影大师。
1916年,《海底两万里》的成功,得益于儒勒·凡尔纳1869年的同名小说和《神秘岛》的原著加持。
现代社会,改编文学对电影的影响不言而喻,它既是电影创作的素材,也体现了电影本身对于文学与时代精神的认识与思想解读。中国第五代导演中的张艺谋就曾多次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并大获成功——《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大火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的《妻妾成群》。

什么会造成电影业的倒退
当然,电影中最直观的表达就是动作与声音了。在它的发展历史中,这两样比文学性更为重要,它能直接地将观众带入到这个光影世界中。
提及默片时代,不能忽略的名字就是卓别林。他将默片电影推向一个高潮,以至于当有声电影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其称为电影业的一种倒退。一部由欧洲移民导演拍摄的美国都市生活故事《孤独》具备晚期默片的优秀素质,但其优点被陈腐无趣的对白彻底抹杀。
什么是默片时代的辉煌作品,不如看看卓别林在《淘金记》中是如何表演的:卓别林扮演的是一个困在小木屋内的衣衫褴褛的淘金者,他有一段吃皮靴的境头堪称经典。卓别林用让人难忘的一丝不苟的态度精心装盘,细嚼慢咽,仿佛鞋带是美味的意面。这简直成为默片的象征——用幽默的方式演绎残酷故事。此方法至今都有人在舞台上效仿,成为演绎默剧的套路。
可1927年在纽约首映的《爵士歌手》就没有这么好运,这部有声电影上映的第一天就被影评人称为“滑铁卢、萨拉热窝和珍珠港般决定性的,铭刻影史的可怕一天”。虽然这一说法略显夸大,却如实地反映了有声电影出现之初的震撼和人们对其可能摧毁电影艺术的恐惧。
我们今天站在电影艺术越来越多样化的今天来回望这段历史时会感慨,如果没有前人的突破与尝试,就没有我们今天在大银幕上所呈现出来的更丰富的视觉盛宴。科幻电影的技术与想象、恐怖电影的冲击、黑帮电影的枪战、史诗电影的恢弘场景等等,可能都无法有效的表达。但有个问题始终需要警惕:什么会造成电影业的倒退?我认为,作品中脱离对现实的关怀可能会严重影响到电影的发展。
回顾其历史,电影的发展几乎都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反映。卓别林的《淘金记》是对美国那段淘金热的反思,著名的好莱坞犯罪片是由20世纪70年代以震惊美国的曼森家族血案拉开帷幕的。水门事件无可换回地玷污了最高机构的权威之后,不得人心的越战以美军撤出西贡的不光彩方式结束。幻灭、质疑权威和被害妄想充斥着这一时期的犯罪电影,一如当时的社会。阴谋电影,比如《窃听大阴谋》《总统班底》《星球大战》等也出自这样的时代的背景。

离开美国,将视野移到好莱坞之外,非洲电影同样也反映着他们自身的时代特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非洲电影可谓是一个创作高峰期,其创意和活力不输给任何时代和地区的电影复兴运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机会、能量和政治催生了大量独一无二野心勃勃的作品。比如塞内加尔导演迪吉比里尔·迪奥普·曼贝提的《土狼之旅》准确把握了非洲年轻人的心声。当殖民时代刚刚结束,新成立的政府纷纷陷入腐败,此时的非洲电影人把目光投向了社会现状。这一阶段的电影包含了诸多争议之作,塞姆班的《哈拉》因无情地揭露塞内加尔独立政府换汤不换药的政治统治,遭到当局的审查和删减。他的野心之作《外来人》借19世纪的故事譬喻今日的非洲传统遭到的外部威胁。喀麦隆电影《穆那茂多》批评新郎缴纳彩礼的嫁娶制度。来自马里的电影《工作》则反映了一家纺织工厂工人的日常生活,并通过一位工程师质疑业主的情节反映了导演的马克思主义者背景。
欧洲电影也同样紧紧地跟随时代的声音。反映“二战”时期的德国和苏联电影,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统治背景下创作了有极强政治倾向的电影。匈牙利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也不乏优秀作品,其中《留给女人的日子》所组成的“日记三部曲”里回顾了当时的政治变迁。
大名鼎鼎的法国新浪潮电影无疑是在反映社会与时代的作品中,个性与艺术成就颇为凸出的作品之一。提及“法国新浪潮”离不开“作家电影”这个名词,他们将电影导演一以贯之的个人印记视作伟大的财富。代表人物有戈达尔、里维特和侯麦,他们热于走出摄影棚,来到街头,既不受困于内景和布光的束缚,也积极展现当下法国人生活的现状与思考。

反映现实是电影发展与创作的核心,无论是哪国电影,要走进人心、走向国际并推动其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经过十年动乱停摆的中国电影业,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仍很少有人能料想中国电影能够制作出享誉世界的原创作品。北京电影学院的重新开张为这一切铺平了道路,而到了首批本科生毕业的1982年,被称为“第五代”的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酝酿一场革命。与此同时,年长的第四代导演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动荡的过去。谢晋用故事片《天云山传奇》表现了1966-1976年期间的社会境遇。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革新的形式出现了,张暖忻的《沙鸥》即采用了半纪录片形式。第四代也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谢飞在《湘女萧萧》里描写了边远地区存留的旧式婚姻习俗。

张艺谋说:“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第五代继承了非戏剧化的结构和去政治化的叙事,而用更少的对话和音乐为人物和故事带来更多诠释的空间。”和前辈“讲述”一个事件的习惯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展示”。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始,疫情是否会影响导演们的“展示”,但无论是讲述也好,展示也罢,我们所需要看到的电影,都应该是世界的、国家的、民族的、个人的苦难与欢愉。
电影院何时能恢复往日的繁荣现在还不好说,但电影的呈现是多样的,影院或许是市场化的入口,但电影的入口永远在生活里。正如这肆虐的疫情,终会有电影会为我们讲述和展示此刻的得失。
(晶报供稿)
编辑 李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