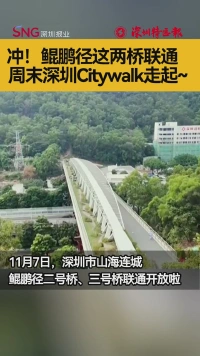深圳布吉大芬油画村,一个闷热难耐的夏夜,星光在大气的扰动下,形成了旋涡状的天空奇观。经过一天的熙来攘往,装卸油画的卡车、讨价还价的画商、四处探店的游客如退潮般消失不见。
此刻,没有人注意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此人长着向上倾斜的前额、强有力的鹰钩鼻、不对称三角形的脸孔和忧郁的眼神,红色须发犹如暗夜中的火苗。他像个幽灵一样四处游荡,村子里举目可见的油画复制品如《向日葵》《麦田》《夜间咖啡馆》《星夜》引他久久驻足,画廊门口的巨幅海报《中国梵高 CHINA'S VAN GOGHS》让他眼含热泪。
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刚刚下过一阵小雨,积雨云随气流涌动翻滚,气氛有些躁动不安。临摹梵高作品已20年的赵小勇怀着朝圣般的心情等候在梵高博物馆门前,却意外发现不远处的纪念品商店竟在出售自己的画作——在国内几百元人民币卖给外国客户的梵高复制品,到这里一转手就是几百欧元。
在欧洲客户的引荐下,赵小勇早于博物馆开馆两个小时进入。他缓步走近《梵高自画像》《盛开的杏花》《群鸦乱飞的麦田》等真迹,仿佛时间凝固了,世界无比安静……与其说他在凝视作品,不如说他在接受作品的审视。
他觉得,大师的笔触已化作簇簇火苗,烧光了他临摹的5万幅画,还有他在大芬村的20年生活。万念俱灰,一切归零。
“在世人眼里,我是怎样的人?是无名之辈,还是一个低到尘埃里的人?倘若果真如此,总有一天,我会用我的作品告诉世人,我虽为无名小卒、区区贱民,却心有瑰宝、绚丽璀璨。”1882年7月21日,刚刚立志成为画家不久的梵高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
自卑而狂热的梵高绝想不到,在100年后的中国南方城市深圳,一片占地不足0.4平方公里的村落将与他发生奇妙关联,人们靠临摹他那些生前无人问津的作品为生。
2016年,由余海波、余天琦联合执导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首映,以赵小勇、周永久为代表的大芬油画村画工群体从反复临摹世界名画到艺术上逐渐觉醒的故事渐渐“出圈”,大芬油画村成了备受瞩目而又毁誉参半的神奇土地。

草莽时代“淘金史”
如果梵高来到1990年的大芬村——这年恰好是梵高逝世100周年——能看到这样的景象:握手楼鳞次栉比,四周杂草丛生、污水遍地。彼时还没有后人熟知的“大芬油画村”,只有令人掩鼻的“大粪村”。
变化是可见的,地处深圳中部的布吉正大力吸引港资以发展“三来一补”产业。深惠路通车带来的交通红利,让原本不起眼的大芬村进入港商黄江的视野。跟其他港商不同,黄江不需要土地、厂房,只要租几间屋子做画坊。他临时组建起一个20多人的油画工作室,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再拿到大芬村完成。上世纪90年代,商业画刚刚兴起,发展势头迅猛。黄江的成功引来无数绘画爱好者、美术学院毕业生,甚至是毫无绘画功底的年轻人淘金,其中就有赵小勇、周永久。
“大芬村老围5号”是赵小勇工作室在地图上的定位,门前那幅“中国梵高”的纪录片海报则是对他过去25年创作历程的高度概括及个人推广。赵小勇生于湖南邵阳农村,自幼习画——他强调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人们更容易理解表面上的因果性:先有前面的伏笔,然后才能有故事。对于在流水线上终日劳作的农民工而言,“靠画画赚钱”除了现实的考虑,还指向一种理想化的生活。
1997年,赵小勇刚刚来到大芬村时,潮汕人周永久已经在这里混迹3年了。初次采访周永久,他正在一条狭窄的巷子里教人作画。这种简陋的教学法不足为奇,既为画家省下了一笔租金,还能为大芬村增添一抹风情。谈及早年经历,周永久将他少年时如何顽劣不堪,又如何在一连串机缘巧合的作用下来到大芬村和盘道出。
当油画撞上流水线
为什么是梵高?首先是这类欧洲订单最多,此外还有一个大背景:1987年,一幅梵高的《向日葵》在英国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出2250万英镑的天价,梵高的作品已成为财富和品位的象征。“不断崛起的欧美新中产阶层未必买得起真迹,买一两幅仿品,装点门面。”大芬油画村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可说。
谁知道,农民工逃离了一条流水线,却撞上了另一条“流水线”:欧美订单呼啦啦涌来,一个画样通常要复制几十、几百幅,交货时间屈指可数,于是每名画工专门负责画一个部分,画完后再由下一名画工接力,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如期完成。“我们在大芬村创造了‘深圳速度’。”赵小勇自嘲说。
在大芬村,想优哉游哉地学画简直是做梦,毕竟不是中产阶层的小孩上油画班,生产永远是“第一要务”。刚刚入行的画工边干边学,两三个月就能出徒。至于赵小勇学了多久,有各种说法,总之时间极短。出徒的标志是自己租房、接订单。那两年,赵小勇十天半个月才能卖出一幅画,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
吊诡的是,在这片艺术与世俗之间的“飞地”上,对艺术无比狂热的信徒反而会被淘汰,现实主义者往往能胜出。1999年,一位香港画廊老板循着“四楼专画梵高”的招牌找到赵小勇,开口要20张样稿。几天后,画廊老板表示美国客户非常满意,又抛出两三百张油画的订单。赵小勇临时招募徒工,动员家人齐上阵,昼夜赶工,一刻不停……这种“满产满销”状态持续了10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要画上千幅。
纪录片《中国梵高》里有这样一幕:周永久的一名徒工画不好梵高《自画像》,把画家画得像一头熊。周永久改了几遍,徒工还是不得要领,两个人都很生气,于是争吵起来,徒工索性摔了画笔要回家——要知道,这个徒弟几个星期前还在学调色,现在就要把梵高名作画得真假难辨。这就是大芬村画匠们的真实处境,他们的劳动连接着最高雅的艺术和最市侩的生意。

▲赵小勇在应付订单的10年之间只干了一件事,而大芬村却发生了沧海桑田之变。
被锁定的转型之路
“洞中方十日,世上已千年。”赵小勇在应付订单的10年之间只干了一件事,而大芬村却发生了沧海桑田之变。新世纪之初,来自政府和民间的“两只手”对大芬村进行深度改造和产业引导。在村容村貌上,拆除雨棚、整顿村容、修整道路;在品质升级上,建成大芬美术馆、艺术广场。大芬村告别了野蛮生长的“草莽时代”。这也是大芬村狂飙突进的时代。2005年前后,全球油画市场70%左右的仿制画都出自大芬村,这里一跃成为全球闻名的“欧洲油画小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了高度依赖外贸出口的大芬村。为了扶持原创画家,大芬村为画家兴建了公共租赁住房,建成全国首个美术产业园区配套美术馆,专门辟出展厅免费举办大芬本土原创油画展览,携手中国美协举办一年一度的全国(大芬)中青年油画展,定期组织原创画家外出采风……而以赵小勇、周永久为代表的“非原创画匠”,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外贸订单断崖式下滑倒逼大芬村油画产业逐渐由出口转向内销,作为芸芸农民工画匠中的普通一员,赵小勇当然不能幸免。他抵消冲击的方法是盘下一间画廊,想把生意逐步转到线下。那时大芬村已盛名在外,成为世界各地游客来深旅游观光的目的地之一。
一天,有位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游客进店逛了一圈,显得很激动。翻译告诉赵小勇,他们误以为走进了梵高博物馆,从没见过一个画廊只经营一位画家的作品。原来,对方是个荷兰画商,想买赵小勇的画……这次合作一直延续到2015年。赵小勇说不清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知道继续做“行画”(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的油画工艺品)只有死路一条,但放着找上门的订单又不可能不接。
订单萎缩反而让周永久有更多时间琢磨自己的画。一天,回兰州就业的徒弟在QQ上发来一组照片:一株株硕大饱满的向日葵、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花海。周永久一下就被镇住了,仿佛见到了梵高向日葵的“真身”,他觉得有必要实地看看。于是,就在赵小勇还在为梵高故乡发来的订单忙得不可开交时,周永久已经置身于万亩向日葵花田之中,像梵高一样作画了。
物质与精神的临界点
画工们赤膊作画,是《中国梵高》里的经典一幕。余海波记得第一次走入赵小勇的世界,为这一景象而深深震撼,他觉得这个题材有极强的隐喻性。那几年,他每天都带上一二十个胶卷去大芬村,跟画工们终日厮混。时间一久,大家成了朋友,对他的拍摄熟视无睹,相互之间乃至披肝沥胆。
对于赵小勇来说,梵高如神明亦如鬼魅。他曾无数次向余海波讲述一个梦境:大芬村被笼罩在《星夜》一般瑰丽、奇幻的夜空之下,一个长着红色须发的男子在村子里游荡,每次都会经过他的画廊,然后用凌厉的目光打量他,冷不丁问道:“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了?”“我现在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他结结巴巴作答,刚想进一步交谈,梦就醒了。
“海波,你知道吗,我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了……舅舅骂我妈妈不让小孩上学,妈妈说家里没钱……”酒至半酣,赵小勇会瞬间“破防”,向余海波倾诉挥之不去的遗憾。他承认自己是幸运的,早早跟大芬村结缘,通过临摹梵高画作彻底改变了命运,然而至今仍是大师的影子、艺术圈的局外人。
而在周永久身上,类似的自我怀疑正在转化为自我变革。兰州写生,为他的画面注入了蓬勃生机。他甚至不再用画笔而改用画刀作画,油彩在画布上深厚堆垛,呈现出刀工的犀利洒脱和呼之欲出的立体感。除了描绘的主题,周永久在笔触、构图、神韵上都在摆脱梵高原作的限定。
“当然,比起现代艺术圈里那些标新立异的职业艺术家,他们往往是小心翼翼地在原作基础上进行创意性改动,他们的实验是羞涩的。”虽说如此,余海波不觉得画工和画家之间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任何艺术学习都会经历从模仿到创造的转化、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如果只想一味地临摹梵高画作,周永久没必要跑去西北,在向日葵花田中“闭关”3个月,赵小勇更不必跨越关山阻隔,到欧洲拜谒梵高故地。2014年,阿姆斯特丹的客户突然邀请赵小勇来荷兰,“看看梵高真迹,重温梵高历程。”于是,在余海波镜头的全程记录下,赵小勇的欧洲之旅终于成行,也便有了故事开篇一幕。

▲周永久(右)和他的梵高画。
晚了20年的“顿悟之旅”
博物馆广场是阿姆斯特丹最美的角落之一。作为昔日殖民帝国辉煌的见证,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汇聚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其正对面的那座现代风格建筑,就是赫赫有名的梵高博物馆。日复一日,如织的游人鱼贯而入又蜂拥而出,附近的纪念品商店自然成为受益者。在那里,人们可以花几欧元就能买到印有梵高画作的明信片,也可以花几十、几百欧元买到仿作。但游人们绝想不到,这些仿作竟出自一批中国农民工之手。
余海波把赵小勇的欧洲之行比作找寻之旅,先是在博物馆广场的纪念品商店找到了“价格”,又在梵高博物馆找到了“价值”。最让赵小勇失落的不是国际贸易差价对他的“剥削”,而是当他看到梵高真迹时所受到的触动。“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颜色有差别,”他自语道。感叹自己临摹了5万幅梵高,还不及一幅真迹——这种“不及”不仅仅是指价格,还道出了创作的无价。原创是一种从无到有、创世般的活动,与临摹、仿造不可同日而语。
在巴黎郊区的梵高墓前,赵小勇点燃了3根香烟,用这种“特别中国”的方式为梵高“上香”,完成了虽简陋却虔敬的仪式。在法国南部阿尔勒这个梵高生命中的最后一站,赵小勇找到了 “夜间咖啡馆”。他凭记忆当场临摹了那幅名作,引来无数路人围观喝彩。余海波说,赵小勇通过把自己跟伟大的梵高连接在一起,找寻存在的意义。
欧洲之行为赵小勇带来了顿悟式的启发,但他毕竟还要回到大芬村去面对更加复杂的现实。是延续临摹、仿造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原创的新路?出人意料的是,赵小勇提出想在中国建一座梵高复制品博物馆。这个主意看上去很“山寨”,余海波却认为有其可取之处:正大光明的高仿复制有别于以假乱真的赝品制作,前者是以谦卑的姿态承认原作的价值,在高冷的大师艺术与普罗大众的审美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中国梵高》讲述的故事也彻底改变了周永久的命运轨迹。2018年,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在飞机上看过这部纪录片后,随即到大芬村探访周永久,并买下十几幅作品。也是在这位华侨朋友的促成下,周永久有生第一次在槟城举办了个人展览,他的数十幅作品也大多以高价售出——梵高生前只卖出一幅作品,他没能用创作改变自己的生活,却机缘巧合地改变了100多年后一批中国画匠的生活。
作为《中国梵高》导演之一的余天琦是英国电影学博士,回国后在上海交大任教。在她看来,无论电影还是美术,“混圈子”都很重要。“像赵小勇、周永久这些人,读不了美术学院,也就进不了这个圈子,只能继续在纪念品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作品。当代艺术市场缺乏多元性且十分封闭,拒绝不同的目光和风格。大芬村有一种独特的艺术生态,包含着难以定义、激动人心的原创性,这本身就是对艺术圈的嘲讽。”


▲2016年,由余海波(下图)、余天琦联合执导的纪录片《中国梵高》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首映。
久矣,吾不复梦见梵高
“中国梵高”折射了激荡的全球化时代下大芬村画工群体的精神历程,而现实中大芬村却有着更加丰富、庞杂的生态。据张可介绍,大芬油画村现有画廊与艺术机构1800余家、知名企业60多家,村内聚集油画从业人员约8000人,加上周边社区从业人员共20000多人。如今的大芬,不仅仅是油画的大芬,各种艺术门类和业态都可以在这里和谐共存。装裱、配框、画材、物流等配套服务,以及艺术衍生品开发、油画体验、美术教育在整个产业链上彼此互补、生生不息。
文化学者、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认为,随着低廉的租金、人工成本红利消退,名画复制业开始向内地转移,“中国梵高”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已不复存在。在创新驱动、跨界融合的大背景下,大芬油画村只有重新校准自己在全球艺术产业新一轮创新发展中的定位,从单一的油画美术产业向大视觉、大文创方向转型,打造集艺术品创意生产、展示交易、文化交流、文旅融合于一体的高端平台,才能涅槃重生。
最近一次见赵小勇,他说已经很久没梦见梵高了,我想他梦中的星夜一定超出了那位大师的想象……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