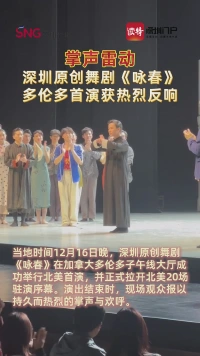张洁(1937年—2022年1月21日)
2022年1月21日,著名作家张洁在美国因病去世,享年85岁。
77岁时,张洁曾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办了她的个人油画展。在这场画展的开幕致辞上,张洁像是在“交代后事”一样做出告别——“张洁就此道别了。”还提到自己已留下遗嘱:“我死了以后,第一,不发讣告。第二,不遗体告别。第三,不开追悼会。也拜托朋友们,不要写纪念我的文章。”
仿佛正因为这份庄重的宣言,张洁逝世的消息一开始并未被大众所知悉。时隔半月甚至跨了个年,我们才得知,斯人已逝。
张洁是唯一一位获过两次茅盾文学奖的作家——1985年,凭借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2005年,又因长篇小说《无字》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她的创作生命力旺盛,自1978年以一篇《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初登文坛,张洁一直保持着创作,除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外,还有小说、散文、随笔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张洁文集》(4卷)《中国当代作家选集》《国际文学大奖得主自选文库》《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等10多部,游记文学集《域外游记》《一个中国女人在欧洲》等等。
面对这样几十年里笔耕不辍的作家,最好的缅怀就是不断去阅读,从作品中汲取某种意义上永恒的生命力。下文从张洁自选文集《我那风姿绰约的夜晚》选取5篇散文,有对朋友、亲人的怀念,也有对生命的感慨:“生命如四季……我怀着希望播种”。文中大多写的是时间不可逆转的流逝,而张洁却在其中留下对人世间的祝愿——“当我离开人世时,我曾爱过的一切,将一如未曾离开我时,一样的新鲜。”
《假如它能够说话……》
九点。应该开始每晚一小时的散步了。
老房子里,已经找不到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物,而我的思绪又总是执着在某一点上,这让我感到窒息、头痛欲裂,还因为我经常散步的那条路上,有许多往事可以追忆。
二十四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女学生的时候,就时常和女友在这条路上行走。我们曾逃离晚自习,去展览馆剧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观看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演出……还彼此鼓劲,强自镇定:“别怕,要是有人在剧场看到我们,他也不敢去告发,想必他也是逃学,不然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和我们相遇?”
毕业晚会我们都没有参加,二十年前的那个晚上,好像就在眼前。天气已经有些凉了,我在灰色裙子的外面,加了一件黑色短袖毛衣。似有似无的乐声从远处飘来,那时的路灯,还不像现在这样明亮,我们在那昏暗的路上走了很久,为即将到来的别离黯然神伤,发誓永志不忘,将来还要设法调动到同一个城市工作,永远生活在一起。好像我们永远不会长大,不会出嫁,也不会有各自的家。
从那一别,十五年过去,当我们重新聚首,我已经找不到昔日那个秀丽窈窕的影子,她像是嫁给了彼埃尔的、罗斯托夫家的娜塔莎,眼睛里只有奶瓶、尿布、丈夫和孩子。像个小母鸭一样,挺着丰满的胸脯,身后跟着三个胖得走起路来,不得不一摇一摆的小鸭子……
她已经不再想到我,也不再想到我们在这条路上做过的誓约。
我还不死心地提议,让我们再到这条路上走一走。不知她忘记了我的提议,还是忙着招呼孩子没有听见,而我也似乎明白了,已经消失的东西,不可追回。我们终于没有回到这条路上来,虽然这条路,距我居住的地方,不过一箭之遥。
哦,难道我们注定,终会从自己所爱的人的生活中消失吗?

没想到后来我的女儿上学,竟也走这条路。通向南北的两条柏油小路,还像我读书的时候一样,弯弯曲曲。两条路中间,夹着稀疏的小树林、草地和慢坡。慢坡上长着丁香、榆叶梅和蔷薇。春天,榆叶梅浓重的粉色,把这条路点染得多么热闹。到了傍晚,紫丁香忧郁的香味会更加浓郁……只是这几年,马路才修得这样平直和宽阔,但却没有了慢坡、草地、小树林子、丁香、蔷薇和榆叶梅。
女儿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只有十岁。平时在学校住宿,只有星期六才回家。每个星期天傍晚,我送她返回学校。她只管一个人在前面蹦蹦跳跳地跑着,或追赶一只蜻蜓,或采摘路旁的野花……什么也不懂得。但有时,也会说出令我流泪的话。八岁那年,她突然对我说:“妈妈,咱家什么也靠不上,只有靠我自己奋斗了。”
一个八岁的孩子!
是的,无可依靠。
那几年,就连日子也过得含辛茹苦,我从来舍不得花五分钱给自己买根冰棍,一条蓝布裤子,连着春、夏、秋、冬,夏天往瘦里缝一缝,冬天再拼接上两条蓝布,用来罩棉裤。几十岁的人了,却还像那些贪长的孩子,裤腿上总是接着两块颜色不同的裤脚……
现在,女儿已经成为十七岁的大姑娘,过了年该说十八了。每个周末我依旧送她,但已不复是保护她,倒好像是我在寻求她的庇护。
她那还没有被伤害人心的痛苦和消磨意志的幸福刻上皱纹的、宁静如圣母一样的面孔,像夏日正午的浓荫,覆盖着我。
我已经可以对她叙说这路上有过的往事。她对我说:“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不论是快乐或是痛苦。”
我多么愿意相信她。
我也曾和我至今仍在爱着,但已弃我而去的恋人,在这条路上往复。多少年来,我像收藏宝石和珍珠那样,珍藏着他对我说过的那些可爱的假话。而且,我知道,我还会继续珍藏下去,无论如何,那些假话也曾给我欢乐。

我一面走,一面仰望天空。这是一个晴朗的、没有月亮的夜晚,只有满天的寒星。据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星在天上,但天空在摇,星星也在摇,我无从分辨,哪一颗属于他,哪一颗又属于我。但想必它们相距得十分遥远,是永远不可能相遇的。
李白的诗句,涌上我的心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路,如同一个沉默而宽厚的老朋友,它深知我的梦想;理解我大大的,也是渺小的悲哀;谅解我的愚蠢和傻气;宽恕我大大小小的过失……哦,如果它能够说话!
今晚,我又在这路上走着,老棉鞋底唰唰地蹭着路面,听这脚步声,便知道这双脚累了,抬不动腿了。
汽车从我身旁驶过。很远、很远,还看得见红色的尾灯在闪烁,让我记起这是除夕之夜,是团聚的夜,难怪路上行人寥落。
两只脚,仍然不停地向前迈着。每迈前一步,便离过去更远,离未来更近。
我久已没有祝愿,但在这除夕之夜,我终应有所祝愿。祝一个简单而又不至破灭的愿:人常叹息花朵不能久留,而在记忆中它永不凋落。对于既往的一切,我愿只记着好的,忘记不好的。当我离开人世时,我曾爱过的一切,将一如未曾离开我时,一样的新鲜。

《我的四季》
生命如四季。
春天,在这片土地上,我用细瘦的胳膊,扶紧锈钝的犁。深埋在泥土里的树根、石块,磕绊着我的犁头,消耗着我成倍的力气。我汗流浃背、四肢颤抖,恨不得躺倒在那要我开垦的泥土地上。可我知道我没有权利逃避,上天在给予我生命的同时,也给予我了责任。
无须问为什么,也无须想有没有结果;不必感慨生命的艰辛,也不必自艾自怜命运的不济:为什么偏偏给了我这样一块不毛之地。只能咬紧牙关,闷着脑袋,拼却全身的力气,压到我的犁头上去,也不必期待有谁来代替,每个人都有一块必得由他自己耕种的土地。
我怀着希望播种,绝不比任何一个智者的希望谦卑。
每天,我凝望那撒下种子的土地,想象着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如同一个孕育着生命的母亲,期待着将要出生的婴儿。
干旱的夏日,我站在地头上,焦灼地望着南来的风吹来载雨的云。那是怎样的望眼欲穿?盼着盼着,有风吹过来了。但那风强劲了一些,把载雨的那片云吹过去了,吹到另一片土地上。我恨不得跳到天上,死死揪住那片云,求它给我一滴雨——那是怎样的痴心妄想?我终于明白,这妄想如同想要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于是不再妄想,而是上路去寻找泉水。
路上的艰辛不必细说,要说的是,找到了水源,却发现没有带上容器。过于简单和容易发热的头脑,造成过多少本可避免的过失——那并非不能,让人痛心的正在这里:并非不能。
我顿足、我懊恼、我哭泣,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有什么用?只得重新开始,这样浅显的经验,却需要比别人付出加倍的努力来记取。
我也曾眼睁睁地看着,在冰雹无情地摧残下,我那刚刚灌浆、远远没有长成的谷穗,如何在细弱的黍秆上挣扎,却无力挣脱生它、养它,又牢牢锁住它的土地,永远没有尝受过成熟的滋味,便夭折了。
我张开双臂,愿将全身的皮肉,碾成一张大幕,为我的青苗遮挡冰雹和狂风暴雨……但过分的善良,可能就是愚昧,厄运只能将弱者淘汰,即使我为它们挡过这次灾难,它们也会在另一次灾难里沉没,而强者却会留下,继续走完自己的人生。

秋天,我和别人一样收获,望着我那干瘪的谷粒,心里涌起又苦又甜的欢乐,并不因自己的谷粒比别人的干瘪而灰心丧气。我把它们捧在手里,贴近心窝,仿佛那是新诞生的一个我。
富有而善良的邻人,感叹我收获的微少,我却疯人一样地大笑,在这笑声里,我知道我已成熟。我已有了别一种量具,它不量谷物只量感受。我的邻人不知,和谷物同时收获的还有人生。
我已爱过、恨过、笑过、哭过、体味过、彻悟过……细想起来,便知晴日多于阴雨,收获多于劳作,只要认真地活过、无愧地付出过,谁也无权耻笑我是入不敷出的傻瓜,也不必用他的尺度来衡量我值得或是不值得。
到了冬日,那生命的黄昏,难道就没有别的可做?只是隔着窗子,看飘落的雪花、落寞的田野,或点数枝丫上的寒鸦?
不,也许可以在炉子里加几块木柴,让屋子更加温暖,在那火炉旁,我将冷静地检点自己,为什么失败;做错过什么;是否还欠别人什么……但愿只是别人欠我。

《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到了后来,你总是要生病的。
不光头疼,浑身骨头都疼,翻过来、掉过去怎么躺都不舒服,连满嘴的牙根儿也跟着一起疼。
舌苔白厚、不思茶饭;高烧得天昏地暗、眼冒金星;满嘴燎泡、浑身没劲儿……你甚至觉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去好。
这时,你首先想起的是母亲。想起小时候生病,母亲的手掌,一下下摩挲着你滚烫的额头的光景。你浑身的不适、一切的病痛,似乎都顺着她一下下的摩挲排走了。
好像你那时不论生什么大病,也不像现在这样难熬,因为有母亲替你扛着病痛。不管你的病后来是怎么好的,你最后记住的,都是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的母亲,和母亲那双生着老茧、在你额上一下下摩挲的手。
你也不由得想起母亲给你做的那碗热汤面。当你长大以后,有了出息,山珍海味成了餐桌上的家常,便很少再想起那碗热汤面。可是等到你重病在身,而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时候,你觉得母亲亲自擀的那碗不过放了一把菠菜、一把黄豆芽,打了一个蛋花的热汤面,才是你这辈子吃过的最美的美味。
于是你不觉地向上仰起额头,似乎母亲的手掌,即刻会像小时候那样,摩挲过你的额头;你费劲地往干疼的、急需沁润的喉咙里,咽下一口难成气候的唾液……此时此刻,你最想吃的,可不就是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
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
你转而思念情人,盼望此时此刻他能将你搂在怀里,让他的温存和爱抚,将你的病痛消解。

他曾如此地爱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舍难分,要星星不给你摘月亮,可你真是病到再也无法为他制造欢爱的时候,不要说是摘星星或是摘月亮,即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也不曾。
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洗手做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又不贵的小菜,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外卖似乎也不难,可是你的期盼落了空。不要说一个小菜,就是为你烧一壶白开水,也如《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
你退求其次再其次:什么都不说了,打个电话安慰安慰也行。电话机或手机就在他的手边,真正的举手之劳,可连这个电话也没有。当初每天一个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可不就是一场梦。
…………
最后你明白了,你其实没人可以指望。你一旦明白这一点,反倒不再流泪,而是豁达一笑。于是你不再空想母亲的热汤面,也不再期待情人的怀抱,并且死心塌地地关闭了电话。
你神闲气定地望着太阳投在被罩上的影子,从东往西地渐渐移动,在太阳的影子里,独自慢慢消融着这份病痛。
你最终能够挣扎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自来水龙头下接杯凉水,喝得咕咚咕咚,如在五星级饭店喝矿泉水。你惊奇地注视着这杯凉水,发现它一样可以解渴。
饿急了眼,还会在冰箱里搜出一块干面包,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照样堂堂皇皇地把它硬吃下去。
在吃过这样一块面包,喝过这样一杯水后,你大概不会再沉湎于浮华,即便有时你还得沉浮其中,也只不过是难免而清醒的酬酢。
自此以后,你再不怕面对自己上街、自己下馆子、自己乐、自己哭、自己应对天塌地陷……你会感到,“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可能比和一个什么人摽在一起更好。
这时候你才算真正的长大,虽然这一年,你可能已经七十岁了。
《我为什么失去了你》
十八岁的时候仇恨自己的脸蛋,为什么像奥尔珈(与下文丹吉亚娜同为普希金小说《欧根·奥涅金》中的人物)那样红得像个村妇,而不能拥有丹吉亚娜的苍白和忧郁!不理解上两个世纪的英国女人,在异性到来之前为什么捏自己的脸蛋,使之现出些许的颜色。而现在对着自己阴沉而不是忧郁、不仅苍白而且涩青的脸色想,是否肝功能不正常;
十八岁的时候为买不起流行穿戴而烦恼,认为男人对我没有兴趣是因为我的不“流行”。而今却视“流行”为不入流之大忌,唯恐躲之不及地躲避着“流行”;
十八岁的时候为穷困而窘迫、害臊。如今常在晚上八点以后,穿着最上不得台面的衣服,去五星级的国贸大饭店,买打折的面包。那里有特别的师傅、特别的面粉、特别的做法、特别的香料。为求品质上乘、口味新鲜,二十点过后就半价销售,第二天上的货,绝对是刚从烤炉里出来的。一天晚上早到三十分钟,毫不尴尬地对售货小姐凯瑟琳说:“先放在这儿,等我到下面超市买些东西,回来就是八点了。”我们现在成了老交情,她远远看见我,就对我发出明媚的微笑;
十八岁的时候,喜欢每一个party,更希望自己是注意的中心。现在见了party尽量躲,更怕谁在“惦记”我;

十八岁的时候豪情满怀、义不容辞地为朋友两肋插刀。现在知道回问自己一句:人家拿你当过朋友吗?而后哑然一笑;
十八岁的时候为第一根白发惊慌失措,想到有一天会死去而害怕得睡不着觉。现在感谢满头白发替我说尽不能尽说的心情,想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天,就像想到一位可以信赖却姗姗来迟的朋友;
十八岁的时候铁锭吃下去都能消化,面对花花世界却囊中羞涩。现在却如华老栓那样,时不时按按口袋“硬硬的还在”,眼瞅着花花世界却享受不动了,哪怕一只烧饼也得细嚼慢咽,稍有闪失就得满世界找三九胃泰;
十八岁的时候喜欢背诵普希金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心急,阴暗的日子总会过去……”现在只要有人张嘴刚发出一声“啊——”就浑身发冷、起鸡皮疙瘩,除了为朋友捧场,从不去听诗歌朗诵会;
十八岁的时候渴望爱情,愿意爱人也愿意被人爱。现在知道“世上只有妈妈好”,如果能够重活一遍,是不是会做周末情人不好说(如果合适的情人那么好找,也就不只“世上只有妈妈好”),但肯定会买个精子做单身妈妈;
十八岁的时候相信的事情很多。现在相信的事情已经屈指可数;
十八岁的时候非常怕鬼。现在知道鬼是没有的,就像没有钱,面包也不会有的一样千真万确;
十八岁的时候就怕看人家的白眼,讨好他人更是一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现在你以为你是谁?鄙人就是这个样儿,你的眼睛是黑是白,跟我有什么关系?善待某人仅仅因为那个人的可爱,而不是因为那个人对我有什么用;
十八岁的时候“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样腐朽地对待每个许诺、每个约定,为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的人之常情而伤心、苦恼、气愤、失眠、百思不得其解,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地等到不能再等的时候……现在,轻蔑地笑笑,还你一个“看不起”,下次不再跟你玩了行不行;

十八岁的时候明知被人盘剥你的青春、你的心智、你的肉体、你的钱财……却不好意思说“不”,也就怪不得被人盘剥之后,又一脚踹入阴沟。而成名之后,连被你下岗的保姆都会对外宣称,她是你的妹妹、侄女、外甥女……更因为可以说出你不喜欢炒青菜里放酱油而证据确凿。有些男人,甚至像阿Q那样声称“当初我还睡过她呢”,跟着也就不费吹灰之力,一夜蹿红;
对名人死后如雨后春笋般的文章《我与名人×××》,从来不甚恭敬。甚至对朋友说,我死之前应该开列一份清单,有过几个丈夫、几个情人、几个私生子、几个兄弟姐妹、几个朋友……特别是几个朋友,省得我死了以后再冒出什么什么,拿我再赚点什么什么。朋友说,那也没用,人家该怎么赚还怎么赚,反正死无对证了。可也是,即便活着时,人家要是黑上了你,你又能对证什么;
十八岁的时候想象回光返照之时,身旁会簇拥着难舍难割的亲友。现在留下的遗嘱是不发丧、不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如有可能,顶好像只老猫那样,知道结尾将近,马上离家出走,找个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独自享用最后的安宁。老猫对我说,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句话得留到那个时候自己说:“再也没有人可以打搅我了”;
…………
一个人竟有那许多说不完的、十八岁的不了情……

张洁画作
《就此道别》
——张洁画展开幕致词
三十多年前,冰心先生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在我们这些老朋友之间,现在是见一面少一面了。”而现在,轮到我来说这句话了。我们的文字中,常常会用到“永远”这个词儿,但永远是不可能的。长江后浪推前浪,花开花落自有时,适时而退,才是道理。
我一直盼望有一个正式的场合,让我郑重地说出这些话,但这个机会实在难以得到。非常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当然现代文学馆的后面其实是中国作家协会,还有我的“娘家”北京市作家协会,为我组织了这个画展,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表明我的心意。说是画展,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告别演出”。
除了感谢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我的“娘家”北京作协支持外,我还非常非常惭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小母亲就告诉我,对所有人的给予都应该回报,我也是努力这样做的。但有些给予真是无法回报。其实我很想跟我母亲讨论这个问题:您觉得所有的给予都能回报吗?有些给予其实是回报不了的。这就是我面对那些无法回报的给予时,常常会非常惭愧的缘故。于是这些无法回报的给予,就成了我的心债,让我的心不得安宁。今年春天,我把这些心债写成一篇稿子,但被退稿了,这是我今生第二次被退稿。我也知道它确实难以发表,因为涉及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背景。可是没关系,这些事都记录在我的日记里,我想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它一定会得到发表的机会。

张洁画作
我这辈子是连滚带爬、踉踉跄跄地走过来的,从少年时代起,当我刚能提动半桶水的时候,就得做一个男人,又得做一个女人,成长之后又要担负起“做人”的担子,真累得精疲力竭。可是这一次画展——也可能是我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承办人却没有让我花一分力气,没有让我操一分心思,没有让我动一根手指头……一个累了一辈子、已然精疲力竭的人,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心里是什么感受?那真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此外,我还要感谢两个具体办事儿的人。一个是兴安,说老实话,兴安这个家伙不太靠谱,但是他为这次画展做的画册相当漂亮,还为了画展前前后后地奔波。另一个是我的邻居任月华女士,我不在京期间,许多细枝末节,画册的清单、交接,都由她代劳,和现代文学馆的计蕾主任商量办理。很多人认为我是个非常各色、不好相处的人,可是我们邻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儿矛盾。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画,我很高兴;如果你们不喜欢,臭骂一顿,我也不在意。我现在的状态是云淡风轻。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我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希望我只记得那些好的,忘记那些不好的。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太不容易了。就在七八年前,睡到半夜,我还会“噌”的一下坐起来,对着黑暗大骂一句,然后再“嗵”的一声躺下。可我现在真的已经放手。我从不相信任何宗教,但我相信一些奇怪的事。我常常会坐在一棵树下的长椅子上,那个角落里的来风,没有定向,我觉得那从不同方向吹来的风,把有关伤害、侮辱、造谣、污蔑等等不好的回忆,渐渐地吹走了,只留下了有关朋友的爱、温暖、关切、帮助等等的回忆。我还认识了一只叫Lucy的小狗,它的眼睛干净极了,经常歪着小脑袋,长久地注视着我。当它用那么干净的眼睛注视我的时候,我真觉得是在洗涤我的灵魂。我非常感谢命运在我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给了我这份大礼,让我只记得好的而忘掉那些不好的回忆。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我在一家很好的律师事务所留下了一份遗嘱,我死了以后,第一,不发讣告。第二,不遗体告别。第三,不开追悼会。也拜托朋友们,不要写纪念我的文章。只要心里记得,曾经有过张洁这么一个朋友也就够了。至于从来就没停止过诅咒我的人,就请继续骂吧,如果我能在排遣你的某种心理方面发挥点作用,也是我的一份贡献。
再次感谢各位来宾,张洁就此道别了。
2014年10月23日
(原标题《“张洁就此道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