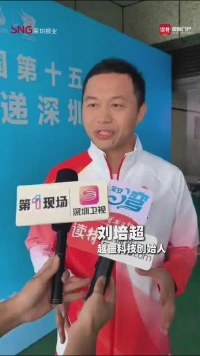马立明
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这两个概念遭到有意或无意地混淆。所谓跨文化传播,指的是发生在不同文化介质中的传播行为,比如美国嬉皮士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这种传播过程可理解为全球化的产物,是全球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时出现的现象,它是温和的、诗意的、富有弹性的。但是国际传播则有所不同,它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环,是某个国际政治行为体的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活动。某种程度上,它相当于一次文化上的行军。
国际传播带有更多的策略性与目的性。自20世纪80年代起,为什么我们能接触到大量美国小说、电影、音乐、体育,但却接触不到加纳、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任何文化产品?原因之一是美国的文化产业远远比加纳等国家强大,但另一个原因更应该值得重视:美国的文化产业是有策略性的,除了资本驱动外,还有政治的有意促动。这是美国大外交政策中的重要一环。在“文化帝国主义”的主导下,美国的国际传播也是一种带有价值观导向的行为,向非西方世界源源不断进行意识形态输出。
当我们讨论国际传播时,不能将它理解为“去政治化”的存在。好莱坞电影进入中国市场时,除了研究过如何技巧性打入中国市场(比如使用华裔演员),更重要的是带有美国核心价值观。有学者将其称为森林里的一枚果实,文化是外部的“果肉”,而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果核”。这种传播模式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与政治联合驱动的。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化”:令全世界的青年都在好莱坞、漫威、麦当劳、NBA的渲染下成长,从而变成美国文化的天然消费者。这种策略内嵌于美国的传播策略之中,伴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在各个维度上充分言说。正如福柯所言,我们进入到一个规训和控制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文化产品在对受众进行有针对性地“内化”,受众在不知不觉间完成了思想上的形塑,从而失去了文化主体性。
如果对每个案例进行剖析,结果会让我们感到丧气。多个打着理想主义的西方媒体、NGO、基金会,他们都打着普世价值或全球主义的情怀来到第三世界国家,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帮助”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保护环境、保护人权、新闻自由等)。但是,如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所言,“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目的是维持这样的中心—边缘的结构”,让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这显然更符合西方国家的核心利益。这些西方媒体、NGO、基金会,有可能是带有某种使命的“特洛伊木马”。
当下的国际社会,已经告别全球化时代的理想主义,从而进入到现实主义的维度之中。更加强调主权、民族、国家意志的现实主义范式,对国际社会的现状更具有解释力。因此,国际传播也可以理解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权力支配方式,强国对弱国不仅仅在政治、经济、科技上处于支配地位,在文化上依然享有极大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国际传播不像跨文化传播,它并不是茶话会,而是某种气氛激烈的话语博弈。
当下,中美关系仍然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我们也见到,美国使用他们的话语霸权,在对中国进行着抹黑与诋毁。尽管当下局面也有好转的可能,我们也不会放弃建设性的努力,但低估形势的复杂性,这一点恐怕并不明智。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显然要放在中美关系的大局中考虑。
作者马立明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