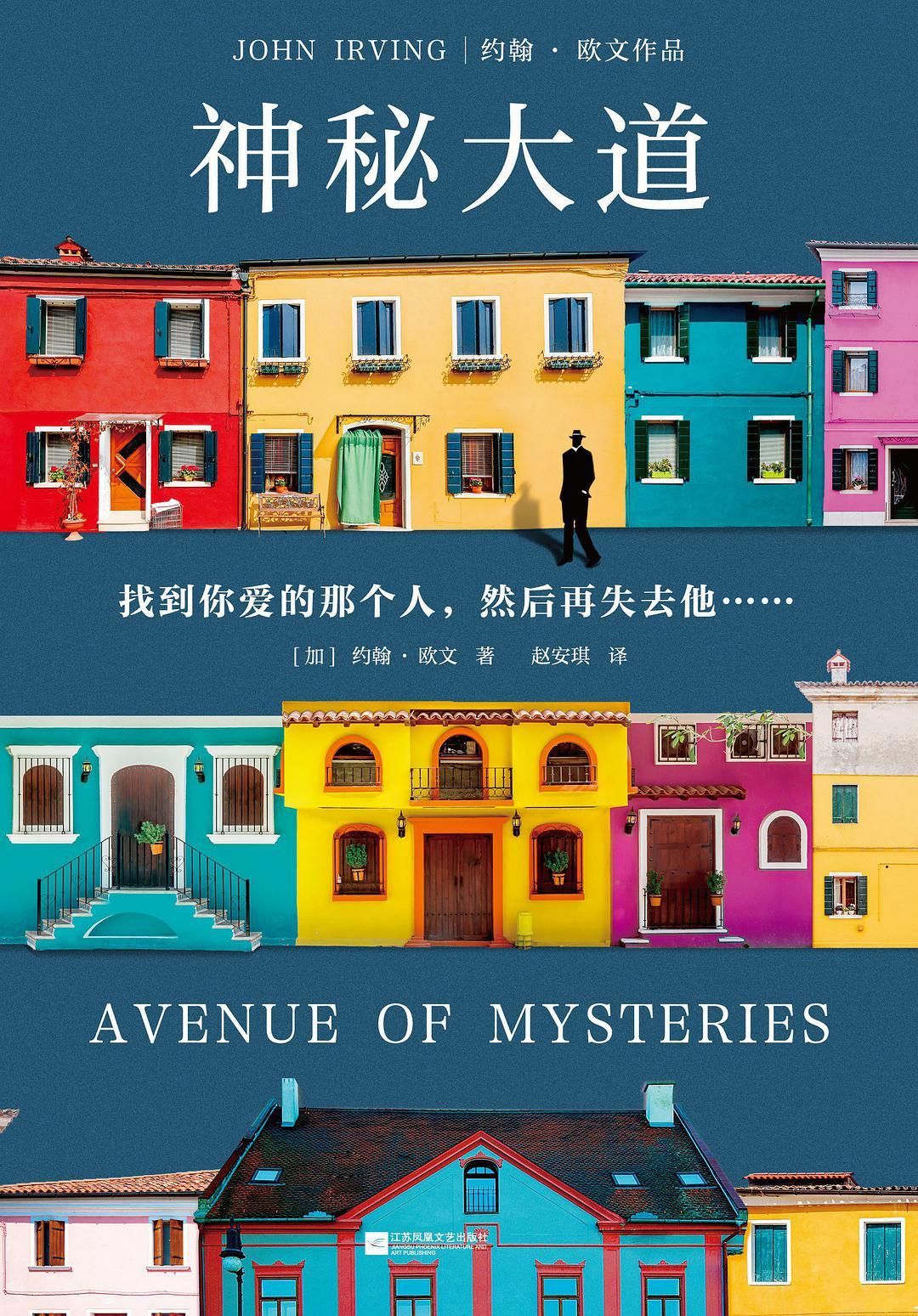说起索南才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9年《作品》杂志曾一次性发出他五篇小说,外加一个对谈和评论。这应该是史无前例的推荐力度,可见编辑对其作品的喜爱程度。2020年,索南才让的中篇小说《荒原上》进入收获排行榜,这也是难得的荣誉,瞬间备受关注。记得去年读《荒原上》时,印象最深刻的是小说中人物金嘎的死亡。这死亡是同伴确罗那不知深浅的日常调笑所导致的,这情节使我想到索南才让在《作品》杂志发出的对谈文章里曾自述说自己是“坏孩子”。那一刻,我脑回路想到:索南才让会不会就是确罗这样的坏孩子?

《荒原上》索南才让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7月
关于“坏孩子”,索南才让有一段解释:“孩子的坏其实挺可怕的,你想想,一个孩子冷漠地去做一件坏事,而且很可能是一件危及别人生命的坏事,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甚至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是单纯地为了好玩去做,而且也没有对后果的认知,这多可怕?”在《荒原上》里,确罗当众“揭发”金嘎的自慰行为,纯粹就是因为好玩,他并没有想太多,不会觉得自己的“揭发”会带来什么后果。像确罗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成长记忆里其实非常普遍。一些爱开玩笑的同伴或者长辈总喜欢把我们不愿示人的事情抖露出来,作为日常消遣供大家欢乐。这类行为对于很多心理承受能力好的人而言,尴尬和不快很快就会过去。但对于一些心理比较敏感相对脆弱的人而言,这种玩笑很可能留下长时间的心理阴影,甚至如《荒原上》里的金嘎一样走向自杀。
索南才让当年是不是《荒原上》中确罗这样的坏孩子,这并不重要。从“坏孩子”视角来看索南才让的写作,可以抵达一些相对隐秘的精神话题。金嘎的死是《荒原上》这个中篇故事的高潮所在,前面的故事似乎都是为它而来,都可视作一种叙事铺垫。金嘎死后,小说也进入了尾声。如此理解《荒原上》自然是简单化了,毕竟小说还有更重要的“荒原”主题,还有“我”和银措那因文学通信而生成的纯真情感,但作家让这一因“坏孩子”而导致的死亡情节作为叙事刺点,似乎说明“荒原”之所以为“荒”,并非老鼠/鼠疫肆虐,而是人“坏”了。小说中,该消灭的老鼠没有给人带来什么灾祸,反而是灭老鼠的人在“相互伤害”,归根结底还是人祸。
索南才让只是在写“坏孩子”吗?如果这一主题只是《荒原上》这一篇的倾向,或许还不值得着重探讨。但读完索南才让最新小说集《荒原上》,感觉到其中很多篇都是围绕“坏孩子”而展开。比如在《在辛哈那登》一篇,开头就是母亲回光返照之际给“我”的叮嘱:“第一,不要闯祸了!第二,再也不要闯祸了!!第三,照顾好你阿爸!!!”可见,“我”在母亲眼里是个经常闯祸的“坏孩子”。小说没交代“我”曾经闯过多少祸,但小说最后“我”找到有新的女人、安了新家的阿爸时,“我”对阿爸说话时的那种冷嘲热讽,像极了《荒原上》确罗的日常作风。还如《德州商店》里的贝子、马兽医,包括叙事人罗布藏对真假父亲的直接质疑,习惯于口无遮拦,传布着一些可能伤害人心、破坏家庭的“流言蜚语”。这种热衷于打听、传播他人隐私的行为,也与确罗形象遥相呼应。
“坏孩子”形象最突出的,要属《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里面的三个青年莫属。女朋友卢晓霞来草原找我,我给出的车站是张口而来的地名,也不安约定时间去车站接她。到家后我和卢晓霞的对话也是较劲着使坏,这“坏”有一半是调情,一半是较真。谁在调情、何时较真,这情绪也随时转换着。最后卢晓霞受不了我的较真,随随便便地找上了我的朋友、她有一面之缘的申登。这种随意惹怒了我,我宰了一头羊要为卢晓霞送行。卢晓霞好奇如何宰羊,灌血肠时被吓晕,醒来后闹着要离开,不再吃我特意为她准备的羊肉,并且带着怨毒似地说以后再也不吃肉了,这种随意再次激怒了我。最后,我强行送卢晓霞去车站,但没有在车站停下,又强行载着她去看湖,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表达了“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卢晓霞的随意和我的较真,跟《荒原上》确罗的无良与金嘎的决绝,难道不是异曲同工?
索南才让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坏孩子”?坏孩子并不恶,“坏”只是不善,但没有直接抵达恶,只有在恶的后果如金嘎的死亡事件发生后,“坏”才从良知感层面通往了恶,但也不是法律层面判定的罪恶。索南才让笔下的确罗等众多坏孩子,他们并不是恶人形象,他们只是无知、无良与无德。草原上如此多的“坏孩子”,这个草原能不沦为荒原吗?“坏孩子”是作家把大草原置换为大荒原的文学渠道。写“坏孩子”,也就是写人。这些青年的“坏”之所以为“坏”,背后是作家对草原青年人群的精神诊断。确罗为何这么热衷于开玩笑?这不是一种性格使然,而是无知在作祟,他虐待老鼠尸体是对自然、对生命毫无敬畏感的表现。索南才让笔下的众多青年,确罗、金嘎、申登等等,普遍都不识字,只对女人感兴趣,内心世界空洞无比,他们对开玩笑、对捉弄他人的热衷,也是缘于这种精神的荒芜。
人心的荒凉才是真正的荒原。索南才让对人心、对精神问题如此关注,这也解释了为何其小说要直接表现文学、写作和阅读的力量。如《荒原上》喜欢阅读的“我”,能够通过教人识字赚钱,能够发挥讲故事的能力赢得尊重,还能够写信/写作追到其他人无法接近的女孩,获得一段浪漫的爱情。文学在草原世界还有这么大的魅力,这种故事设计看似滑稽,实则意味深长——草原需要文学滋养,荒原需要精神救赎。总而言之,索南才让不像传统意义上热衷于写景观、亮情怀的草原作家,围绕着“坏孩子”而来的文学虚构,内涵着他对于当代草原青年精神荒凉的诊断与批判。让荒原复归草原,“坏孩子”需要成为“好孩子”。
编辑 贺曦 审读 刘春生 审核 李林夕 郑蔚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