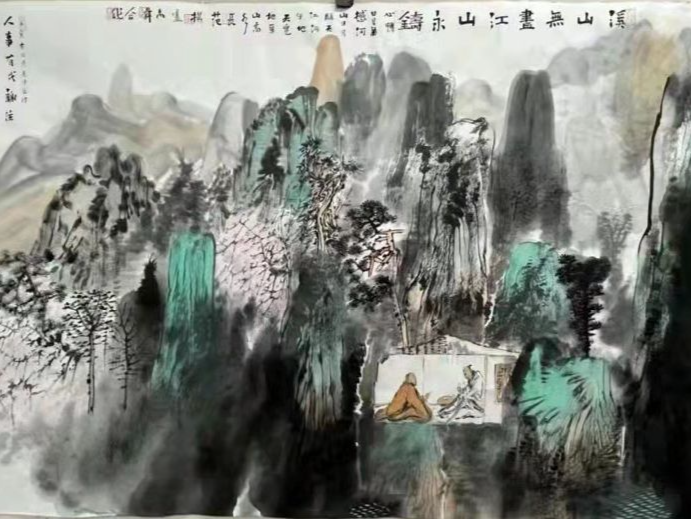无尽藏(第35集)
在徐铉奉太宗皇帝敕编撰的十二卷本《江南录》中,耿先生事迹被写入“方术传”。徐铉在《耿炼师》一节中有如此这般的描述:“耿先生鹤发鸟爪,姿首妖冶,尝着碧霞帔,飘然若世外人,世人莫测其由来。然晦迹混俗,素以道术修炼为事,且能拘制鬼魅,其术不常发扬于外,遇事则应,黯然而彰。尝雪夜拥炉,索金盆贮雪,又令人握雪成锭,投诸火中,片刻徐举出之,皆成白金,而指痕犹在。……”
徐铉笔下的耿先生俨然方外异人,而令人费解之处在于,徐铉对其世间真人的一面竟不着一字。南唐寖灭,徐铉以降臣之身追录前尘旧事,虽忘远取近,亦未免过于疏略。不干时忌,不涉隐曲,那部《江南录》不过是他的一番呓语。明哲世故如徐铉,其实是有意为之。今朝的史官遵奉的自是今朝的官家,身为降臣而为旧朝修史,他们聊可追记的亦只是风花雪月的余韵,他们惟恐因触忌而得罪。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徐铉写耿先生尽隐其侠风,写朱紫薇则惟彰其官德。朱紫薇虽为书法大家,但却并非博识高才之辈,与韩徐等饱学鸿儒相比,他的诗文实也无足称道,徐铉乃备述侈饰其尽忠职守事。朱紫薇清慎明著,克尽厥职,徐铉将其列入“循吏传”。如此作史方能投新主所好,惟因历朝君王无不倚重这等辅臣和循吏。所谓正心诚意,所谓修身齐家,终来不过维系在一个官运上。朱铣三世寒微,端赖合族人积垫,方有一朝登入龙门,而家族之荣枯亦维系于他一人。孤身在外为官,祖地却有合族百口人靠他照拂,朱铣断不敢少容松懈,亦不敢有半点闪失。名为济世拯民,实是为食禄养家。盖因动辄得罪,百慎一疏,即或有诛夷九族之祸。如此便有徐铉所言:“博练政体,兢兢自保。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徐铉笔下的朱紫薇足可为天下榜样,然对于朱紫薇“忠至灭身”的真实情由,徐铉却语焉不详,仅以寥寥数语带过:“铣率兵剿贼于玄武,不幸为贼所虏,或传贼以化药解尸,身首遂失其下落。”
我却知晓朱紫薇身首之下落。他的尸身并未被化解。尸解即可成仙,朱紫薇实无这福分。我也知晓朱紫薇以身殉职的实情。徐铉的《江南录》为新朝君主所嘉纳,太宗皇帝亦将其视作南唐一朝的官修正史。我却深知这位史官所隐蔽的真相。《江南录》付梓时他尚在人世,我也与他略有过往,但我强使自己钳口不言。我甚至强使自己放弃质疑他的冲动:开宝六年那个中秋,是谁向朱紫薇密告了我的行迹?
那天清晨父亲被拘之后,我最先求助的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徐尚书。而在此之后,便有两位画师在我抵达之前遇害。我在舍利塔前偶遇耿先生,她以那样一种闪烁之辞告诫我勿求他人,那时她已知我去过妙因寺边的徐府。
深稳练达的徐铉,他也隐蔽了那场皇宫灾变的实情。在他那部钦定传世的史录中,那场灾变只有轻描淡写的几个字:宫禁失火。
而我分明是在那火光中看到了一种宿命。那正是朱紫薇舍生忘死而必欲掩盖的真相。朱紫薇以一己之死保全合族百十口,那是足可彪炳史册的至孝。天下杜口,以言为讳。身为主控舆情的重臣,朱紫薇秉心贞亮,查秘籍,禁谣传,亦可谓防民防川,守土尽责。国主追赠他的谥号是“文忠”。
徐铉虽在《江南录》中将朱紫薇归入“循吏传”,却又誉其为“烈士”。
世道沉沦,人心已是不可收拾。忠孝两全者稀有,忠孝复又忠烈,朱紫薇不枉徐尚书笔墨!而我决意保持缄默。我虽念其可叹,却也知其可悲。朱紫薇至死都未能见识那真相。
那真相亦非他以烈士之死所能掩没。
马车在清冷的官道上疾行,小长老在驭座上执杖开路。寂寥的夜色中不见人影,只有几条野狗在觅食,又有人家的孩子在啼哭。啼哭声从长干里那边传来。长干里曾经有座长干寺,传说那寺塔中供奉有佛顶真骨舍利子,如今那地带却只有一片粪秽遍地的民居。那粪秽之下会有一个地宫么?那地宫中会有怎样的秘藏?我情愿国主不复他求,情愿他所要的就是我眼前这宝匣。
车过长干桥,那暗处忽然传来一声哀叹:“老天爷!这可叫人咋活啊!”
前方就是那重楼高耸的朱雀门。
“天使回宫,速速开门放行!”那车夫学着官腔吆喝。
我撩起窗帷仰望谯楼上的大鼓,此刻无人擂鼓。我也不想听到那催命的鼓声。
掖门缓缓开启,守卒在旁拱手迎候。小长老合掌颔首,守卒向他交还铜符。马车顺畅地穿过这门券。
城市仍在沉睡中。车过朱雀桥,我朝不远处的太学和贡院望一眼,也朝那乌衣巷望一眼。前方即是笔直的御道。御道的两侧是散从官营和民宅,也有鳞次栉比的坊市,有鸡行、米店和油坊,有酒肆、茶社和药铺,也有花行、丝行和银行。雨后的御道不见积水,砖铺的路面泛着幽光。
车厢在微微颤动。我与耿先生相对而坐,宝匣就放置在两人之间的金漆方案上。车厢如此狭小,我与她之间却似隔着遥远的距离。那个拥抱的感觉早已消失,那只是瞬间的温情。此时此刻,她的神态又复归于那惯常的冷淡。我已说出自己的好些个疑问,而她只以简短的话语作答。岂只是冷淡,这简直就是冷若冰霜了。这问答的间隔便有难堪的静默,马车正在穿过夜色,夜色也是这般的静默。这静默令我感到压迫。我不时地撩起窗帷望着街景,而她也不时地瞄一眼宝匣。宝匣虽有些沉重,匣壁却未必很厚实。这梅芯锁却是异常坚固,我不知谁会有锁匙开启它。
“看好它,或许你就是下一位护法了。”
她低声说出这句话,眼睛并不看我,我却能感觉到她眼神中的阴影,隐约闪现的阴影。我的头皮便立时有些发紧。
“可我……我都不知这是何物……”
“你能找到它,你也就配得到它。”
“我不要得到它。这是我父亲的秘藏。”
“他们也是为防万一。”
我最怕这万一的事情发生。我一时语塞,不知能否以这宝匣换回父亲,也不知该如何说话。她也不再言语。她侧身望着窗外。在这幽暗的车厢里,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有那张苍白冰冷的脸在颤动。
如此难堪的静默,不再有视线的交会,她甚至也不再有那讥讽的冷笑。她说我配得这秘藏,言下之意即是说,她自己早已不被信任,甚或可以说,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敌人。我深知自己仍处在她的掌控中,假使她愿意,她随时可以抢走这宝匣,也随时可以取走我这条小命。虽有这番遇合,我却依然难以辨清她的本相。这昏暗的车厢在晃动,而与我对坐的似乎只是一个人影,只是一袭长发和长袍。
她曾是韩熙载和我父亲的同道,后来她却成了朱紫薇的情人。我亲眼看见樊若水掐死了王屋山,樊若水却说郎县令和陈博士是凶手。大司徒既与王屋山有奸情,却又对其死因不予深究,而舒雅和李家明也是形迹可疑。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勾当?
我正这样想着,就见她撩动一下长发说:“舒雅宣州人,李家明庐州人,樊若水池州人,张洎滁州人,小长老淮北人。”
我蓦然一震。如梦忽醒,那确是无以名状的惊悸!那一刻我现出的是怎样的一副蠢相!她这读心的神通是从何而来?
“是有那么一党。” 她似是在喃喃自语。
“淮党。”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朝官中不少是淮党,这几个又为这宝物而结拜。”
“既已结拜,如何又有这番螳螂捕蝉?”
“小人结党总会如此,那女魔头不是说灭就灭么?”
“王家少妇王屋山?”
“你可知她胃口有多大?”
“学生请愿,也揭发王屋山独揽天下铜矿,就是倚仗大司徒的势要……”
“由是大司徒才要除掉她!她手里把柄多得是,你也知淮党拜盟是在哪?”
“风月楼?樊若水却跟她看似并不熟……”
“这倒不然,他们也是早就有过首尾的,那婊子只是做戏给你看。”
“可樊若水也还是灭了她……”
“那就只怪她多嘴了,其实也是难怪,不过是那么个贱坯……那钓鱼的事也只是樊若水自知。”
“可那李家妹的事又怎么说?”
“你想说是我灭了那粉头。”
“正是!你却将她移尸风月楼……是恐她招人去往藏书楼……”
“你也还不算笨。”我能听出她这语气中讥嘲的意味,但我确也有自知之明,我知自己并非蠢人,我确是说破了她的隐秘。
“你道我何以要有这番事?”
“你以为那里有秘藏。”
“才说你还不笨!其实是因你在那里头,就在那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