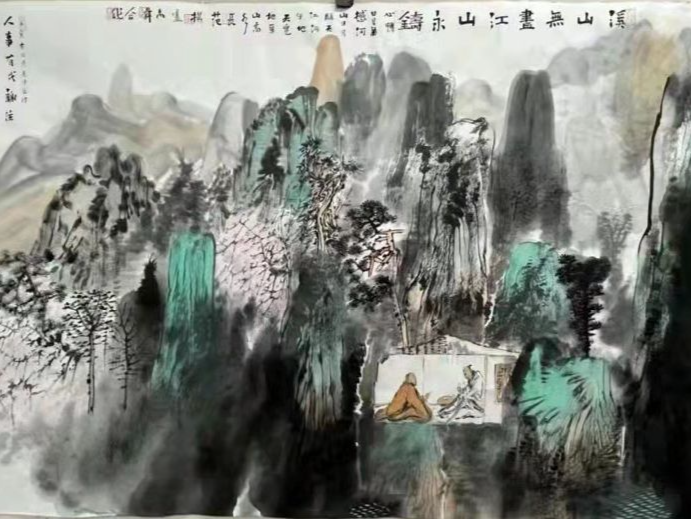无尽藏(第29集)
我再次走过这长长的廊桥。前无阻碍,后无跟踪,桥下亦无暗伏。我时而回望那湖山,那片风景渐渐模糊起来。
无尽藏的大火业已熄灭,那虚墟上却依然人影杂沓。有人在朝那片焦土泼水,也有人拿长钩在瓦砾中抓刨。又有几个在争抢中扭打,我听不见他们的吵嚷声。
火起火灭,仅在一个时辰间。灯笼已被鬼风吹灭。那盏命灯究竟能燃到几时?
那位女道人行踪飘忽,言词闪烁,我虽对她深怀疑惧,却也难以否认她说的是实情。国主佞佛已是走火入魔,传闻他每日与小周后僧衣僧帽,课诵佛经,跪拜顿首已致额结瘤赘。国主惑而不返,纲纪为之坏乱。每有死刑奏牍,国主即以“命灯”决断。传闻国主对佛燃灯,每以达旦为验,灯灭则依律处斩,灯不灭则宽贷免死。总有富商显贵犯法者厚赂内官,内官窃续膏油,犯法者遂获免罪。我不指望宫中会有哪位好心内官为那命灯续油,我只盼佛祖慈心慧眼,让其身前的那盏油灯燃到天明。
我要在天明前面见国主。我要逃离这罗网。
这是我所看不见的罗网,这罗网满布眼线,而所有的眼线都隐藏在这暗夜中。暗夜中的园林就是这罗网,就是这迷阵。这是比藏书楼书库更大的迷阵。这些逶迤交错的曲径,这些暗香浮动的树丛,这些于沉寂中陡然响起的鸟叫声,这些看不见的圈套和陷阱,它们构成一个杀机四伏的迷阵,而杀手们也曾走过我正在走的这路线,他们就藏匿于这迷阵的暗影中。
那片菜畦就在这迷阵的一角,就在这庄园的东南边,就在那片荒寂的隙地。稻田,杂树,瓜棚,菜畦,那片隙地别有一种野趣。微雨迷蒙,只有一条土路通往那菜畦。
韩熙载说那片菜畦是“藏园”。我要在那些杂树间找到那梅树。
大司徒似是信守了承诺,我的身后确是无人跟踪,周遭也不见有可疑的人影,而我要提防的不只是大司徒。李家明听命于樊若水,大司徒收了樊若水的金禅杖,可郎县令陈博士那边又会作何反应?倘若郎陈的幕后主使是朱紫薇,大司徒张洎既已亲自出马,朱紫薇自然也会伺机而动。朱紫薇与那女道人交好,那女道人此时又在何处?
我忽然有种可怕的推想。那位女道人会否就是这布阵者?毕竟是她最先给了我诗签,又是她写的朱雀二字将我引到了这韩府。果真如此,大司徒张洎未必就能最终得手,而我或将成为朱紫薇和女道人的猎物。
一条沟渠蜿蜒流经那片菜畦,菜畦中只有零星几棵小树,篱笆边有一簇簇野菊。我先欲查看入口处的瓜棚。那瓜棚看似已被废弃,当我悄然走近时,一只野兔飕地蹿出来。这瓜棚有槛无门,里边亦无人埋伏。秦蒻兰说那棵梅树长在河边,我当沿着这沟渠寻找。这沟渠蒿草茂密,两边种满了萝卜和芜菁,也有几垄大葱和芫荽。
那棵梅树就静立在渠水旁,虽有虬枝盘曲,而树形却不甚铺张。这是一株卧龙梅。这是韩府仅有的一棵梅树,它就长在这小河边,而这小河就是韩公意中的“河洛”了:黄河与洛水。
梅树的一枝已被砍断,树身上依然有发白的斫痕。我蓦然想到无尽藏那堆柴草堆。
那柴草堆中有新斫的梅枝,那是来自这棵梅树么?再看这树身上的斫茬,这分明与那断枝上的斫茬有一样的粗细。倘若这是有人刻意为之,倘若这是一种暗记,那么此举显然是为给我以指引。
这指引或许是一种误导,或许对方只为将我困死于此,然后收拢其罗网。
那被砍下的树枝确实不在此处,树身的断茬正对着一个小土丘,一个野菊簇拥的小土丘。——史虚白衣冠冢!这坟丘并无墓碑,坟前只有一块青石作供台。
供台是一块三尺见方的青石板,石板上并无供品,却有一截尺许长的梅枝。
这也是一截新折下的梅枝,似是有人故意将它摆在这供台上给我看。
我紧抱着这棵古梅的树干摇晃,这梅树根底牢固,非人手所能撼动。这梅树的周遭并无异样,坟丘上只有杂草和野花,惟有供台上的树枝显得很怪异。
雨水冲刷后石板泛动着光亮,石板下的泥土已有些疏松。我双手猛力掀开这石板,就见有一片细小的蚯蚓在蠕动。
蚯蚓和湿土之下有砖缝,砖缝间却无石灰粘连。我徒手拆开这六层青砖,就见这砖层下另有一块青石板。这青石板比上边那块更大更厚重,而我也使出更大的力气掀开它。
石板之下是一个竖井样的黑洞。井下一片漆黑,一时难断其深浅。黑暗中有星星点点的萤虫在飞动,这使我想到要取火。
我忙取过灯笼,又从背囊里取出火镰荷包,就趴在坟丘的背风处打火。
我左手捏紧火石,右手拿火镰快擦猛击。火石上火星迸溅,火石下的火绒便冒起青烟。我将火绒吹起明火,用这火苗点燃灯笼里的蜡烛。
我探下灯笼照亮这黑洞。这黑洞其实并不幽深,这只是一个约有丈许深的枯井,而洞围仅可容身。洞壁上粘满臭虫,也有一些特辟的脚蹬,而井底只有一些碎砖和杂草。
霉气直冲上来,有一股令人窒息的酸腐味。我咬紧牙齿叼着灯笼,强忍一阵阵恶心降到井底。
我扒开地上的腐草和烂砖。这井底土质坚实,非徒手所能深挖。正在这绝望之际,烛光照见洞壁上有道小石门。
这石门看似也难以徒手挖动。我脚蹬井壁升起身子,又发力朝石门猛踹一脚——
石门在微微晃动!
我再次升身猛踹,这石门便轰然倒下!
一股冷气冲来,石门倒处现出一个黑洞。
这该是史虚白衣冠冢的墓室了。
“朔风揭屋宇,浑家醉不知。”我在进入墓室的这一刹那,忽忆起史虚白的这诗句。
当年元宗帝南迁时路遇史虚白,问其居山多年可曾赋诗,史虚白说近得一联,就随口吟出这两句。元宗帝闻之变色,这诗句显然是暗讽国事,而“朔风”当指北方的强敌。这诗句也好似一道谶语,接踵而至的事变已应验了这谶语,而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应验。
而此时此刻,我只想到自己是一个闯入者。我破门闯入他的墓室,这位真人难道会浑然不知么?
“史虚白的事竟也还没完……”
那位女道人曾对我说这话。